核心提示
白河出沽源,流经赤城,一路南下,最终汇入首都北京的水系脉络。
为保证进京水质达标,沽源与赤城两县人民数十年携手攻坚,治河护岸、植绿固土、涵养水源……白河流域综合治理的脚步不断加快,范围逐步拓展。如今,每一滴奔涌进京的清水中,都浸润上游地区的脉脉涵养和执着守护。
时光飞逝,河水汤汤,这场碧水保卫战的乐章,还在叮咚不息地奏响……

解锁从岸净到水清的修复“密码”
在沽源县小河子乡,大片农田间,一条河道蜿蜒而过。
河道里一级级溢流坝错落有致,水生植物郁郁葱葱,水面倒映着蓝天白云,潺潺流水缓缓地流着。
“这就是沽源县白河流域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典型示范工程。”市生态环境局沽源县分局相关负责人于秀国告诉记者,该工程位于白河源头上游,实施目的就是为了进一步提升白河水质。该工程完工近四年,成效逐步显现。
“以前,一下大雨,周边的农田、山坡产生的地表径流,携带着泥沙、杂质通过沟沟岔岔的河道向下汇入白河,一定程度影响白河水质。”于秀国介绍,“现在建成的表流湿地,就是一个水质净化生态系统。在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地方,其实正在进行着一场净化常态战。”
在于秀国的手指方向,一条长长的石头墙横在山坡下公路边。这正是净化水质的第一道防线——铅丝笼坝,其对山洪进行拦截缓冲,干砌的石头坝中填充火山岩等填料,水经过第一道净化关后,来到生态隔离带,这里栽种的灌木等生态林将水携带的污染物氮、磷等吸收净化后,水通过管涵流入河道。河道内溢流堰层层叠水,放缓流速,让水在河道里至少停留7天,泥沙得到沉降。同时,河道内种植的芦苇、水葱、荇菜、睡莲等水生植物再次进行水质净化,让有机质得到分解。

“在白河源上游治水,需要跳出水而治水,上游的山,上游的耕地等需综合治理,这就是所谓的‘空间治理’。”于秀国说,“空间治理”的理念是好,但工程实施起来并不容易,特别是在坝上高寒地区种植芦苇、睡莲这些水生植物也是第一次。
“这种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项目,在南方常见,但在北方很少见,前期设计方案时,专门请教了北京化工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相关单位和专家组成员进行了多次的实地勘察。在哪儿建坝?怎么建?种什么植物?一遍一遍地勘察调整,才确定好最终建设方案。”他说。
建成表流湿地200多亩,16级溢流坝,每一级水面间落差50厘米,水深约70厘米,每天净水3000立方米——说到建设成果,于秀国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以前这里不下雨时就是个干河湾,下完雨变成烂泥潭。如今有流动的清水,丰茂的植物,栖息的水鸟,示范工程的成功为高寒地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据介绍,沽源县持续开展农业面源污染治理。2024年,总投资6300万元的沽源县白河流域上游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与水域生态修复工程已开工。同时,积极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和农药、化肥“双降”;加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等,通过一系列项目措施的实施,有效隔离畜禽养殖、农业种植等人为干扰对河流的负面影响,进一步减少面源污染,使全县白河流域水生态环境得到进一步保护修复。
抓住小流域治理这个“牛鼻子”
清晨,大海陀下,薄雾锁青山,道道山水汇聚成大海陀河,经刚修建的叠水坎逐阶而下,河中的树池将古树保护起来,影影绰绰,丛林间鸟鸣交错呼应,啾啾啁啁、嘟嘟哒哒……好不热闹。
赤城县水务局水保站站长赵振华正在巡河,2630米的铅丝石笼护岸牢牢阻挡了砂石,山水听话得如同孩童,沿着1860米的浆砌石护岸奔流向前,与红河相拥。不远处,堤坝上机械声轰鸣,施工稳步进行……这是投资1250.83万元、治理面积25平方公里的大海陀清洁小流域综合治理施工场景。
赵振华说,这25平方公里是施工难度最大的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涵盖大海陀自然保护区山脚下的三个行政村。河道里巨石堆积,有的石头比一间屋子还要大。为了砌护坝开槽,工人们用炮锤破开石块,弄平河道,垒砌护坝,吃尽苦头。
赤城县地处北京上风上水区域,每年向延庆白河堡水库集中送水,占了密云水库53%的水量,是建设首都水源涵养功能区和生态环境支撑区的前沿,战略意义颇为重要。然而,上世纪末,工厂建起,矿场林立,牛羊肆意啃食草场,在阵阵机器轰鸣声中,原本就脆弱的生态愈加失衡。
大海坨村党支部书记刘志军印象中,他小时候的大海陀河宽敞而清澈,后来河道狭窄,山石滚落,植被破坏,洪水肆意。“我自己就经历过两次大洪水,山水铺天盖地而来,太吓人了。”
赤城县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称法,全县5272.8平方公里,山地面积占到了总面积的80%,基础设施建设薄弱,治理谈何容易。为保护水源,赤城县关停取缔了一大批影响河流水质的工业企业,相继砍掉了近百个可能造成水污染或影响北京供水安全的项目,为生态“留白”留足空间。

赵振华走遍了赤城每一条河,每一个沟,每一道渠,摸清了这片山河每一寸脉络。他的口中,小流域综合治理,不是简单的治理一条河、一个湖,而是围绕流域上下游或者支流周围的村庄、树木、山地,因地制宜地布设水土保持措施,使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和耕作措施达到最佳配置,实现从坡面到沟道、从上游到下游的全面防治,形成完整、有效的水土流失综合防护体系。
“赤城县实行小流域综合治理的历史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中间几经起伏,近年来摸索出一套对症赤城县地貌、行之有效的办法来。”市水土保持工作站副站长王贺说。
在赤城书写的生态篇章里,有许许多多水务人书写出的小流域综合治理答卷:
2014年,北京市、河北省、地方政府整合各类资金用于清洁小流域治理项目;
2015年,开始实施密云水库上游生态清洁小流域治理项目,柳林屯村率先作为试点开工建设;
后来,距白河源头6公里的东栅子村创建了首都北部高寒贫困地区生态清洁小流域典范,获评“国家水土保持示范工程”;
在西沟生态清洁小流域治理成效初现,形成层林叠翠的生态屏障;疏通沟道后,水清河明,芦苇摇曳,成为靓丽的景观带……
通过采取以小流域为单元的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等多种治理方式,从2011年至2022年,全县水土流失面积减少了215.63平方公里,从2013年至2024年,累计完成水土保持综合治理面积356.5平方公里。
减,换来了“增”的空间,赤城县水土保持工程建设年减少土壤侵蚀量可达20万吨,增加土壤蓄水能力1000万立方米,境内红白黑三条河常年保持稳定水量,进入延庆白河堡水库的水质达Ⅱ类标准,年均入库水量2亿立方米以上,一条清洁的河、一份清澈的爱,缓缓流向北京。

建设“能吞能吐”的水源涵养林
群山青翠欲滴,白河源景区静卧在山脚下,草原天路从门前经过,蜿蜒延伸。
“保护白河源,植树造林涵养水源是头等大事。”塞北林场沽源分场工作站高级工程师袁保力说,2006年,林场在白河源周边植树造林一万多亩,截至目前,全县造林50多万亩。
2012年,沽源县启动京冀水源涵养林建设项目,到2019年,在莲花滩乡、西辛营乡、小河子乡、小厂镇等6个乡镇,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的重点区域,营造林4万余亩。
沿着草原天路东线驰骋,连绵起伏的山丘上,落叶松、樟子松、云杉、桦树、柠条、沙棘等植被茂密,区域林草面积达到宜林宜草面积的85%以上。林草覆盖度由治理前的27.3%,提高到治理后的71.2%。监测资料显示,年拦蓄泥沙46.44万吨,保土效率达75%,白河源径流0.5立方米/秒增加到0.65立方米/秒。
“森林生态系统具有涵养水源的强大本领,能‘吞’雨‘吐’水。”他说,“森林对降水具有截留、吸收和贮存,将地表水转为地表径流或地下水的作用,主要功能表现在增加可利用水资源、净化水质和调节径流三个方面。”
白河,三分之二以上的流域在赤城。这个时节,正是赤城县绝佳的旅游季,深浅不一的绿交织成锦绣山河。
“荒山变青山,可不容易。”与赤城县林草局总工办负责人李金龙一同前往云州水库上游的马营乡,澄澈的马营河静静流淌,汇入水库,沿途高低错落的储备林如梦如幻。

赤城县,既是首都“两区”建设的桥头堡,也是浑善达克沙地歼灭区的核心攻坚区。
治水,先要治沙。治沙,则要种树。
2000年开始,国家开始加大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力度。赤城先后实施京津风沙源治理、退耕还林、塞北林场等生态建设工程,完成营造林200多万亩,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150平方公里,阻挡了来自内蒙古高原的冬春季大风,抵挡了大量风沙,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治理速度大大提升。
从2013年到2018年的五年间,在马营乡、云州乡和独石口镇实施了京冀生态水源保护林建设合作项目以及国家储备林基地项目造林,605万株油松、落叶松、山杏、云杉等6万余亩荒山披上绿。
绿色版图不断扩张。赤城县重点公益林总面积188.8万亩,森林覆盖率达54.41%,林草覆盖率达到84.16%。荒山变青山,沿岸的生态环境得以恢复,在河水连绵不绝的滋润中,河滩地区形成许多绿洲,水鸟飞翔其间。
治理进、污染退;高端进、低端退……两岸人民正以更绿色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随着一河碧水奔涌向前。(记者 臧波 张凤燕 摄影记者 武殿森 陈亮 通讯员 赵晨阳 王晓曦 王怡宁)
来源:张家口新闻网原标题:算好“清水”进京的“加减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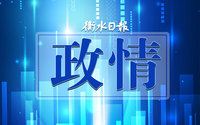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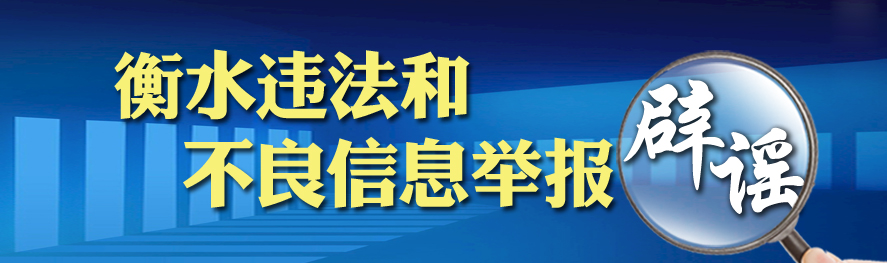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