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盛夏的早晨,我和老伴在公园遛弯。
在一片幽静的树丛里,我偶然看到一个意外掉落在地刚刚脱壳的夏蝉。看到这个幼嫩的生命,我的心里顿生了一种怜悯。因为用今天的生态学讲,在茫茫“地球村”里,它也是人类的朋友,况且这小东西还成为“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的夏日风景呢。于是我轻轻将它捏起来送回了小树的丫杈,希望能够助它完成一次生命的“蝶变”。
忽而,我想到了老伴的几次梦想和几次人生“蝶变”。
幸福的家
上世纪60年代,我中学毕业后在县城当了老师。那时女孩间流传着一个“一工二干三教员”的择偶歌谣。她怀着一个只有她自己才知道的“家”的青春梦想选择了我。在新中国成立10周年之际,我们成婚,成家,她由闺秀成了主妇,完成了为人妻,为人母的一次“蝶变”,开启了她新的人生旅程。
但是,她的这次“蝶变”远没有实现她的梦想。
我们的家庭天灾人祸接踵而至,先是母亲久病直至病故,接着1963年滹沱河特大洪水泛滥成灾,我的家乡地处滹沱河畔,连年洪涝灾害过后,耕地都成了“流沙”,土地常常是有种无收。接着,我又失去了工作。以后的十来年中,她年纪轻轻跟着我受了不少苦。
所以,对于这次“蝶变”,她心里有的只是一片困顿和彷徨,“家”的幸福一时杳然无存。
吃“商品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乘改革开放的春风,扬起了风帆,打起了精神,用心打理的日子像芝麻开花节节高。她开始抱着一个个的梦想,在几亩薄沙地上,寻觅着自己的幸福。
我们先后引进了“徐州684”“徐薯18”等花生和红薯优种,以及多项先进种植技术。当年,我们的花生单产达到了350多公斤,在河滩的流沙地上,我们的红薯单产达到了两三吨,两种作物比这里的传统品种不仅质量好,产量也高出几倍。1983年衡水农科所特别赠送了我们1公斤“衡单8号”玉米种子让我们试种。这年夏天,一场狂风暴雨过后,全村上千亩玉米方田的玉米被刮得一塌糊涂,唯独我家的玉米傲然挺立,灾后产量竟达400多公斤。还有正定县的“冀棉8号”棉花优种,我们所收籽棉其产量和质量,更是受到乡亲和收购站的青睐与赏识。所有这些,在我村都是空前的。
那年听电台广播,河北省农民人均收入达到了1200元,而我家的人均收入已经远超了这个数值而被乡亲们所艳羡。
丰收之后不忘乡亲,老伴把自己收获的全部籽种,凡可复种的,完全赠送或等量交换给了乡亲和友人,使几十家亲友的花生、红薯和棉花都获得了高产,首次打了农业翻身仗。
随着生活环境的提升,她的一个沉溺多年的梦想又开始复苏:就是像工人、老师、干部的家属,吃上“商品粮”,带领孩子们走出“沙土窝”。
上世纪80年代,我调到城里工作,按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她和孩子们“农转非”随我进城,她终于美梦成真,迎来了她多年孜孜以求的“商品粮”身份,实现了她的第二次人生“蝶变”。
一本鲜红的“退休证”
她常对我回忆说,从1978年到2019年,在这后半生的40年中,她经历的最大变化就是,把转非与未转非的孩子都带到了城里安居乐业,她也乘改革开放的春风,对孩子们苦心教育,带领她们彻彻底底告别了贫穷,走向了小康。如今几个孩子都在城里购置了商铺、住房和轿车,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人到老年,最需要的就是有自己的“老本儿”。于是,我的心里,她的心里,成天想的就是从我的养老金里尽量抠出一些留点积蓄,以备后用。
她万没想到的是,在她70多岁时忽然被批准按“家属工”办理了“退休”,她从“家属”又蜕变成了“企退工人”,领到了一个鲜红的“退休证”,今年她的养老金涨到了2000多元,从此没有了后顾之忧,最使她感到幸福的是,这才是一次最美好的“人生蝶变”。
前几年,市、县电视台为我的文化生活录制了一场电视节目,其中特别穿插了她的几个片段,她也一时名噪乡里,一夜间从名不见经传的农妇,倏忽成了她们家族的“名人”。她回老家,亲友问她生活怎样,她总有说不完的话。她说:“活了80多岁,俺真的说不出自己的生活多么甜蜜,俺常使劲儿地想,真的是一点也想不出自己还缺什么。”说到激动处,她甚至还会半歌半白地讲述着自己“人生蝶变”的最大感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辛劳为人民,共产党一心救中国……赶走了帝国主义,改善了人民的生活……”
从老伴的歌声里,我切实感到了她对美好生活的满足和对中国共产党的感激。
作者:张治安
 广告
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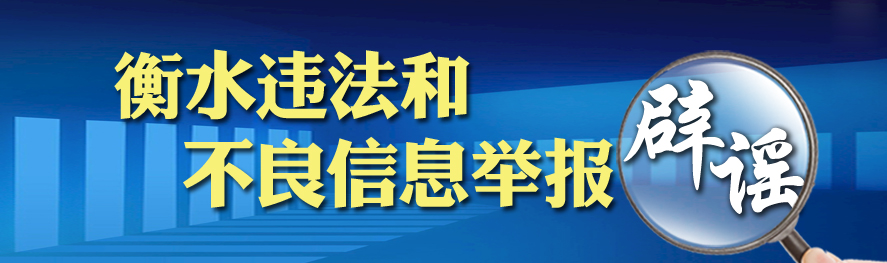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