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美国女诗人露易丝·格丽克(又译格吕克)。获奖理由是:她带有朴素美的、清晰的诗意声音,令个人的存在普世化。
格丽克的诗风别具一格,应该获奖。
读她的诗,会发现精警震撼的句子不多,但诗句的连贯每每出人意料、带来欣喜。读者思绪如落花在小溪中漂流,方向多变,却一直在石缝间前进。水底并不深黑,还清澈地透出石块石子,却不知终点多远。读罢意犹未尽,感觉弦外有音,于是忍不住再读一遍。这样的阅读感觉,贯穿在她十多本诗集。
她的诗篇开头大多是沉思的姿态。很多从回忆切入,带来更多回旋时空、自如思虑;也有的从当下切入,用“当我”引出思考和场景;还有的直接从哲理语气切入,一下就把现实生活感受转换为观照。后者更常用,比如“我醒着,我在世界上”(《星》),“夜不黑,黑的是这世界”(《别离》),“在我苦难的尽头/有一扇门”(《野鸢尾》),“看着夜空/我有两个自我,两种力量”(《春雪》),开口就把现实哲理化。
格丽克的诗风格独特,内容也贴近普通人生活。
她个人生活正常,大部分时间在高校任教。她童年不算温暖但一直深情对待家人,有过两次失败婚姻却并不偏激到否弃人生,这些都成了她诗歌回忆思考的基调。她的诗歌主题,集中于生死、情欲、梦境和家庭等人生感悟。在诗歌成熟期,她的诗行还加入了古希腊罗马神话以及宗教意象,把日常生活诗化、神化。显然,她热爱生活的情思都融汇到大量的诗作中。
《夏日花园》这样开篇:“几周前我发现我母亲的一张照片——/她坐在阳光下,她的脸涨红像是洋溢着成就或胜利。/太阳照耀着。几只狗/在她脚下打盹,在那里时间也睡着了,/像在所有照片中一样平静、不动。”多么温馨而深情。
《雪》的一段:“十二月底:我和爸爸/去纽约,去马戏团。/他驮着我/在他肩上,在寒风里:/白色的碎纸片/在铁路枕木上飞舞。/爸爸喜欢/这样站着,驮着我/所以他看不见我。”这样的亲情场景,很少人不为所动。
可以说,格丽克的生活体验和生命感悟貌似朴素实则深沉,貌似特殊实则蕴含普遍的人性。这就是颁奖词里“令个人的存在普世化”的含义。
如果进行比较,格丽克作为诗人的人生态度更为积极。美国早期女诗人狄金森终生独身,幽闭的生活限制了她的视野,诗意狭深却偏执。美国现代“自白派”女诗人伊丽莎白·毕肖普被视为同性恋,另一位女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以自杀诗篇闻名并自杀离世。智利女诗人米斯特拉尔(1945年获诺奖)因为情人病死而一生未嫁,最出名的诗篇竟然是写占有情人尸骸的满足。而人生态度积极的格丽克,即使心怀恐惧写死亡也不厌世,生活就是她生命的依托。1996年获诺奖的波兰女诗人辛波丝卡虽然也贴近现实,却从不把个人生活写进诗里,其贵族气远不如格丽克的诗歌更具人情味。无疑,热爱生活是诗人格丽克的突出优点。
格丽克诗歌的汉译者柳向阳认为,格丽克的诗意来自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诉诸日常生活特别是中产阶级家庭女性日常生活的感悟,更容易受到美国中产阶级追捧。其诗歌的哲理表达和神话宗教意象,也带给受教育的中产阶级读者以追索的乐趣。
这样也就比较容易理解,格丽克为什么多次获奖并成为2003—2004年美国桂冠诗人。此次诺奖颁给她,也就水到渠成。当然,她最后在众多角逐者中脱颖而出,还有今年的全球疫情大背景。
当全人类都在这场瘟疫威胁中担惊受怕,无数人困在家中相依为命的时候,格丽克诗中的生死、情欲、梦境和家庭主题正是当今人类的普遍话题。珍爱生命,热爱生活,防疫抗疫,是全人类的共识。这时候世界文学的最高奖,理应颁给格丽克这样热爱生活、敬畏生命的杰出诗人。
诺贝尔文学奖2016年颁给美国通俗歌手鲍勃·迪伦,今年又颁给一个热爱生活的诗人,这让许多以晦涩高贵自居自恋的作家诗人很失落。上世纪以来,由于西方现代派影响,很多诗人愤世嫉俗坐井观天,逃避到自然和文化,甘于病态生活甚至以自杀惊世,其诗歌不是狭隘偏激就是玩弄语言技巧,只能自娱自乐失去读者。几年内诺贝尔文学奖两次颁给趋向普通生活的诗人,昭示了文学回归大众和日常生活的正确导向。
这次颁奖,也会对中国诗歌创作产生良好影响,并给格丽克赢得越来越多的中国读者。让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陈世钟 编辑:李耀荣







 广告
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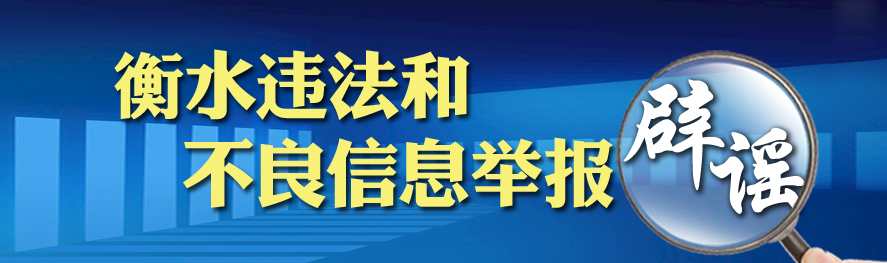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