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近年来,重点服务3岁以下婴幼儿的托育服务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而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托儿组”“托儿所”,到改革开放的“雇保姆”“市场化”,再到如今的“10分钟托育圈”“社区全覆盖”……数十年间,国家在相关政策上的调整轨迹、衡水因地制宜做出的种种尝试,在我们的报纸报道中被如实记录。

衡水市妇幼保健院托育中心,一名医护人员为孩子们做健康体检。
幼有所育、幼有所托,是重要的民生问题。近年来,随着国家生育政策的调整,相关配套服务也有了新变化:2019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婴幼儿照护服务迈向规范化、专业化;2024年,加强普惠育幼服务体系建设被明确提出,支持用人单位办托、社区嵌入式托育、家庭托育点等多元模式发展;2025年7月,《关于加快推进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明确,加快构建“1+N”托育服务体系。目前,衡水市已建成361家托育机构,每千人口托位数达5.6个,位列全省之首,实现了社区托育全覆盖。
“托儿组”福利+去家庭化
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将女性从“摇篮”解放出来成为重要议题。婴幼儿照料问题逐渐脱离“家务事”的范畴,福利性质的应急、固定托儿所及互助托儿组应运而生并取得了显著效果。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托儿所在衡水城乡、单位机关内大规模地广泛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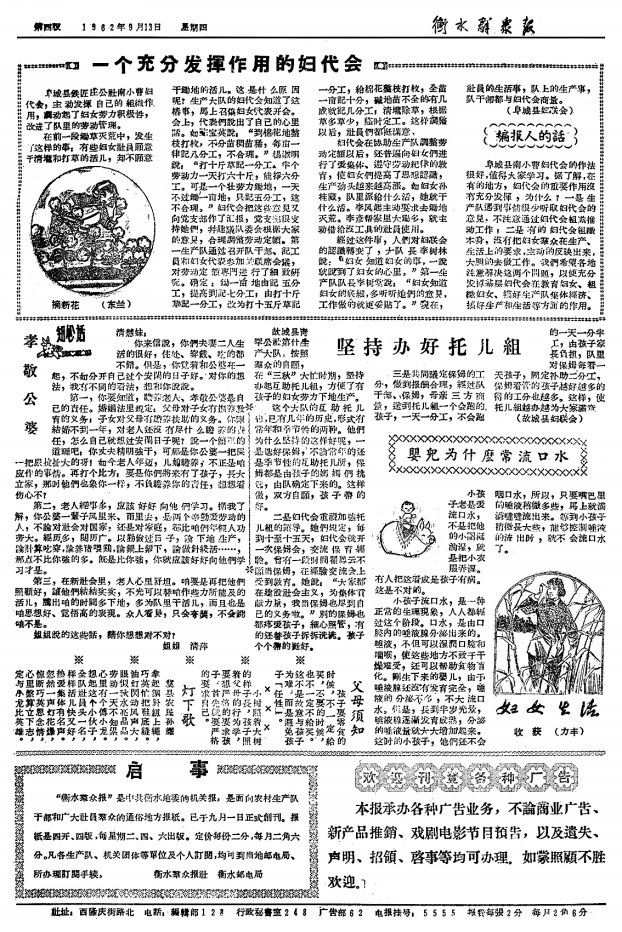
1962年9月13日《衡水群众报》
“故城县青罕公社第什生产大队。按照群众的自愿,在‘三秋’大忙时期,坚持办起互助托儿组,方便了有孩子的妇女劳力下地生产。这个大队的互助托儿所,已有几年的历史,形式有常年和季节性的两种”(1962年9月13日《衡水群众报》4版)。
“在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中,我区广大妇女发挥了重大作用。”1963年3月7日的头版上,一组组数据力证了这一结论:一般妇女劳力全年出工,平均达到150到180个劳动日,多者达到300个劳动日以上;妇女劳动日数占到男女劳动日总数的50%左右;农业战线上出现的妇女先进人物达43856名……而这,皆缘于各地注意合理安排妇女劳动力,根据生产需要和妇女社员要求,组织了托儿所(组),解决了妇女下地生产时孩子无人看管的问题。“仅深县、景县、故城、阜城、武强5个县,在农忙季节组织托儿组1758个,受托孩子达到38727个。”
托儿所(组)的出现,不仅推动了经济生产的发展,更获得了群众的一致好评。这不,景县李高义大队贫下中农忍不住向报社投稿,《夸夸俺队的幼儿班》:1969年“三秋”大忙季节,一些带孩子的妇女看着大伙忙得喘不过气来,心急火燎。大队党支部立即组织研究落实办幼儿班的事。当年,30多名带孩子的妇女摆脱了孩子的负累,积极投入生产中。“几年间,大队坚持常年办幼儿班,解放了妇女劳力,大家都说办幼儿班是个好办法”(1975年12月8日《衡水日报》3版)。
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婴幼儿照护服务多以工会或生产组织的集体福利形式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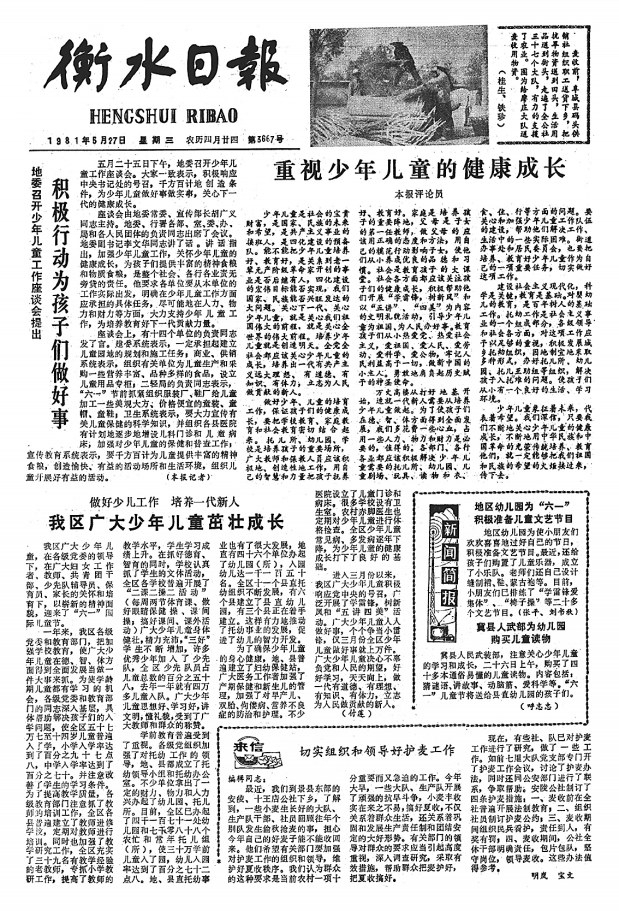
1981年5月27日《衡水日报》
衡水地区各级党组织加强了对托幼工作的领导,地、县都成立了托幼领导小组和托幼办公室。不少单位拿出了一定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兴办起了幼儿园、托儿所。1981年5月,全区已办起了4171处幼儿园和7088个农忙和常年托儿组(所),使30万学前儿童入了园,幼儿入园率达到了72.8%。地、县直托幼事业也有了很大发展,地直有46个单位办起了幼儿园(所),入园幼儿达1150名。全区11个县直托幼组织不断发展,有6个县建立了县直幼儿园,有3个县正在着手建立(1981年5月27日《衡水日报》1版)。
“雇保姆”家庭+市场化
改革开放以后,托育服务逐步从单位福利转向市场化供给,家庭育儿责任被强化,出现了自办托育机构。
武邑县城关镇东街生活优渥的中年妇女杨秀清,自筹4000元办起家庭幼儿园,致力于儿童教育,受到幼儿家长欢迎。她不仅自费盖起了3间教室,购买了一些幼儿图书、玩具、小车和一架风琴,还专门到县幼儿园学习掌握幼儿教育知识。“创办一年间,就精心培育了30名幼儿”(1987年10月31日《衡水日报》3版);安平县后庄乡场屯村离休干部窦世安,回乡后义务办起一个能照护50多名幼儿的托儿所,解决了农忙季节村里大部分学龄前儿童无人看管的问题(1989年10月6日《衡水日报》3版)。
1988年国家教委等8部门联合制定的《关于加强幼儿教育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养育子女是儿童家长依照法律规定应尽的社会义务,幼儿教育不属于义务教育,家长送子女入园理应负担一定的保育、教育费用。”托育服务开始由原先的公共福利占主导,逐渐转向家庭和市场并举的局面。
这一阶段,托育更多地回归了家庭,家庭中的老人承担了很多:阜城县张晓入职后不久就成为一名妈妈,因为工作忙碌顾不上幼子。开明的婆婆主动承担了看孩子的任务,才让她心无旁骛地扑在工作上,连年获得荣誉(1990年6月29日《衡水日报》3版);读者投稿《爸爸为我看孩子》中这样写道:前两年,爸爸刚办完离休手续,本想静下心来好好享享清福,岂料我那呱呱坠地的小女儿又给爸爸增加了新工作。我和妻子上下班时间卡得很紧,这下可把爸爸忙得不亦乐乎,连平常划拉两圈麻将的喜好也被迫取消了(1992年11月19日《衡水日报》3版);一篇《离退休干部职工心态录》,归纳了几种不同的生活形态,把“看孩子”、成为“免费保姆”的老人归入了劳累型。戏言“把老人看成不要工资的保姆,看了老大的孩子,还得看老二老三的孩子。有时三四个都送去,闹哄起来,没个清静的时候”(1994年2月1日《衡水日报》3版)。

1995年6月18日《衡水日报·星期刊》
与此同时,雇佣保姆也成为更多家庭的选择——农民雇保姆料理家务,这一新鲜事出现在故城这个冀南小县。农家妇女纷纷离开锅台,投入商品生产和流通领域,又被繁杂的家务牵扯。于是,一些妇女也学着城里人的做法请人帮助料理家务,照看孩子,以便自己能轻装上阵,闯荡商海。“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县城及各乡镇约有200户农家雇了保姆”(1995年6月18日《衡水日报·星期刊》1版)。
“托育圈”社会+体系化
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社会需求增加,托育服务再次受到关注。
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幼有所育”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而“谁来育”“怎么育”,成为公众关注的问题。据统计,当时全国婴幼儿在各类托育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1%,远低于一些发达国家50%的比例。“入托无门”成为很多0岁到3岁幼儿家长的心病(2017年11月13日《衡水日报·晨刊》B3版)。
国家政策不断调整,持续释放着大力发展托育服务的信号。我市各级各部门积极响应。
2020年,《衡水市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实施方案》出台,确定了“一年试点先行、三年全面铺开、五年巩固提升”的总体安排,以创新发展、务实高效、管理规范、满足需求为总体目标,推动全市婴幼儿照护服务事业健康有序发展。力争到2025年底前,主体多元、管理规范、服务优质、覆盖城乡的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基本形成,人民群众的婴幼儿照护服务需求得到进一步满足(2020年7月27日《衡水日报·晨刊》B2版)。
接下来,我市在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中,将完善托育公共服务设施列入丰富社区服务供给、提升居民生活品质需求的内容行列(2021年3月18日《衡水日报》1版);市卫健委大力推进婴幼儿照护服务试点工作,全市共建成省级试点4个、市级试点10个、县级试点1个。据统计,全市各类托育机构共接收3岁以下婴幼儿1076名,通过备案的有13家(2021年6月8日《衡水日报》3版);次年,我市发布《落实婴幼儿照护服务试点示范工程实施方案》,促进多种形式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发展(2022年2月21日《衡水日报》3版);其间,不断举办托育机构和家政服务培训会,推进我市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快速发展、建成一批具有示范效应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提高托育照护水准。
……
星光不负赶路人,江河眷顾奋楫者。
2023年3月,衡水全市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省、市级试点达65家(2023年3月15日《衡水日报·晨刊》B2版);4月,我市入选首批全国婴幼儿照护服务示范城市(2023年4月8日《衡水日报》1版);5月,“衡水幼教论坛”交流研讨与学术报告会在衡水职业技术学院举办,为推动衡水幼教领域高质量发展、京津冀一体化教育协同发展增添了新动能、指明了新方向(2023年5月17日《衡水日报·晨刊》B1版);6月底,我市托育服务工作成绩亮眼,全市千人口托位数、托育机构备案率和托育服务机构普惠率等多项指标在全省排名第一(2023年9月25日《衡水日报》3版);11月,我市千人口托位数5.40个,提前3年完成“十四五”目标任务,22518个托位均为普惠性,297家托育机构全部纳入“互联网+托育”平台,市、县两级均建有婴幼儿照护服务指导中心(2023年11月29日《衡水日报》1版);12月,我市成为2023年“中央财政支持普惠托育服务发展示范项目”入选城市,为河北省唯一(2023年12月26日《衡水日报》3版)。

2023年12月26日《衡水日报》
作为全国首批婴幼儿照护服务示范城市,我市持续推动托育服务提质增效——打造10分钟托育服务圈,出台入托补贴政策,建立市、县两级婴幼儿照护服务指导中心,发展医育结合、智慧托育等新业态;将婴幼儿照护服务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不断完善政策支撑体系,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努力实现“方便可及、价格可承受、质量有保障”的托育目标,托育服务供给能力获得显著提升,让幼有所育真正实现了“托得到”“托得起”“托得好”。

衡水市康复托育中心探索出“医育融合”特色模式。

景县第一托育中心内,孩子们在老师的陪伴下玩耍。

衡水市小萝卜托育中心保育老师们在给入托宝宝读书讲故事。

衡水雪融托育中心保育师带领幼儿做泥塑。
(本版配图均为资料图片)
领办人:韩雪
线索征集邮箱:hsbhbq2025@163.

 广告
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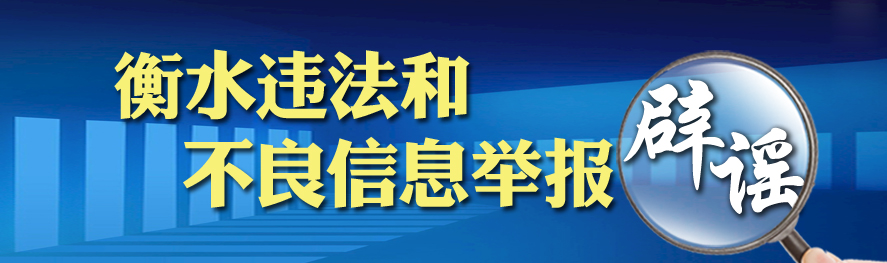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