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幼在大运河边长大,听惯了纤夫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
自从隋炀帝开凿大运河以后,这条河就成为南北水上运输的“黄金通道”。特别是元、明、清三代,封建王朝定都北京,漕运进入了鼎盛时期。当时,每年运粮漕船两万余艘,首尾衔接十几里,伴随浩浩荡荡船队的,是此起彼伏、气势磅礴的号子声。
运河号子实际上是为提高劳动效率,由劳动人民严格说是那些船工们而创作的一种专业性的“民歌”。运河行船,拉纤的一般有十几人甚至二十余人。运河号子起到协调动作、激发士气的作用,就像战场上的军号声,具有统一号令、指挥行动的功能。
运河号子就像运河平缓的流水,“歌词”朴实,调子粗犷、沉稳、雄浑、有力,节奏感很强。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工作,有不同的号子。它伴随着船只从起航到收航,从船上到船下的各种劳动场面,起唱迎合。充分表现了船工们不畏艰险、敢于战胜困难的信心和乐观主义精神。
运河号子根据行船转弯及顺流、逆流等不同情况的变化,有冲号、上嘴号,修船时有捻号。现在能忆起的大约有打蓬号(推船桅)、跑蓬号(落船桅)、起锚号、拉冲号、拉纤号、摇橹号、撑篙号、窜篙号、出舱号、闯滩号、绞管号、警戒号、联络号、下桩号、闲号等十几种,分上游号歌、下游号歌两大类。上游号歌包括拉帆、开船、拉船三种。下游号歌包括打锚、撑船、摇橹等。如启航前喊打蓬号,平水时喊摇橹号,上水时喊拉纤号,船搁浅时喊推船号,卸货时喊出舱号、上肩号、搭跳扛粮号(过翘板)等。起锚号是在铁锚久拖不起时船工用力拔锚所唱的号子,船工们抓住锚绳边拉边唱:“千斤呀,万斤呀,嗨!铁锚呀,动身呀,嗨!”慢慢地,铁锚在众人的齐声唱和中被缓缓拔起。
商船成年累月漂游在水上,很少有上岸的机会,船工们的生活枯燥孤寂可想而知。运河号子应运而生,它的歌词都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根据实际境况自行编排的,多数采用乡间俚语,生动有趣,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意在调剂人们的情绪、活跃气氛、振奋精神。如“嗨呀哈嗨!栽下膀子探下腰,背紧纤绳放平脚,拉一程来又一程噢,不怕流紧顶风头。临清州里装胶枣,顺水顺风杭州城,杭州码头装大米,一纤拉到北京城。”“哟嗬嗬……哟嗬……一声号子我一身汗,一声号子我一身胆。”纤夫们在“嗨呀哈嗨”的“歌唱”中忘记了疲劳,忘记了寂寞,俗语有“号歌一唱轻三分”的说法。
运河号子的歌词既有对现实生活的调侃,也有自我解嘲的诙谐;既有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也有对旧社会的痛恨和控诉。例如:
喂哟,摇起来了!喂喂!(领)
一条手巾哎织得新,
上织新年迎新春哟。
乾隆乘船北京去哎,
文武百官随后跟哟;
两条手巾织得长哎,
运粮河上运粮忙哟。
江北的焦枣往南运哎,
江南的大米过长江哟……
咳哟!(合)
运河号子的演唱形式除起锚号为齐唱外,其余都是一领众合。如拉纤号:
运河水哟,东南流哟(领),咳哟、咳哟!(合)
流水长吆,没有头哟(领),咳哟、咳哟!(合)
过张秋吆,入黄河哟(领),咳哟、咳哟!(合)
大纤绳吆,三丈六哟(领),咳哟、咳哟!(合)
拉呀拉吆,向前走哟(领),咳哟、咳哟!(合)
顶着风吆,淋着雨哟(领),咳哟、咳哟!(合)
用力拉吆,不停留哟(领),咳哟、咳哟!(合)
道又远吆,船又重哟(领),咳哟、咳哟!(合)
拉到头吆,到杭州哟(领),咳哟、咳哟!(合)
又如摇橹号:
喂哟,摇起来了!(领)咳哟!(合)
逆流拉纤号:
喂了我的喂,拉顺了(领)!喂上喂!(合)
哈下你的腰(领)!喂上喂!(合)
打住我的鸟(领)!喂上喂!(合)
……
一唱一和,一呼百应,组成了一套情感丰富的小乐曲。
小时候,远远地听到运河号子,就知道航船来了,于是跑到河堤,去看那埋头拉纤的纤夫,扬着白帆的船队,学唱着那高昂、豪放的运河号子。凡河边上长大的,大人小孩几乎每人都会喊两口。
领唱的人叫做“号头”,一般都是有经验的老船工。他发出韵化了的号令,歌中有词,词中见情,即兴编唱,用音乐语言来指挥劳动,整齐大家的动作,给人们带来欢乐,往往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当船舶行驶至船多、人多之处,如遇港口各路航船相聚时,“号头”还会以号歌打招呼表示友好,唱各种花号,比谁的音调唱得美,谁的词意编得好,一方面取长补短,互相交流,一方面为大家休息时玩赏助兴。哪只船的船工唱得响亮有力,哪只船的主人就会感到自豪。因此,号子也成了船主实力的一种标志。
20世纪60年代末,运河因大旱断流,航运停止消失,运河号子也消失殆尽。现在,会唱运河号子的人凤毛麟角,这套错落有致、韵味悠长的“船夫曲”成为千古绝唱。幸喜的是,一些有识之士已认识到抢救运河号子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开始整理出一些号歌。运河号子吼出的是一段船工的真实生活,唱出的是一首壮美的史诗。
作者:宫瑞华 编辑:李耀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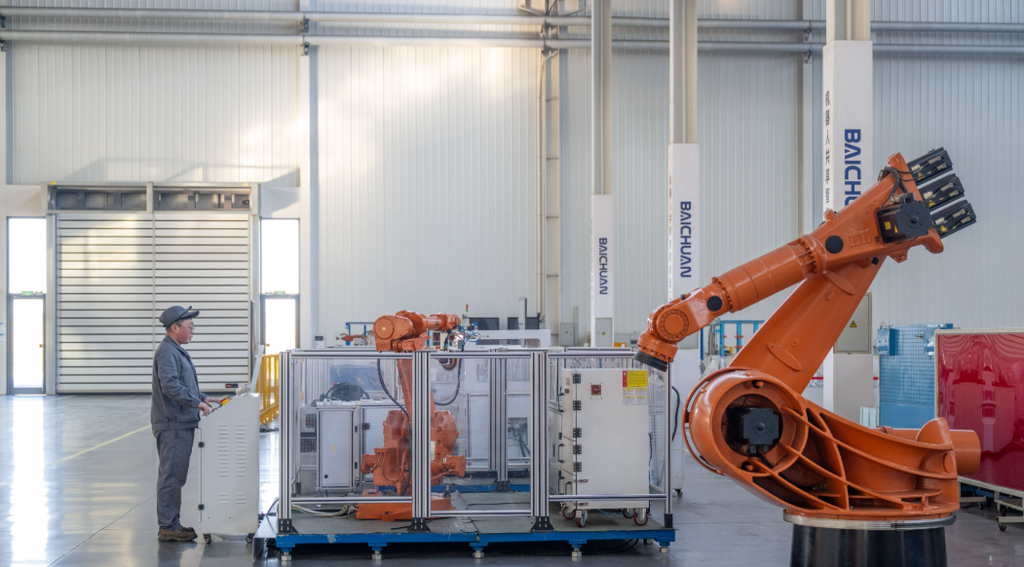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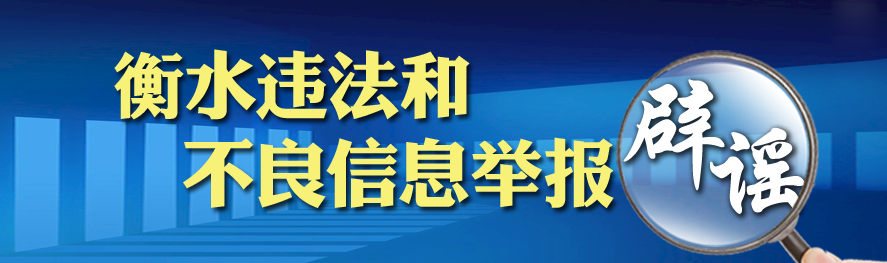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