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里香”“八里香”“满口香”“护脖香”……这是我在关外之地——沈阳的街头早市烟摊所见的牌子,真是很惊异于卖烟人的文学天赋。“十里香”比“八里香”优胜何在?“满口香”与“护脖香”味道如何?真叫人有些馋涎和想入非非。
过去我也算“半截烟袋”,但所抽都是卷烟。但印象中“香”字招牌却不多见。似乎有种“郁金香”,但却没抽过。
村中发小多抽烟,都是“攒忙”所学。那时村人互助,打坯盖房,砌墙抹顶,再穷人家也要准备旱烟,就成了“烟枪手”的培训基地。
我在家常做攒忙小工,但没学过卷烟。到县委宣传部上班后,和老秦对桌而坐。他烟勤,常抽一毛六的“岗南”牌。写稿是望墙憋的差事。他憋不出词时就吞云吐雾。我挨憋时就撕纸。一张纸先撕成条,再团成蛋蛋,然后用脚来回搓。
有次我写报道,总对导语不满,脚下一会儿就团了五六个纸蛋。这时老秦笑着把一支烟递到我手边,笑着说:“熏熏就开窍了。”然后又“啪”一声打着火,晃到我眼前。我也不知怎样接了送到嘴边。虽然没照镜子,但拿烟的姿势肯定笨拙而可笑。
老秦的抽屉里,总备着几盒“岗南”。那天他要下乡,就拿出一盒塞到我抽屉里,似很认真地说:“给你一盒。若有人找你,递根烟也好看。”俨然一副老大哥的气度。
这盒烟放了几天,恰好村里发小来访。我递他一支,他很高兴地猛吸两口,笑嘻嘻地说:“你没白混官饭,长了点儿出息!”
看来老秦说得对,“烟香”之理确关处世之道。老秦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后来没几年就当了县长,我却始终默默无闻,寸功未建。常找我的村中老友调侃说:“要叫我站你这地方,早在县里打圆了场!”这样说的原因,往往是我没好烟叫他抽的时侯。
我虽抽过烟,但对烟之“香”却未曾领略过,也可以说一窍不通。
上世纪七十年代,抽过最好即最贵的烟是“石桥”,每盒三毛一分。那时下乡吃派饭,一天要交三毛钱。这盒烟超过了一天的饭费。记得那是抽老部长徐立文的蹭烟。他每次下乡都要买两盒“石桥”,自己一根不抽,却只卷大叶。烟卷专供司机和反映情况的干部社员享用。有次在车上他亲自给司机点着烟,又递我一支。我连连摆手,表示不会。他却说:“听说你正学哩。”硬塞给我一根。我心里也想尝尝好烟的滋味,就接了。但抽过之后却并没什么特殊感觉。那时一到村里,必有不少干部群众来找徐部长,有的一进门就不客气起说:“抽部长根好烟!”有的则抓过徐部长的烟布袋卷大叶。他的烟“香”之道是和百姓打成一片。
后来读孙犁,大师在文中写道,让老百姓产生信任感和亲切感的经验,“一是烟酒不分家,二是抢着抱孩子。后一种做法尤其受女人欢迎。”
大文人多喜欢烟。
鲁迅不用说,他的照片、版画多有手夹香烟的形象。大师学医出身,莫非不知烟之利弊?
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的汪曾祺,在《烟赋》一文中,写了一首诗:“玉溪好风日,兹土偏宜烟。宁减十年寿,不舍红塔山。”他并非调侃,郑重其事地接着写道:“诗是打油诗,话却是真话。”
最令人惊叹的是陕西文坛三座并峙的高峰——路遥、陈忠实和贾平凹,都是烟名不逊文名,深谙烟香之道。
路遥写《平凡的世界》,在屋里闷一周就要扫出半簸箕烟头。
陈忠实创作《白鹿原》,则是回乡下老屋,天天抽着黑黢黢的雪茄,雪茄偶有断顿则卷大叶。
贾平凹抽烟则更有豪爽之名。每得新鲜的高档烟,必呼朋引类到家共同品赏,也算“烟坛”佳话。
每当读到此类文字,我就想到挚友老秦的话,“熏熏就开窍了。”那些文豪级人物,肯定也有不通窍的时侯吧。陈忠实的《白鹿原》完稿后,曾悲壮地对妻子说:“这本书写不好,我就和你回乡下养鸡!”其实他应该说“我就从此戒烟!”
他们的烟“香”之道是为文学拼命。
其实戒烟很难。别说那些“瘾君子”,即使如我这曾经的“半截烟袋”也很难一刀两断。
我没在口袋装过烟,只是“蹭抽”,这难免叫堂而皇之的吸烟人看不起说:“你这叫抽烟吗?”但与那些根本不抽的人相交,又自觉不太“纯粹”,人家则说“原来你也抽烟啊!”
据说真正“瘾君子”能够果断戒掉的都是狠角色。我曾经把熟识之人滤过一遍,此话大抵不差。
我无此刚毅之力。多次想戒,偶遇相识旧交,递过一支又不好辞却。但真抽两口,实在难解“烟香”,就又产生悔意。由烟悟道,思及处世之理,也总是“足将进而趔趄,口将言而嗫嚅”,前瞻后顾,首鼠两端,以至涉政寸功难建,为文少有佳绩。古书上常说“文也不成,武又不就”,还说“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大概就包括我这类人。
我其实几十年也尝过很多名牌烟,都已毫无印象,也没觉出“香”过。但多年来总想到老秦那盒“岗南”和徐部长的“石桥”。老秦回原籍后多年未通信息,徐部长过世也二十年矣。每当想到他们,似依稀有淡淡的香气缭绕于前,使人深思和怅然。
看着眼前的烟摊,我想无论这些烟有多“香”,也再不去品尝了。即使品尝,还能找到当年的味道吗?
作者:何同桂 编辑:李耀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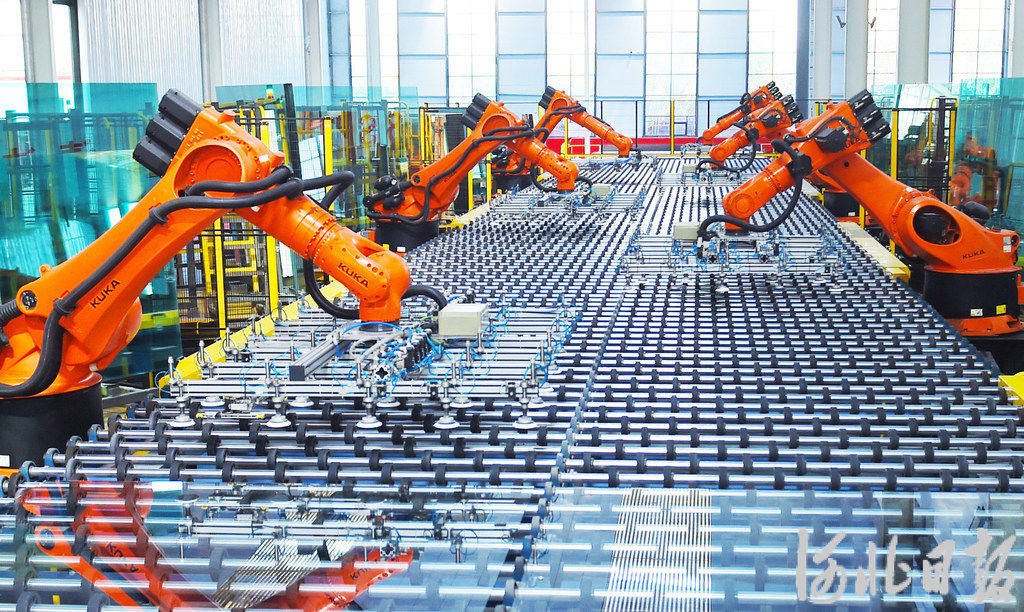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