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枣强县新屯镇,娄子村如一颗镶嵌在冀南大地上的明珠,既有战火淬炼的厚重历史,又有今朝安宁的乡村景致。2100多名村民在此世代居住,让这个村既承载着民族抗争的集体记忆,又续写着新时代的祥和篇章。
驱车沿着蜿蜒的柏油路驶入娄子村,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村外生机勃勃的田野,玉米、高粱在风中舒展腰肢,盛夏的绿意沿着田埂蔓延至村落边缘。村内,平坦的水泥路连接着家家户户,红砖墙、灰瓦顶的院落错落分布,门前的月季、院内的石榴树为村落点缀出鲜亮的色彩。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斑驳的光影,孩童们骑着自行车在巷口追逐打闹,清脆的笑声穿透了村庄的角落。老人们则在树荫下悠闲地话着家常,处处洋溢着岁月静好的气息。然而,只要和村里的老人们聊起过去,他们眼中便会泛起别样的光芒,80多年前“奇袭娄子镇”的战斗故事,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一位老人指着村西的娄西街告诉记者:“当时我们村是娄子镇所在地,现在都变成普通民房了。”时间回溯到1941年,那时的中国大地正深陷抗日战争的烽火,冀南抗日根据地是抵御日寇侵略的前沿阵地,而娄子镇作为交通要道上的重要集点,被日军设为据点,像一颗“钉子”插入了抗日根据地。
这个据点可不简单,由日军一个小队18人驻守,小队长斋藤狡黠凶狠。他们配备了轻重机枪各一挺、掷弹筒一个,武器精良,据点工事坚固,还囤积着大量弹药、食品和资财,此外,还有伪警备队及警察所三十余人助纣为虐。更棘手的是,据点东南十二里的大营镇驻有日军中队部,随时能提供支援,拔除这个据点的难度极大。
但娄子村的群众抗日觉悟极高,村内有活跃的党支部组织,日伪政权的维持会的会长、副会长都是经批准打入的共产党员,全村没有一人在外当伪军,这为我军行动提供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和情报支持。1941年5月上旬,维持会会长向冀南军区新七旅19团送来详细的敌情报告,表达了村民们打击日伪的强烈愿望。
19团的战士们经过细致侦察,发现了据点的防守规律:白天由伪军放哨,会征派民夫到据点内干活,日军则在屋里睡觉;夜间,日军轮番上碉堡站岗执勤。针对这一情况,团部制定了精妙的奇袭方案:15人组成的奋勇队配手枪扮民夫突入,40人组成的突击队夺岗哨,二营负责歼灭伪军与搬运物资,一营阻击大营援兵。
为确保行动成功,19团率先开展锄奸斗争,掌握了日伪政权的维持会,又组织15人的奋勇队,全部配上手枪,化装成民夫,准备利用早晨民夫上工的机会混入据点。奋勇队还下设3个组,分别负责消灭前院敌人、占领后院和干掉日军小队长。
1941年5月23日凌晨4时,陈再道司令亲自进行战前动员,奋勇队趁着夜色出发。天亮后,地下党员、伪维持会会长魏子阳以带民夫做杂工、送食物为名,敲开了敌人据点大门。看门的两个伪军见篮子里有鸡蛋,便伸手去拿,奋勇队员趁机下了他们的枪,迅速冲进据点。
勇士们如猛虎般扑入据点,第一组全歼了前院在睡梦中的日军,并将重机枪送出院外,第二组突袭后院,15名日军迅速毙命。当第三组攻向日军小队长斋藤住处时,枪声惊醒了他,斋藤挥刀顽抗,击伤队员后窜上碉堡,一名伤兵也趁机钻入同守。突击队强攻时遭遇手榴弹与毒气阻击,因无防毒装备难以近前。
与此同时,二营部队已经搬运出许多弹药资财,附近群众也积极响应,用提前准备好的十辆大车迅速将缴获物资装车运走。此时,大营来援的敌军已与一营部队接触,为避免陷入被动,团指挥员果断下令撤出战斗。而住在另一个院子里的伪军,在我军强大的政治瓦解与军事威迫下,多数缴械投降。
这场奇袭娄子镇的战斗,耗时90分钟,19团以伤亡11人的代价,毙日军16人、俘伪军9人,缴获轻重机枪各1挺、掷弹筒1个及大批物资。它打破了日军 “囚笼政策” 的嚣张气焰,成为冀南抗战中以智取胜的经典战例。
历经岁月的洗礼,当年的娄子镇现在已经归属到枣强新屯镇,娄子村也早已不是当年深陷战火的模样。但这片土地上的抗战记忆从未褪色,那些手持简陋武器却无畏冲锋的战士,那些在敌后传递情报的地下党员,那些推着大车支援前线的普通百姓,他们用生命铸就的精神丰碑,永远矗立在历史长河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
如今的娄子村,虽已不见当年的战火纷飞,却永远铭记着那段烽火岁月。它用今时今日的安宁与祥和,告慰着那些为这片土地牺牲的先烈们,也向世人展示着从战争创伤中走出的乡村,在新时代焕发出的蓬勃生机。







 广告
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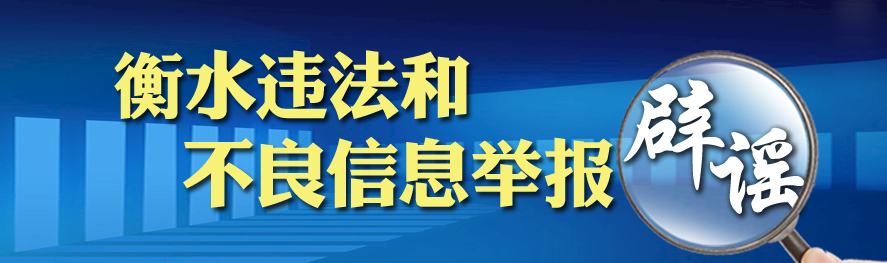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