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张丽钧在《无可挽回的老去》中写道:人生只有三晃,一晃大了,一晃老了,一晃没了。直教人读来触目惊心,真的这样两晃三晃,一生就没有了?我们的生命竟是如此的仓皇、局促、囫囵和盲目。
时光将生命带走了,我们还不晓得时光的样子。《辞典》告知我们,时光意指时间,是指一切物质不断变化和发展所经历的过程。多么无情的一句话啊!从故乡到异乡,从少年到白头,生老病死,哪个不是过程?在时光这个大到无限的容器里,我们如何自处?
二
“我拼命工作,天天洗澡,不接待来访,不看报纸,按时看日出(像现在这样)。我工作到深夜,窗户敞开,不穿外衣,在寂静的书房里……”居斯塔夫·福楼拜在写给最亲密女友的一封信中说。读到“按时看日出”时,我的心被狠狠地蜇了一下。这位远离名利场的大剧作家,以“面壁写作”为誓志的世界文豪,一个吝惜时间拼命工作至深夜的人,却在每天惦记着迎接日出,把在我们看来寻常不过的晨曦之降视若生命的盛事,当成了一门灵魂的日修课。
原来对于时光的莅临,这才是我们该有的仪式,庄严,神圣,深怀敬畏之心。
三
在李敖的文章中,我同样读到过这位放荡不羁的“文化狂人”对于时光的虔敬。他习惯对任何事物都采取批判的态度,唯独在时光面前就变成了活脱脱的赤子。“只要天气好,我每天中午都有一个约会,约会的对象不是人,也不是人活在上面的地球,而是比地球大130万倍的太阳。”要知道,他约会的这个地点,不是高山、平原和海边,而是在失去自由的牢狱。约会的这个时间,更是他仅有的午饭后到下午劳动前的两个多小时特别安静的时间。这是他狱中最宝贵的时间,他没有用来思考,没有用来写作,更没有用来抱怨和批判,而是用来平静地看看太阳。
阴暗的囚室,巴掌大的小窗,童真的李敖,目不转睛地望着时光从左边的窗沿一步步走过右边的窗沿,最后消失不见。失去自由,那一缕时光仍为他保留下温暖、责任和良知。
四
孔子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庄子说,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李白也曾慨叹,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苏轼更是对人生留下了千年一喻,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我们的祖先有过太多的关于时光的论述和关注,只是不知自何时起,我们生命的注意力已悄然转移。在日常交谈中我们发现,有些人熟知汽车的配置、性能和价位,有些人对于服装的品牌和款式如数家珍,有些人则对某些官员的背景和履历了如指掌,还有一些人最善于洞察商机和股市,甚而有一些人则痴心于各式各样的彩票和赌博。时光的位置正在被功名利禄、酒色财气一步步取代,终至哪天被忽略不计。
《儒林外史》中有一处情节说是:杜慎卿几个文人游金陵雨花台,“坐了半日,日色已经西斜,只见两个挑粪桶的,挑了两担空桶,歇在山上。这一个拍那一个的肩头道:‘兄弟,今日的货已经卖完了,我和你到永宁泉吃一壶水,回来再到雨花台看看落照!’”可叹吧,我们一辈子到头还不如这两个卖粪人在时光上的觉悟高妙!
五
生命的价值正是在对时光的品味里得以升华。如今不消说品味,生活中就连看一眼时光都显得奢侈而多余。需要追求的东西太多,哪里有这个工夫?说到品味时光,我最喜欢木心的一句诗: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时光里的爱情,爱情里的时光,多么令人向往的生活情致!
时光没有变,脱离了时光的爱情却已变得面目全非。有的人囫囵半咽,一辈子过得寡淡少味,这实在怨不得别人。
六
米兰·昆德拉在《为了告别的聚会》中对捷克人的生活有一番这样的描述:在这个国家,人们不会欣赏早晨。闹钟打破了他们的美梦,他们突然醒来,就像是被斧头砍了一下。他们立刻使自己投入一种毫无乐趣的奔忙之中,请问,这样一种不适宜的紧张的早晨,怎么可能会有一个像样的白天!
我真庆幸,在他的笔下,这个被斧头砍醒的民族是别人而不是我们!可我们又是怎么样醒来?拥有一个什么样的白天呢?
作者:贾九峰 编辑:李耀荣
 广告
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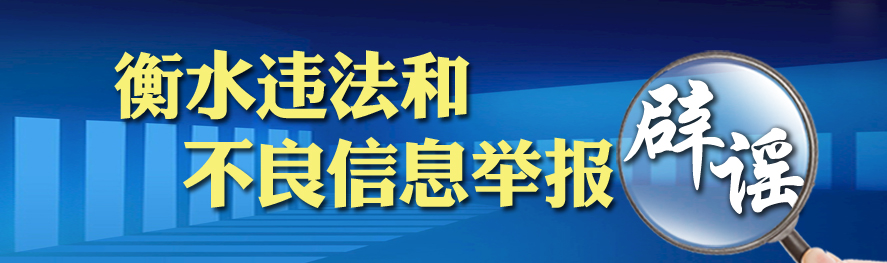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