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衡水市区一间工作室里,李红玉正用布满老茧的手指细细梳理苘麻纤维。案头狼毫笔的暗黄色麻胎,承载着“北国笔乡”数百年的制笔记忆,也见证着这位青年匠人让百年“侯笔”重焕生机的不懈追求。


“侯笔”自明代永乐年间起在衡水侯店村代代相传,曾与“湖笔”齐名。鼎盛时期,村里半数以上人家以制笔为业,年出口量达300多万支。然而,由于制笔技艺学成需3至5年,且初期收入有限,愿意潜心学习这门手艺的年轻人日渐稀少,如今能完整制作麻胎毛笔的手艺人已屈指可数。
“老辈人总念叨,这吃饭的本事怕是要断了。”李红玉听着外公、老匠人王丙强的叹息,回想起儿时看家人制笔的场景,于2016年作出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当时19岁的她,放弃在省城的化妆师工作,回到家乡跟随外公从头学起,重拾家族这门制笔技艺。

“以前觉得制作化妆刷工序繁琐,没想到毛笔制作更为复杂。”李红玉坦言,“工厂生产化妆刷要七八道工序,而制作一支毛笔却要经过八十多道工序。”村里年轻人大多不愿涉足这一领域,王丙强曾带过10个徒弟,只有李红玉坚持了下来。19岁起步在这个行业已属“晚学”,她还选择了北方鲜有女性参与的“水盆”工序——这是制笔过程中最关键,也是最辛苦的环节。

初学阶段,“掰手弄麻”就让她吃尽了苦头。左手四指要用木夹板固定成直角,压平掌纹才能在梳麻时不被扎伤。“每天左手肿得像馒头,夜里疼得睡不着觉。”但李红玉深知,麻胎是“侯笔”的灵魂所在,“过不了这关,就做不出有筋骨的笔”。

在她看来,麻胎毛笔的精妙之处在于“刚柔相济”:苘麻是“骨”,动物毛是“肉”,二者的配比需像老中医抓药般精准。“北方气候干燥,苘麻处理后不易变形,笔锋才能保持挺括,这是‘侯笔’能在北方立足的根本原因。”


为让老手艺跟上时代步伐,李红玉六次前往湖州、北京,向非遗传承人请教,带回30多本典籍潜心钻研,经过上百次试验,调整毛料配比。“现在纸张种类多了,笔也得随之变化。”生宣吸水性强,她就多加苘麻以增强笔的韧劲;熟宣偏滑,她就少放麻让笔锋更柔顺。每支笔出厂前,她都要在特制试笔纸上写满三行小楷,“笔锋弹不弹、蓄墨够不够,是骗不了人的”。这份较真劲儿,让她制作的毛笔逐渐走出国门,远销日本、韩国。但李红玉并不满足:“手艺若只藏在作坊里,早晚得被遗忘。”
2023年,李红玉开始学习拍摄短视频、开启直播。在镜头前,她举着麻胎向网友展示:“这暗黄色才是好料,是苘麻经石灰水浸泡,阳光晾晒后的自然色泽,能保存几十年不变形。”工作台虽布景简单,但她的直播常常吸引数千人同时在线观看,月销售额达4万元。
她还开展“非遗+研学”活动,接待数百名青少年体验梳麻、扎笔等环节。“孩子们问为啥非要用麻,我就告诉他们,这是老祖宗的智慧——麻让笔耐用,就像做人得先立住‘骨’。”在她心中,传承不仅是传授手艺,更是传播文化,对材料的尊重,对工序的敬畏,比手艺本身更重要。
外公王丙强起初不理解孙女对着手机“吆喝”,直到看到发往各地的快递单,才笑着感慨:“这孩子,是真懂这门手艺了。”
如今,工作室里的订单标签日益密集,美国、东南亚、新加坡等地的订单不断。夕阳下,李红玉轻抚新做好的毛笔,笔锋在光中泛着温润的光泽。“想让‘侯笔’成为能代表中国的国际品牌。”这位年轻匠人,正以青春之力,让百年老手艺在坚守中焕发新的活力,续写新的篇章。
视频 王天祥








 广告
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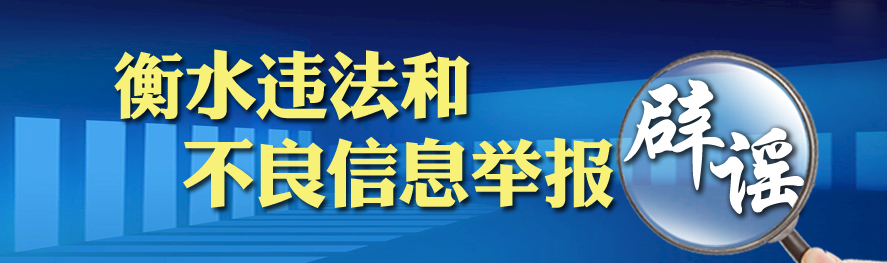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