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单位放了三天假,假期的第二天,天刚刚亮,我便蹬上自行车,向城外骑去。
“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今年的端午节和芒种相邻,地里的小麦已经成熟。乡路两旁的麦田里已经有联合收割机在收麦子了。我来到一块正在收割的麦田地头上,饶有兴致地驻足观看,麦浪滚滚,一望无垠,收割机奔驰在麦田里,就像一把大号的理发推子,转眼功夫,把田野推平,颗粒归仓。
看着眼前这丰收的一幕,我不由想起小时候在农村老家收麦的情景。那时,凌晨三四点钟,全家人就拿着镰刀,来到地里。壮劳力六个垄,孩子四个垄,太小的孩童也不能闲着,分一两个垄,大家排好兵布好阵,开始割麦子。两三个人一组,割得快的在前边用两绺麦子打个结,放在地上,当作捆麦子的腰绳。后面的人割了麦子都放到这个腰绳上,最后捆成大小适中的麦个子。
一开始割,太阳还没有出来,天不热,人也有劲儿。大人孩童都低着头哈着腰,脊背朝天,挥舞着镰刀,麦子一片一片地倒下,身后留下一个又一个的麦个子。到了六七点钟,太阳就发挥了威力,越来越晒,汗水已经湿透了衣裳。但再热也不能脱衣裳,必须长衣长裤,不是割麦子要有仪式感,而是但凡身体露在外面的地方,都会被麦芒扎得一片红。到了八九点钟,太阳已经很高了,天气越来越热,“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形象地描绘了割麦时的场景。割到一个节点上,上了年纪的大人回家套牲口车。其余人仍然继续割麦子。等牲口车来到,大家一起将刚收割的麦个子装到车上,拉到场院里卸车、晾晒。
“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人们简单地在地里树荫下吃罢饭,接下来就是翻场晾晒。太阳越毒,天越热,越要勤翻动麦子,好让麦子快些干透。麦子干透了,再套上牲口,拉上碌碡,在麦子上一圈又一圈地转着轧场,目的是为了让麦粒从麦穗上脱落下来。等轧得麦穗上的麦粒全部脱落,就拾场。将被辗轧过的麦穗用木杈抖抖,再挑到场院边上,堆成麦秸垛。麦粒就留在地上了。看到地上的一层麦粒子,人们也欣喜起来,好像忘记了劳累。有的拿木锨,有的拿扫帚,大家齐心协力把麦粒堆成一堆。这时的麦粒麦糠掺杂在一起,还要通过扬场把麦粒和麦糠分离。扬场就是用木锨把麦粒和麦糠抛向高空,借助风力,把麦糠吹到一边。这个活儿需要技巧,既要让风把麦糠吹走,还要让麦粒落成一堆。就这样一锨一锨地扬啊扬,颗粒饱满的麦粒越堆越多,麦粒堆越堆越大。扬完场,装口袋,拉回家。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收麦子就用上了割晒机和脱粒机等简单的农机了,比起原来麦熟,收麦时间缩短了,大约一周,麦子就全部入了囤。劳动强度大大降低,劳动效率成倍提高,但仍然很累人。
联合收割机的轰鸣,把我的思绪拉回了现实。我和收麦的老农攀谈起来。现在的农民不仅不用交公粮,国家还给了很多补贴,与“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的古代农夫境遇有了天壤之别。
年年收麦,今又收麦,随着时代的发展,割麦子的方式也在不断进步更迭,原来繁重的收麦情景,已经成为记忆。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发展,我们的生活一定会越来越美好。
作者:张大龙 编辑:李耀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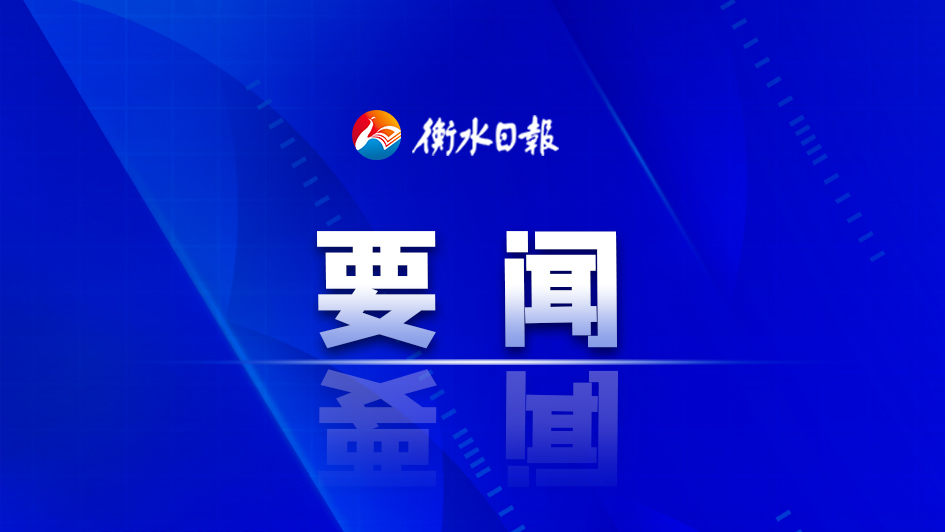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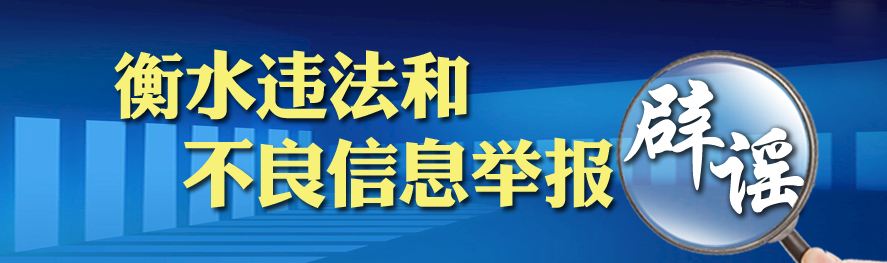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