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小学的时候,我就读过孙犁先生的课文《荷花淀》,他描绘的“女人坐在小院当中,手指上缠绞着柔滑修长的苇眉子。苇眉子又薄又细,在她怀里跳跃着;水生媳妇和几名妇女,为给丈夫送衣服,在荷花淀遇上鬼子,她们巧妙地把船驶入水浅处,使鬼子陷入伏击圈;那宽厚的大荷叶下面,有一个人脸,下半截身子长在水里。荷花变成人了?那不是我们的水生吗?又往左右看去,不久各人找到丈夫的脸,啊!原来是他们……”这活灵活现的写法让人无法忘怀。
因这永不消逝的课文情结,拜望孙犁故居的念头,也一直在我心中萦绕。今年5月27日,这一愿望终得实现。在这个鲜花铺满大地的季节,我随团驱车去了安平县孙遥城村。
眼前这阔大的青砖院落,于2014年翻新重建。黑大门、高台阶,门楣上,有莫言手书的“孙犁故居”四字。在孙家门前,我并不觉陌生,有那么一刹那竟陷入了遐想。想那久远年代,大门开合之际,闪出一张少年清秀的脸。他在此领略了人生之初的温暖亲情,青布长衫从这个门里走出来,走向那露珠清亮的田野,走向梦和远方,从此,归来是游子。
进大门,迎面是影壁,影壁前一小池,灌满了水,铺满了大片大片的荷叶。我们都觉得,这小池就是该种荷花。孙犁生活的地方,怎么能缺荷花呢?灵魂被荷花香透的人,才会对荷有那么深重的情思。
这座院落,为上世纪30年代北方民居建筑风格:四合院布局,外院套内院。外院有佣工房、牲口房、磨房、门房、大车棚、大门、二门。从样式风挌、从布局到摆设,真正还原了它当时的场景。在外院建有孙犁著作碑林,包括《荷花淀》《风云初记》《铁木前传》《津门小集》《芸斋小说》等孙犁先生的代表作品,让人感叹孙犁先生的创作之丰富、著作之经典。院内空地里种几畦菜,正鲜嫩的小葱、韭菜,在阳光里如半院翡翠。进内院,亦有影壁,影壁后植了竹子,绿叶葱葱,随风舞动,风声竹喧,一派雅重。
北望,正房三间两跨,东西各有厢房。正屋前,一棵槐树,满树绿意葱茏,在阳光的映照下绿得发光;月季花五颜六色迎风绽放。
我们听着讲解员的讲解和安平县文联主席王彦博的介绍,了解到孙犁先生好多鲜为人知的故事。中学时,孙犁开始尝试写作,取笔名“孙芸夫”。1938年参加抗日战争后,又名孙犁。“芸”通“耘”,“犁”为耕耘工具,而他的书房,名曰“耕堂”,皆取意耕种劳作。孙犁的心,时时刻刻都紧紧联结着他的土地。他说:“对于我,如果说也有幸福的年代,那就是在农村度过的童年。”孙犁特别爱读书。这是从幼年养成的积习,从小学开始,孙犁就读《封神演义》和《红楼梦》;上高小,开始读新文学作品和新杂志;中学六年,集中精力读文艺作品、政治经济学等,失业村居时,他订了《大公报》,经常学习,有时坐在柴草上读。他这种学习精神,为他以后的写作奠定了基础。看着屋顶棚糊的《大公报》、“耕堂”里摆放的孙犁先生的写字桌,桌上有老式蓝色方格稿纸、黑色钢笔、黑框眼镜、小收音机,桌旁放的那把藤椅,我想他撰写的《风云初记》《铁木前传》《津门小集》等,返乡时,在“耕堂”里写作的过程可能会有的。
他生活简朴,善待家人。他的卧室里,一盘土炕占据了一半空间。炕上铺着老家织布的炕单,单子上遍布蓝白相间的格子,是乡村常见的那种粗朴的织物。炕中央的小桌,幽幽承载着窗外的天光,寂寞的,没有人团坐合围。
北墙镜框里的老照片,是孙犁在不同年代跟家人的合影:他清丽的妻子,他灵秀的一子三女。孙犁的妻子,是邻村王氏女子。北方人信一句老话“女大三,抱金砖”,在家人主张下,孙犁与大他三岁的王姑娘结为夫妻。婚后,他来往于北平、保定等地谋事,夫妻一向聚少离多。1949年,孙犁落户于天津工作,才把妻儿接到身边,并为妻取名“王小立”。40年岁月共度,孙犁对妻子由衷感激,称她“知足乐命,安于淡素”。
孙犁对家人,一向温煦。他写作常熬夜到凌晨一两点,临睡前,总会去老母亲的屋子看一下,轻轻推门,悄悄看看,掖掖被角。母亲爱吃鱼,孙犁就拣中段儿夹到她碗里。孙犁写过,母亲和妻子是他文学语言的源泉。劳动妇女的质朴美德,奠定了他早期作品的基调,使他在走进繁华的城市后,还联结着冀中平原的地气。
照片下面的柜子里,陈列着孙犁先生的一些旧物。棉袄、帽子、毛毯以及被铁凝写在文章里的蓝色旧套袖……那套专为赴莫斯科访问做的衣服,仍显得新簇簇的。王彦博主席动情地说:“他就出国时穿了那么一次。”孙犁,一向是朴素的,朴素如庄户人家的读书人。
孙犁深知自己的个性,他曾写:“余性僻,疏于友道,然与青年相处之,有情者则终生念念不忘。”对于文学后辈,他总是尽力扶持,抱有火一般的热情。1979年,铁凝写了《灶火的故事》,接连遭受退稿。铁凝不泄气,将小说寄给了孙犁,没想到很快在《天津日报》的《文艺》增刊上刊发了。铁凝说,是孙犁点亮了自己心中的文学灯火,而孙犁,就是那位提灯的宽厚长者。
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孙犁先生对青年作家的发现与提掖是少有人比肩的,他曾扶持刘绍棠、铁凝、贾平凹、莫言等人,使他们成为享誉中外的著名作家,这一切,源于他锐利的眼光。他去世后,很多作家写文悼念他。铁凝在《怀念孙犁先生》一文中写道:我第四次与孙犁先生见面是2001年10月16日。病床上的孙犁先生已是半昏迷状态,他的身材不再高大,他那双目光温厚、很少朝你直视的眼睛也几近失明。但是当我握住他微凉的瘦弱的手,孙晓玲(孙犁女儿)告诉他“铁凝看您来了”,孙犁先生竟很快做出了反应。他紧握住我的手高声说:“你好吧?我们很久没有见面了!”他那洪亮的声音与他的病体形成的巨大反差,让在场的人十分惊异。我想眼前这位老人是要倾尽心力才能发出这么洪亮的声音的,这真挚的问候让我这个晚辈又难过,又觉得担待不起。在四五分钟的时间里,我也大声说了一些问候的话,孙犁先生的嘴唇一直嚅动着,却没有人能知道他在说什么。在他身上,盖有一床蓝底儿小红花的薄棉被,这不是医院的寝具,一定是家人为他缝制的吧,真的棉布里絮着真的棉花,仿佛孙犁先生仍然亲近着人间的烟火,也使呆板的病房变得温暖。直至2002年7月11日孙犁先生逝世,我经常想起孙犁先生在病床上高声对我说的话“大道低回——”我耳畔似乎听到孙犁先生的呼喊声,耳闻目睹,真正悟透了,孙犁先生晚年书屋里,挂着他为慰勉自己亲笔书写的“大道低回”匾额的真正内涵。是啊,人生的道路是曲折的,尝尽酸甜苦辣而归于淡泊,淡泊而宁静,宁静以致远。时近黄昏,金灿灿的阳光给孙犁先生老宅披上金色的外衣……
作者:徐朝 编辑:李耀荣








 广告
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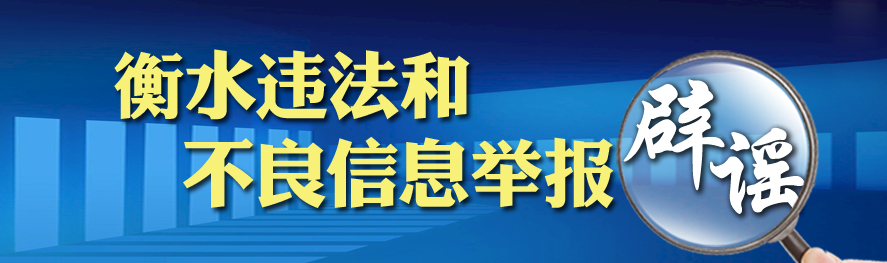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