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古今诗词,最爱毛泽东的华章丽句。所以存过十几种版本的《毛泽东诗词》。
最近翻腾旧书,找到十年前董春恒赠我的两部《毛泽东诗词鉴赏本》,不禁想到很多往事。
董春恒当年算是饶阳县城一个人物。
他是西南街农民,曾任村公安员和民兵连长。他家和旧县委几乎对门,又是城中村的场面人物,所以与县里干部们通常称兄道弟。他的父亲是民国时期闻名的“圣林馆”掌柜董圣林,所以与年岁较大的上层人士多有渊源。
老董书画俱精,也通文字。他的水墨画和诗文上过报刊,笔名“董天”。文革中,县城的伟人像、语录牌和大标语多出他手。他说:“现在写稿没稿费,画画写字有用处。”我们相识以后,每逢喝酒他总抢着掏钱。我有时付账,他就说:“你一个月才三十多,我比你来钱快!县委会议室的一百多把椅子,叫我用黄漆写字,十块钱包干,我半天就完活!这种事哪个部门也抢着找咱。”现在人们常说“文化产业”一词,我想老董无愧先知先觉。
老董天生“高干范儿”。他风度潇洒,宽额俊目,加上口才出众,话语滔滔,站在什么场合,总令人刮目相看。1976年,省里办学大寨展览,衡水只有饶阳安平两个县。县委十分重视,派农林局副局长李老、老董和我赴石筹展,明确由李局负责。但初次和展览馆领导接洽,馆长即认为是老董带队。我们的分工是李局照相,老董美工,由我撰写展览大纲和版词。因只有定下大纲才能照相和设计,前期多讨论大纲。我说想法之后,展馆领导总来一句“老董再说说”,所以李局有些不爽,会下就训老董:“别瞎喳喳!”老董就笑:“我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老董性格开朗,人缘好,自来熟。每天回到宾馆,就给服务员讲故事。他讲的都是自己家事,却像章回评书,如父亲厨艺,女儿趣事,爱人家庭,婚恋经过等等,都说得妙趣横生。只要一讲,三层楼的服务员都跑来听。
老董讲的最多且引为骄傲的,是他的婚姻奇缘。他爱人是北京知青,教授之女,上小学时还有给毛主席献花之荣。到西南街插队后因倾慕老董才华下嫁,比他小了十多岁。每当讲到这里,服务员们就起哄:“你不该叫董天,你该叫董永!”
老董确实聪慧过人,才艺不凡。有次与我上过街横桥时,突然站住向下一指说:“你看那个拉粪车的姑娘多漂亮。”看我没答话,又强调说:“咱来石家庄俩月,这是我看到的最漂亮的姑娘。那些讲解员谁也比不上。”当时二十二个参展县都选一名讲解员在石培训。回到宾馆,他拿出画笔“刷刷”几下就把拉粪姑娘画出,接着又画饶阳那个讲解员,然后有鼻有眼点评优劣。李局笑着说:“你也不怕挨骂!”他却说:“这是艺术,是审美。明天我给他们都画幅速写,她们都得谢我!”
唐山地震时,我与老董正在石家庄。那几天不通车,牵挂家里也回不去,他就劝我:“咱家估计没事儿。”晩上看我闷闷不乐,就说:“我给你唱戏吧。”他文革前在剧团画过布景,对排过的剧目都耳熟能祥。那天他躺在床上唱全本《蝴蝶杯》,男女角的唱腔对白,夹杂着丝弦鼓点,连唱带喊,有滋有味儿。我问他上没上过台,他说:“临时缺人演过一次大兵,刚上去被人一脚踹倒就算完戏。”
老董处事看似有些“油”,但待人却很真诚。他常说:“我对孬人用孬法,对好人讲义气。”展览结束后,他叫我到家吃饭,那是我唯一一次到他家,也见到了曾给毛主席献过花的嫂子。那天喝着酒,他说自己会相面,并对我说:“你搞文字是好手,当官不行——太面善。”还说了一句话叫我很感动:“你结婚时,县委要安排不了宿舍,就来住我的东屋。别人想租,一月五块。老弟要住,分文不取!”那时县直干部确有不少在他们村租房。
落实政策时,老董的爱人迁户回京,继承两套房产。那时老董已是物资局的经理,也办理退休随迁京城。他是艺多不压身的人,到了京城立即混得风生水起,在社区老年大学教授书画,听说那些学员不少都是高级干部和知识分子。
2005年,我在《中华散文》发表一篇散文《好吃不过饺子》,恰叫爱读书的老董看到。他托赴京的亲戚给我捎来一斤虾皮,并在信中说:“看了你的文章,知道你爱吃拌小虾的瓜馅饺子。这是朋友刚送的,绝对新鲜……”
2011年的一天,他突然来一电话,说自己在饶阳的皇都豪庭小区买了房子,现已入住。因之前一无所知,我十分惊喜,想去看他。他说:“我现在腿脚不好,不能下楼,要能动我早去找你了。”我问他缺什么,他说:“听说你出了书,给我找几本,就是闷得难受!”
那次去看他,老董很郑重地赠我两本《毛泽东诗词鉴赏》。一本扉页写的是“明年是您的本命年,望著作日丰、长寿”,一本签的是“知弟喜诗文,遍寻鉴赏本。来年逢花甲,籍此祝寿辰。”签字都谦称“小兄董春恒”,还注明“2011年返乡养老第六日4.26”。看来是早就给我准备好的礼物。
我们分别二十余年,平时也很少联系,但老董不仅记得我的岁数,而且知道我的爱好,甚至“遍寻”我喜欢的书籍相赠。细细想来,茫茫人海之中,能有如此之举的真是廖若晨星。他没求我办过任何事情,即使索书也只有那一次。虽然后来我又给他送过两次杂书,但不久他即因病过世了。
我搞过通讯报道,宣传过一些人,写过散文诗词,也颂扬过不少人。但翻看旧书,突然想到却没给老董写过一字。所以忆旧如上,略偿心债。
作者:何同桂 编辑:李耀荣






 广告
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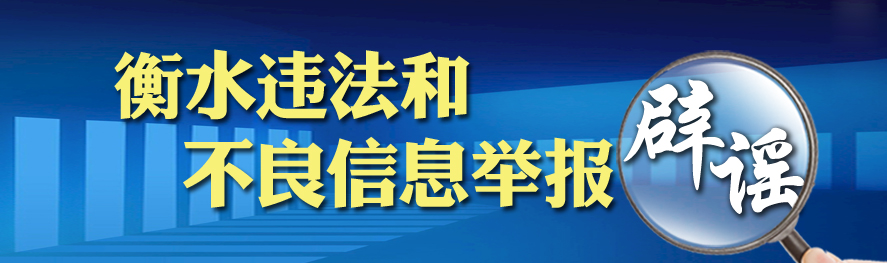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