弓汝恒是清末深州大儒,桐城宗师吴汝纶(1840-1903)“著籍最蚤”的开山弟子,一生从事著述教育。他治家有道,待客有礼,“群从少长以次序立”,吴汝纶见而叹异不已,以为“政行于家”。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就建立他家中,第一任支部书记弓仲韬为其文孙,其他党员多为弓氏子弟。
这样一位重要的人物,然见于文献资料甚少,今人介绍文章多付阙如,或语焉不详,甚而讹误百出。整理这位乡邦前贤史实之志久存于心,近来因为编撰《衡水地区吴门弟子考略》一书,弓汝恒基本史迹不可或缺,遂潜心发力,广事搜求,得相关历史讯息百条以上,然用度之大,也为近年来所少见。
《吴汝纶全集》收录弓汝恒信札三通,《弓斐葊墓表》文一篇;《吴北江文集》有《书隐先生传》《故友录·弓汝恒》文章两篇,其他提及弓汝恒者见于《先府君行述》等多处;《北江先生诗集》收有《送弓子贞》诗一首;刘声木撰《桐城文学渊源考》收弓汝恒介绍两条,《桐城文学撰述考》著述一条;《深州风土记》涉及弓汝恒条目多达数十条,尤以金石卷及知州朱璋达、曹景郕序文为多,其他人谱、荐绅、艺文各卷也不在少数;弓汝恒挚友,明清八家殿军贺涛(1849~1912)之子贺葆真《收愚斋日记》近年句读整理出版,粗粗浏览至弓汝恒逝世年月,已得十二条。
为人作传首重谱系,故先从弓氏家族说起。
一、世业耕读
弓汝恒,字子贞,号书隐,世称书隐先生,深州直隶州安平县台城里人。
据吴汝纶撰《深州风土记》人谱所载,始祖弓彦通、弓亨通于永乐二年由灵石晋水村迁来,弓彦通居台城,占荒三百亩。弓亨通别居庄科头。
弓彦通生弓广,弓广生弓海,弓海生弓胜,弓胜生弓忠,弓忠生弓世铉,弓世铉生弓稳,弓稳生二子弓厚、弓佐。弓厚生弓维国,弓维国,廪生。弓维国生弓射斗,弓射斗,字诣薇,顺治岁贡生。弓射斗生弓旌,弓旌字征贤,生员。弓旌生弓斯张,弓斯张字子壮,候选州同。弓斯张生二子弓开元、弓作霖。弓开元字仲伯,雍正岁贡生。弓作霖,武生员。弓开元生弓裔昌,弓裔昌,监生。
弓稳次子弓佐,生三子弓正国、弓匡国、弓襄国。
弓正国字敷四,武生员。弓正国生弓调矢。弓调矢生弓弬,弓弬字际盛,赠武略骑尉。弓弬生弓扬休,弓扬休字美公,监生。弓扬休生弓炳翼,弓炳翼字御青,乾隆岁贡生。弓炳翼生弓允升,弓允升字登庸,候选州同知,道光七年施谷三百石,赈灾饥民,安平县令彭定泽旌表其闾。弓允升生弓省度,弓省度字巡南,贡生,候选教谕。弓省度生三子弓毓华、弓摛华、弓润华。弓摛华字斐葊,贡生,赏五品衔。
《弓斐葊墓表》称“君少孤废学,学治生,以资使兄弟学。兄弟学皆成立,为诸生,有声学官,而君以一身生聚衣食百余口者五十年”……
君讳某,字斐葊,安平弓氏,尝以饥岁赈灾民有劳,由贡生加五品衔,卒于光绪甲午十月十日,年七十有三。曾祖炳翼、祖允升、父省度,世以儒为业。君娶王氏,继娶吴氏、赵氏。男四人,长者汝恒,汝恒生均,皆副榜贡生。其余孙三人,曾孙二人。汝恒、均先后从余问学”。可知弓斐葊生于1822年,卒于1894年。弓摛华娶妻王氏,生汝恒、汝直、汝恂三子,后续娶吴氏生子汝恩,又娶赵氏生子汝纶。弓汝恒三弟弓汝恂,字季农,生员,也就是安平县附学生员。弓汝直为捻军掠走,未记入墓表当中。
弓汝恒生弓均、弓堪,弓堪子弓仲韬(1886—1964)。曾祖弓摛华去世时,弓仲韬已经九岁,即“曾孙二人”之一。“汝恒生均,皆副榜贡生”,“汝恒、均先后从余问学”,弓均字次崔,也是吴汝纶主讲莲池书院时门人,从师受古文法,光绪二十年副榜贡生。弓汝恒叔父弓润华之子弓汝勤,字子钊者也是吴汝纶主讲莲池书院时弟子。
二、为学笃敬,能成专门之业
弓汝恒考中同治甲子(1864)副榜贡生。同治十年(1871)六月初九,吴汝纶到达深州治所,十日接篆视事,行知州事。深州旧有义学二百四十五所,学田多被有财势、不守法度、凌压贫困百姓的豪民侵占,吴汝纶清查后限期退还,他认为义学是“上务其名,民私其利”【吴汝纶全集·(四)贺涛《吴先生行状》(1139页)】,毅然废除义学,将收回学田一千多四百多亩划归文瑞书院。又为书院设法追回二十多年的欠账白银五千两,广置书籍,选拔一州三县(深州、武强县、饶阳县、安平县)的高材生入书院读书,供给颇丰,吴汝纶到书院“亲教课之,民忘其吏,推为大师”【《清史稿·吴汝纶传》】。弓汝恒被吴汝纶的学养折服,拜在门下,弓汝恒仅小吴汝纶二岁,是吴收的第一个弟子。
同治十年直隶总督李鸿章上奏朝廷,请求专设修志局,重修《畿辅通志》,遂在莲池书院设立修志总局,延聘翰林院编修、莲池书院山长黄彭年(1823—1890)担任总纂,主持编修。随后又令各州县修志备览,吴汝纶奉檄纂修州志,并亲制采访条例十六则,弓汝恒、张廷祯、贺锡珊协助编修。
吴汝纶因其父吴元甲于同治十二年三月十四日逝世于深州官舍,丁忧去职。
后吴汝纶到天津入李鸿章幕府,弓汝恒受深州知州朱靖旬(1834-1895)命追随在侧,协助纂修,光绪六年吴汝纶任冀州知州,弓汝恒在冀州设修志局,继续佐修。第二年朱靖旬任保定知府,撤修志局。十年后深州知州熊寿篯再置修志局于吴汝纶任山长的莲池书院,后又撤局,光绪二十五年(1899),朱璋达任知州复开局修纂,第二年吴汝纶逃命避难于深州,终于完成,编完后在文瑞书院刊刻。因为该志没有绘图,中间吴汝纶虽然历尽曲折聘请李善兰入室弟子熊方柏、杜溯周前来测绘,而时任知州皆不能用之,只得名以《深州风土记》。
《深州风土记》共二十二卷,是清代方志中的佳作,吴汝纶曾以“字字有本,篇篇成文”自许,创立“人谱”一门,广征谱牒及史籍文献,梳理望族大姓的演变,为我们今天研究弓氏家族留下了难能可贵的文献资料。弓汝恒近三十年赞助修志,“每一编脱手,珍重弆藏,视同性命,至亲密友求一寓目不可得”,唯一得见手稿的是老友贺涛哲嗣贺葆真,因为二人同有舆地研究的爱好,珍惜异常,其他人则谁也不敢借予,“数十年守护不怠”,“书局屡辍屡兴,卒得刊刻行世,不中道废坠,稿本不零落散失”,都是弓汝恒“保持之力”【《吴北江文集》·故友录·弓汝恒】。莲池书院修志局是他鸠工刻版,后又将书版拉回深州文瑞书院,修版续雕,今日所见《深州风土记》刻工风格不一,正因此也。
《桐城文学渊源考》说他“师事吴汝纶,受古文法,佐修《深州风土记》,遂尽弃他书,专心舆地之学三十年,贯穴经传,撰《古今地理沿革表》六十四卷”,补遗中说他“在张吴弟子中年最长,好考据辞章之学,其文蹈厉腾倬,甚雄而劲。吴汝纶撰《深州风土记》,汝恒为之具资材”。
《桐城文学撰述考》总其著述为以下几种:古今地理沿革表六十四卷、古碑文字考二卷、古今异音考一卷、说文古今异文考四卷、前汉辑要五卷、所好集九卷、闲闲录六卷。《古今地理沿革表》六十四卷,弓汝恒用力最勤,前后五易其稿。吴汝纶盛赞他道“门下能为专家之业者,惟子贞一人”。其著述今都散落民间,无一存者。前些年我曾在古玩市场见《古今地理沿革表》残本,朱墨套印,以不识弓子贞为谁,竟弃置不取,今日想来顿足捶胸,自掴面颊,不足泄恨!
弓汝恒除协助其师修志外,为革新深州教育出力不少。《吴汝纶全集·尺牍》收录给弓汝恒信札三通,其一为壬辰年(1892年)四月二十七日,题为《与弓子贞》。当时吴汝纶已任莲池山长,该信主要说明《深州志·金石卷》元代以前已经基本定稿,明代以后五百年间也要录入,让弓子贞找出抄录本寄去。尤其说明张江陵撰《柳林寺冯保碑》、《张伯良厘定差徭碑》两文为深州至大之文,如果录本没有收入,当遣人锤拓寄去。查《深州风土记》,柳林寺冯保碑是冯保其父冯汉神道碑。
第二封写于戊戌年(1898年)七月十日,题为《与弓子贞》,此时正处变法之际,吴汝纶说担心“西学未兴,而中学先废”,同时指出“国无转移风气为物望所归之人”,变法不会成功。对弓汝恒想去探望吴汝纶,“一倾积愫”,很是高兴,随后吴汝纶又为弓氏子孙开列应读书单。
第三封写于壬寅年(1902年)八月廿二日,题为《答弓子贞》,此时吴汝纶在日本考察学制,对于如何深州办学,吴汝纶答复弓汝恒等人,不能坐待,应该遍开小学堂,以旧时教法,加上算术课,至于“西学无师”,“暂置后图”。
三、为人至性,治家有道
弓汝恒少年时母亲王氏夫人去世,父亲还未续娶,弟弟妹妹幼小,啼哭不已,抚育重任由他担负起来,他把弟弟妹妹们抱在怀中、负于背上,终夜不睡,环走室内。
同治七年(1868),捻军过安平,他二弟弓汝直被卷走,弓汝恒悲痛哭嚎,只身入捻军营中六十天多天,遍寻不得,归家后,大病一场,从此一睡觉就长吁乱喊,终身没有痊愈。临死前交待在墓石刻上弟弟出生年月及被掠走时日,冀以弓汝直得脱,后人寻祖有验。弓摛华晚年腿脚不便,弓汝恒已年逾五旬,亲自左右扶持,不让子侄替代,曲尽为子之道。父亲去世后,弓汝恒持先父行状赴莲池书院,请恩师吴汝纶为作墓表,请同学张廷祯书丹,刻碑立于墓阡,雄文传世于今,以彰其父之德。自入吴汝纶门下,凡三十三年,笃诚守信,若家人父子。吴汝纶庚子避乱深州,亲至台城里弓家,弓家没有僮仆,“盥洗进食,帣韝鞠跽,皆子弟任之,待客彬彬然”,几位弟弟及子侄辈按次序侍立一旁,弓汝恒命退乃退,吴汝纶羡慕不已。吴汝纶到他住所,“诗书之气,薰染而不能去”。吴汝纶问他治家之道,弓汝恒云“此先子之所贻也”,归功其父。
吴汝纶独子吴闿生(1879—1949年),虽小弓汝恒三十七岁,二人相交甚契,庚子乱时,吴闿生拜访弓汝恒后作《书隐先生传》云其室“萧然一榻,图书满架,不知世变之亟也,自题其室曰书隐庐”,可见其高古之风。
另据范丹凝硕士论文《贺涛与清末畿辅文化圈》82页注,有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弓汝恒与吴闿生“赙金不受”一段轶闻,云弓汝恒困顿乡里,吴闿生赠以重金。弓汝恒坚却不受,往来之际,竟成意气,几致绝交。贺涛斡旋调其中,函中“执事尝怪辟疆以常人相待”,贺涛劝弓汝恒“以全交谊”,接受馈金,有“小廉曲谨,君子弗尚,即有时却馈不受,亦当视其人之交何如,其馈,我知情义如何不能”等语。查《贺葆真日记》,则此事范丹凝硕士略有曲解,日记十六·光绪三十一年六月二日(1905.7.4)记曰“弓子贞先生来。先生著书家居,未尝奔走于世,以干利禄。此次来保,访辟疆与吾父也,即馆于辟疆”。七月十六日(1905.8.16)记曰:“弓子贞来函,却辟疆之馈,子贞之来保定也,辟疆以百金相馈,谢不受。龂龂久之,词色俱利(厉),吾父为和解之,卒不能决,故既归而来函却之也”。贺涛作为吴门弟子桐城后期领袖,国人皆认为能继张裕钊、吴汝纶衣钵者,非其莫属,他当时在保定任直隶文学馆馆长,吴辟疆即吴闿生,当时在保定整理吴汝纶遗作,准备梓行。贺涛自幼与弓汝恒相交,二人最相友善,弓汝恒清贫自守,一则专心著述,再者即于深州从事教育革新工作,很少外出,只有赴莲池拜谒恩师之行,诚如贺葆真所言,“未尝奔走于世,以干利禄”。此次保定之行,我认为所谓访贺涛及吴闿生,是为整理先师遗著而来,所以有“即馆于辟疆”等语,吴闿生赠以百金,不是“赙金”,应该是酬谢弓汝恒整理文稿之托词。弓汝恒认为整理先师遗著乃分内之事,不要说整理一月,就是整理几年,也不能接受任何名义的馈金。二人后来如何言归于好,未见相关文献,但民国十三年时,吴闿生撰《故友录》长文追忆了已去世十年的弓汝恒。
四、简略年谱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生。
同治三年(1864年),二十三岁,参加顺天乡试,未中举,取为副榜贡生。
同治七年(1868年),二十七岁,捻军过安平,二弟弓汝直被卷走,弓汝恒只身入捻军营中六十余日,遍寻不得。
同治十年(1871年),三十岁,拜入吴汝纶门下,协修州志。
同治十一年(1872年),三十一岁,到安平河槽村魏氏宗祠拓《隋故蕲州刺史李君墓志》。
【后黄彭年修《畿辅通志》,命村人将志石送保定,绝爱之,宝蓄为己有,弓汝恒纠合深州士绅欲讼黄彭年,使归志石还安平。吴汝纶撰《深州风土记》詈骂黄彭年,实则二人均为一派宗师,各为宋学汉学之代表,何以致有泼妇骂街恶文,实学术之争延及政治而已。】
光绪元年(1875年),三十四岁,追随吴汝纶到天津入李鸿章幕府,协助纂修州志。
光绪六年(1880年),三十九岁,吴汝纶任冀州知州,在冀州设修志局,继续佐修州志。
光绪七年(1881年),四十岁,深州知州朱靖旬改任保定知府,撤修志局。
光绪九年(1883年),四十二岁,撰《诰授朝议大夫知深州事朱君惪政颂》。
光绪十二年(1886年),四十五岁,孙弓仲韬生。
光绪十七年(1891年),五十岁,深州知州熊寿篯再置修志局莲池书院,时吴汝纶任莲池山长,弓汝恒继续佐修州志,后撤修志局。
光绪十八年(1892年),五十一岁,四月二十七日吴汝纶致函弓汝恒,嘱其搜求明代以后五百年间深州金石文字。
光绪二十年(1894年),五十三岁,长子弓均参加顺天乡试,未中举,取为副榜贡生。父弓摛华去世。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五十五岁,至莲池书院拜谒吴汝纶,吴闿生赠《送弓子贞》诗云:“当筵何为忽不乐?骊歌顿向筵前作。当时寂寞颜不开,百求不获先生来。论诗说赋正未已,敝车羸马翻相催。先生抗心在曾左,去留随欲无不可。佻达年少难为徒,寂寞自怜还故我。病躯初愈健蹊牛,驯马可狎如江鸥。离绪万端归一送,挥鞭欲郤羲和流”。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五十六岁,腊月为子侄□□,迎娶武强贺子久之女。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五十七岁,二月五日到信都书院,请贺涛为伯父弓毓华撰写墓表,即《深州风土记》所载《萝村先生墓表》。
二月五日辞归,贺葆真借观州志稿,许之。
三月二十日,寄去人谱及明以来传记。
五月五日,贺葆真收到弓汝恒书信,并借其吴汝纶注《通鉴地理今释》。
七月十日,吴汝纶致函弓汝恒,言戊戌变法事及为弓氏子孙开列应读书单。
七月二十五日,贺涛在信都书院为诸生说《弓君斐葊墓表》。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五十八岁,三月十八日,贺葆真录毕深州志稿本和吴汝纶注《通鉴地理今释》,还弓汝恒。
是年深州知州朱璋达复开局修纂州志,弓汝恒在莲池鸠工开雕。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十八岁,吴汝纶避难深州,至台城里弓家。本年协助吴汝纶在深州义仓修志完毕,取回莲池雕板,在文瑞书院刊刻梓行。将吴汝纶为父亲撰写墓表刻石立于墓前。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五十九岁,吴汝纶保荐弓汝恒于护理直隶总督周馥。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六十岁,弓汝恒给在日本考察学制的吴汝纶去函请教深州如何办学,八月廿二日,吴汝纶复函云,不能坐待,应该遍开小学堂,以旧时教法,加上算术课,至于“西学无师”,“暂置后图”。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六十四岁,六月二日到保定,访吴闿生与贺涛,驻于吴闿生家中,整理吴汝纶遗著。
七月十六日,回安平后,致函贺涛。
民国元年(1912年),七十一岁,三月十五日贺涛去世。
四月初六日,悼贺涛挽联两副送达故城县郑口,其联为诸悼词中最痛者。
五月十一日,寄哭贺涛诗给贺葆真。
民国三年(1914)年十月卒,享年七十三岁。
韦冰注:年谱月日皆为农历。
记有弓汝恒相关事迹尚有赵衡《叙异斋文草》、贺涛《贺先生尺牍》《贺先生文集》、姚永朴《蜕私轩集》及《吴门弟子集》等书,皆为线装善本,均未句读整理出版,然善本善价,寒儒治史,此也无可奈何之事。常海成先生拍买《吴北江文集》六册,知我研究吴门弟子,借以寓目,方成此文。虽然其他善本尚未得见,以现有文献逆推,想来出入不会太大,补充完善而已。
作者:田卫冰 作者:贾亚楠

 广告
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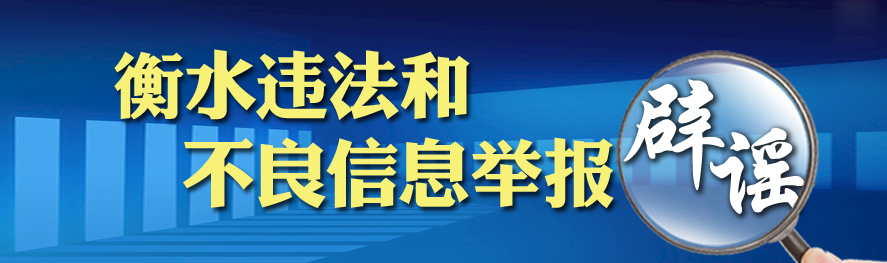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