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刘禹锡一句诗,奠定了洛阳牡丹的国花地位。其实牡丹故乡在菏泽,只是一则故事火了洛阳牡丹。
先说故事上篇。当初武则天一怒之下,将牡丹贬至洛阳,未曾想反倒是成就了她。可是话又说回来,在那个大雪纷飞的隆冬之夜,武皇醉笔写下诏书:明朝游上苑,火急报春知。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百花慑于此命,夜里竞相开放。只有牡丹敢于抗旨不遵,这样不媚上不唯权的底气,自然当得起国花之名。如此看来,到底还是她自己成就了自己。
牡丹在我国栽种培育的历史可上溯到南北朝时期,《嘉记录》《太平御览》等文献均有记载。至隋唐时已繁盛无比,蔚为大观。李白的《清平调》三首,即是借着描写形色各异的牡丹赞美杨玉环,从而取悦了明皇而得以专享高力士脱靴的尊荣。《龙城录》中记有一人:“洛人宋单父,字仲儒,善吟诗,亦能种艺术,凡牡丹变异千种,红白斗色,人亦不能知其术。上皇召至骊山,树花万本,色样各不同,赐金千余两。内人皆呼为“花师”,亦幻世之绝艺也。”此人没有李白的冲天才气,也便没有诗仙那样坎坷的求职经历。可他仅凭能种牡丹,就轻而易举地赢得了玄宗的青睐,被授予“大唐花师”的光荣称号,荣耀一生。
五年前的四月,我和爱人去洛阳赏牡丹。一出站口,满目鲜花着锦,一城焚香欲燃,每到一处,都教人神魂颠倒,如同饮了一盏“千红一窟”。纳罕之余查阅资料方知,如今牡丹的花色品种已不可胜数。仅从颜色一项试举几例,便可以感受到牡丹的美轮美奂。譬如醉酒杨妃、飞燕红妆、出水洛神、貂婵拜月、二乔、金屋娇等,几乎将古代美女囊括其中。最值得费一番笔墨者名绿珠坠玉楼。此牡丹洁如玉脂,每片花瓣的中间都有一颗碧斑,恰似绿珠坠入玉液琼浆之中,令人不由想起西晋美人绿珠姑娘。这牡丹简直美得不可方物,但是在我看来,这款命名却是残忍得很。绿珠姑娘自小才貌出众,卓然不群,在青春正好的年纪,被洛阳土豪石崇纳为爱妾,这几乎是她无法摆脱的命运。石崇能在史上留名,皆因他勇于和王恺斗富。石崇并非簪缨世家,在极其讲究门阀的魏晋很难出人头地。但他因为有钱,在追求及时行乐、穷奢极欲的晋代照样可以无限风光。这样一个依靠搜刮民脂民膏、聚敛财富的地方官员,除了借用绿珠的美貌来装点门面、夸豪竞奢之外,他会给到绿珠一丝一缕的精神之爱吗?绿珠姑娘长年禁锢在金谷园中,豢养如宠物,被恶俗男人玩弄于股掌之间,这可曾是她想要的生活呢?说这个史载“杀妓侑酒”、床边常备“肉屏风”“肉痰盂”的男人恶俗真是轻饶了他,绿珠一天天都在目睹着他的丑陋与罪恶,体味着他的卑鄙和暴虐,她怎么会像史家所述,为了表示对石崇的忠贞不渝,在孙秀闯进金谷园时而选择纵身一跃呢?我同意夏坚勇教授的解析,绿珠是因绝望而死。她的死“是一种解脱,也是一种抗争——向丑恶的男性世界的抗争。可惜这种抗争却被后人善意地曲解了,硬是给她树了一块‘殉情’的贞节牌坊”。“繁华事散逐香尘,流水无情草自春。日暮东风怨啼鸟,落花犹似堕楼人。”在所有吟咏这段往事的诗词中,杜牧《金谷园》于凄婉中发出了繁华易散的感慨,大约是最接近绿珠堕楼时孤绝悲凉的心境的。
将牡丹比作美人,诗词之中并不鲜见。可是借用牡丹的美来警省亡国之君,好像历史上仅有一例。宋僧惠洪《冷斋夜话》中讲了一则小故事。宋军大举南下,饮马长江。可是金陵城中后主李煜仍在赏月观花,诗酒歌舞。法眼禅师看到御苑中盛开的牡丹,作牡丹诗偈有句:发从今日白,花是去年红。何须待零落,然后始知空。无奈后主省悟不到花容难驻、娇艳不常的警示,依旧沉湎声色,苟且偷安,终至金陵城破,肉袒出降。身为亡国之君,囿于汴河一隅,追思当年的牡丹诗偈,后主的词自此得以从花前月下转入了故园山河。王国维《人间词话》: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国色天香的牡丹,借李煜之目助推了危如累卵的南唐小国的覆灭,同时也借李煜之手将词推入了一个更为深挚宏阔的境界。
再说故事下篇。刚强不屈的牡丹一到贬谪之地,便在洛阳烈火烹油般昂首怒放,无拘无束,无遮无拦。这更加激怒了武则天,她敕令用火烧死牡丹。翌年春天,枝干虽被烧焦的牡丹反而开得云蒸霞蔚,春色无限。武则天这才见识到牡丹的矢志不移,敬佩牡丹的焦骨刚心。而千百年来,无数诗人墨客的笔触只是停留在牡丹“形色香”的表面,这实在是风骨牡丹的悲哀。明代俞大猷《咏牡丹》:闲花眼底千千种,此种人间擅最奇。国色天香人咏尽,丹心独抱更谁知。俞大猷为明代抗倭名将,与戚继光并称“俞龙戚虎”。他的奇节与抱负也只有牡丹独守丹心差可比拟了吧。
行文至此,不得不说到《牡丹亭》了。“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无论何时听到这段《皂罗袍》,我都在大美中听闻出了大悲,那真是一种无可名状的情愫。“无可名言,但有惭愧。”作为写作之人,我不得不饱尝此种遗憾。但我也同样庆幸,这般神启似的感觉并不会光临世上的每一个人。
汤显祖是一个十足的理想主义者。他洁身自好,不谙世情,二十一岁中举之后婉拒权相拉拢,致使空负才名,屡试不第。万历十一年张居正死后,汤才子终以三十四岁高龄得中进士,到南京赋了八年闲职。万历十九年,他因目睹官僚腐败愤而上《论辅臣科臣疏》,触发圣怒而贬为地方小吏。在浙江遂昌,他“云钳剭,罢桁杨,减科条,省期会,建射堂,修书院”,劝农桑,施善政,使得浙中偏僻贫瘠之地大为改观。遇赦一年的他把这里看作了自己的理想王国。他为实施自己的政治主张一无顾忌,擅自释放狱中囚犯回家过年,准许他们元宵节陪同家人上街观灯。如此富于理想,怎能为官场所容?一旦政敌把柄在手,暗箭冷枪射来,理想破灭的汤才子即时溃不成军。那是万历二十六年,四十九岁的汤显祖一纸辞呈,扬长而去。他坐回家中窗前,将毕生理想化作锦绣文字,一笔一画,注入起死回生的情爱传奇之中,著成了戏剧史上“前无作者,后鲜来哲”的“玉茗堂四梦”。
《牡丹亭记题词》曰:“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有此一语,天下情爱尽矣。我写爱情故事,被读者僭称为“中国最会讲故事的痴情大叔”。差矣,窃以为,只有汤临川方可担得此名。
作者:贾九峰 编辑:李耀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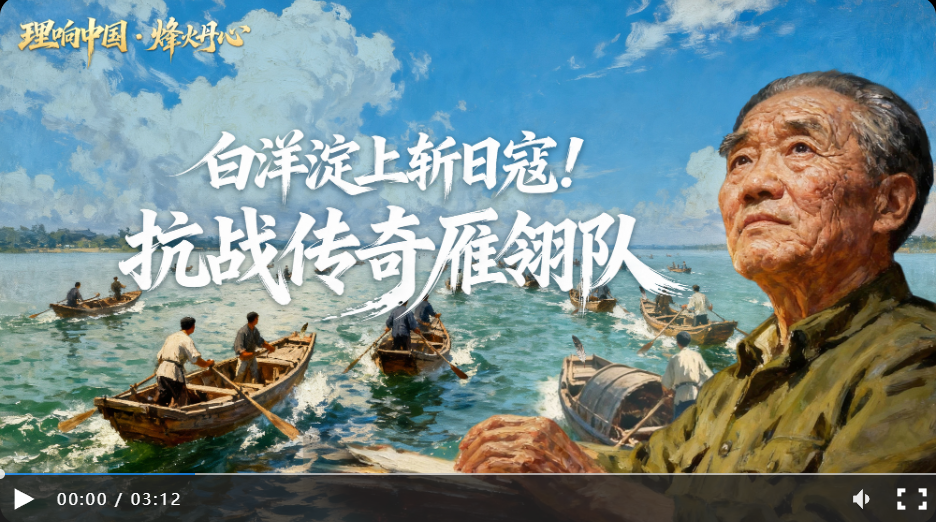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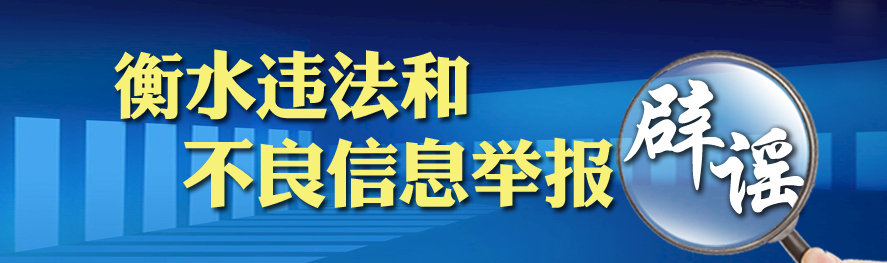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