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裂痕处照见永恒
——蔡崇达文学中的生命救赎图谱
本报记者 赵栋
蔡崇达的文字总带着咸涩的海风,如同闽南渔村斑驳的墙垣上剥落的灰泥,每一粒都裹挟着生命的盐分。从《皮囊》到《我人生最开始的好朋友》,这位执笔如执刀的作家,始终在用文学的X光机扫描现代人精神骨骼的裂隙,在看似破碎的生命图景中拼凑完整的灵魂版图。
《皮囊》中“肉体是拿来用的”宣言,实则是蔡崇达解构生命认知的手术刀。当瘫痪的父亲在咸腥海风中逐渐透明,当阿太用枯枝般的手掌叩击自己的棺木,作者撕开了附着在肉体上的世俗价值体系。这种近乎残酷的祛魅,在《草民》里化作老渔民被海水泡发的伤口——那些与风暴搏斗留下的疤痕,既是生命韧性的刻度,也是存在本质的隐喻。
命运在蔡崇达笔下从来不是宿命的囚笼,而是充满张力的谈判场。《命运》中神婆给出的答案,与其说是对神谕的盲从,不如说是凡人与宿命博弈的智慧。就像闽南渔民既虔诚叩拜又毅然驶向风暴,这种“信而不迷”的生存哲学,构成了作家独特的命运观:真正的勇者,是在看清生命局限后依然选择纵身跃入激流。蔡崇达揭示了一个真相——生命正是在不断的破碎与重组中走向丰盈。
蔡崇达建造的文学祠堂里,神性与烟火气从来不是对立的两极。
《皮囊》中母亲执念修建的房屋,《命运》里缭绕香火中窥见的生死,都在消解崇高与庸常的界限。菜市场的讨价还价声可以成为存在主义的思辨现场,葬礼上的哭丧调里藏着最本真的生命顿悟。当现代文明将人物化为数据洪流中的微粒时,蔡崇达的文字始终在为每个生命个体举行隐秘的加冕礼。
在这个意义不断蒸发的时代,蔡崇达的创作像闽南老厝天井蓄满的雨水,倒映着被霓虹遮蔽的星空。从《皮囊》到新作《我人生最开始的好朋友》,他始终在练习一种文学修复术——用记忆的陶土黏合现实的裂缝,让那些被时代撞碎的灵魂,在文字的慢火煨炖中重新获得完整的形状。我们终于读懂贯穿作家所有作品的密码:生命的救赎不在彼岸,而在我们拾捡命运碎片时,掌心里残留的温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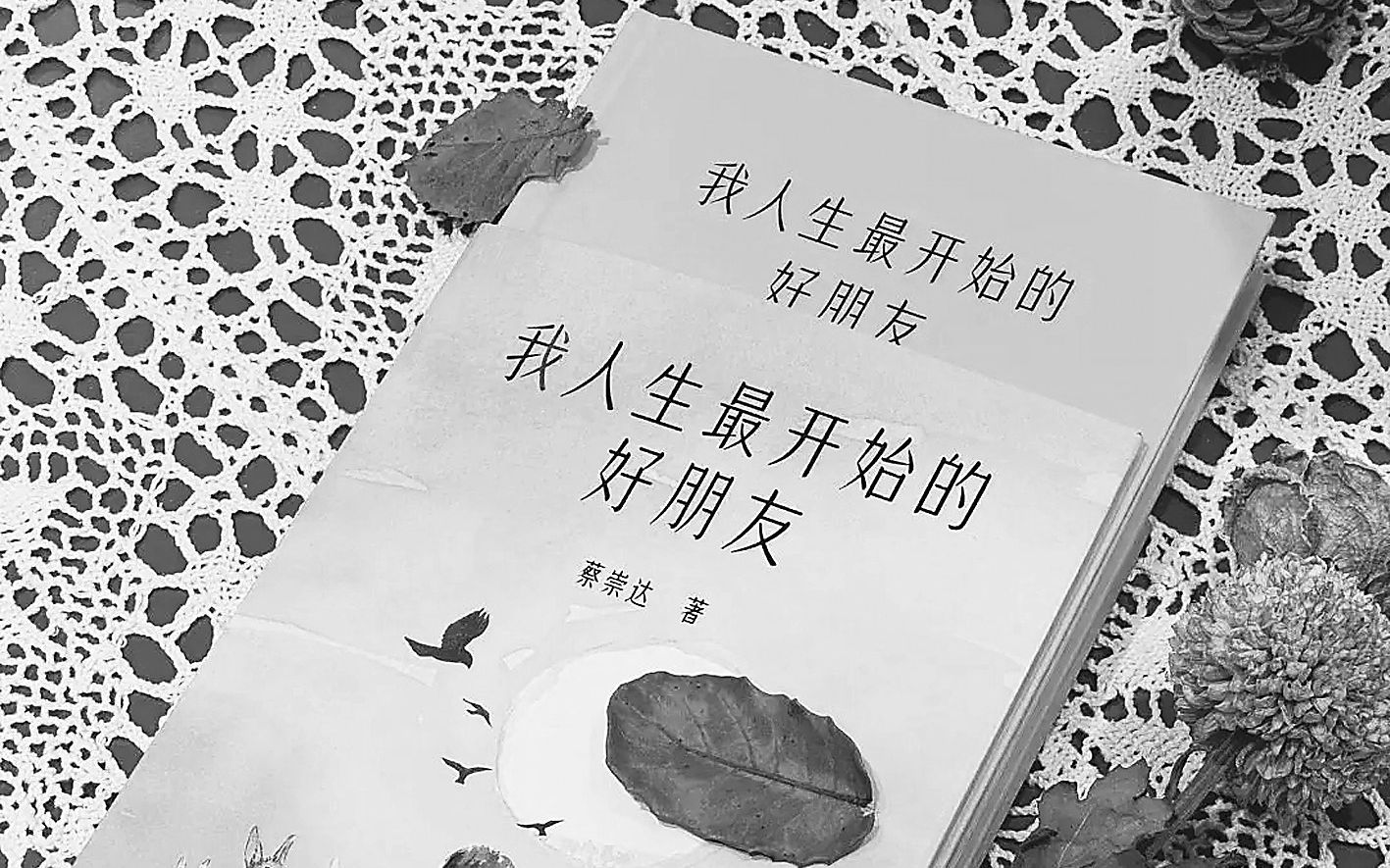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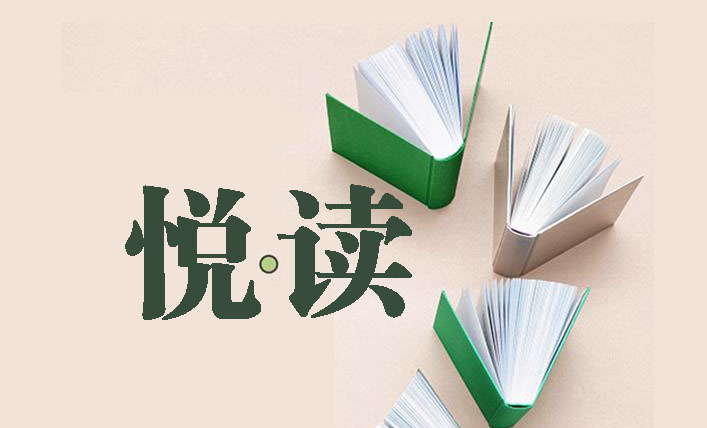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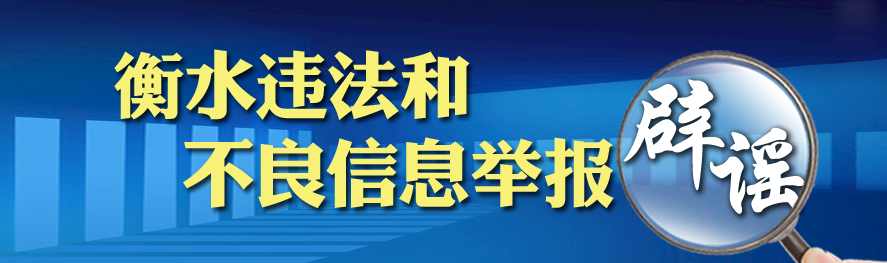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