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妈妈,是一名普通的乡村教师。她生在乡村、长在乡村、生活在乡村、工作在乡村。她先是在我父亲工作过的地方当乡村教师,走遍了大大小小的十几个村庄,后又回到家乡,继续当她的乡村教师,前后几十年,直至退休,桃李满天下。
而今,妈妈离开我已经有十年的时间了,我想念她,更想念她的手艺。
妈妈在外地当乡村教师,我大约三岁不到,随着一纸调令,妈妈拖家带口“回了原籍”,继续做她的乡村教师。回了老家,结束了漂泊不定的生活,妈妈筹划着要盖一座自己的房子。那个时候,我只有六岁,还不到上学的年龄,便成了妈妈手下的“小工”。这是我第一次见识妈妈的手艺——民间建筑手艺。
新房落成了,“大工程”结束,后续是一些小的扫尾“工程”。这些小“工程”,最先要做的是路面硬化,也就是妈妈口中的“砌当院”。每天上午,妈妈就招呼上我,背上筐,到街上、地里去捡拾小砖头。下午就在院子里忙活着铺砖路。妈妈是远近闻名的干净人、利索人。建房子时,她是“总设计师”“总监理师”和“助理建筑师”。这些“附属工程”当然也是由她亲自设计、亲自监督施工。那个夏天,妈妈先设计好路面,打好“灰”线。下雨停歇的时候,就是我们娘俩“施工”的最好时机,因为只有这个时候,才能凭着雨水的流动和积存,知道哪儿高、哪儿低,哪儿该垫些土、哪儿该起些土。好在,雨季过去的时候,我们娘俩的院落也铺完了。街坊邻居来串门,看到硬实、平展的院落,都说这院子整洁、透亮。
我最想说的,是妈妈的厨艺。那时候,缺吃少穿是每个家庭的日常困扰。我们家是“商品粮”,粮食有定量。如何规划一天、一个月乃至一年之中的吃喝,是天大的事。在我的记忆中,每年的春天,是我们饭菜花样最多的时候。早晨,妈妈招呼我早早起床,去地里挖野菜。我们挖的最多的是青青菜、荠菜、蒲公英,有时还摘树上的榆钱、嫩榆叶、槐花等。我最爱吃妈妈用榆钱或槐花做出来的“菜拿糕”。软软糯糯,香甜可口。我还爱吃妈妈用马齿苋晒干做馅、白面和玉米面混合做皮,蒸出来的“菜团子”。野菜的清香和混合的面香相融在一起,是人间少有的美味。最期待的,是我上初中时,妈妈独创的一种方便食品——泡饼子。那时候,到校时间早,为了让我能多睡一会儿又不迟到,妈妈就在每天晚上睡觉前,先把一个玉米面的贴饼子切好,放在碗里,再把食盐、香油、酱油、葱花、醋等调料放好。等第二天早晨把开水倒进去,这样泡出来的饼子既鲜香入味,又温度适中、不凉不热。即泡即吃,几分钟吃饱喝足,不耽误上学。其实,我最盼望的,还是临近春节时,妈妈准备的那些过节的食品,糕啊、馍啊、鱼啊、肉啊,常惹得我垂涎三尺。我最中意的,是妈妈做的“素大锅菜”。我打小不吃肉,临到春节时,为了让我也尝到年的滋味,妈妈总会为我准备好这道“独食”,就是用煮肉的肉汤,加上大白菜、老蘑菇、豆腐、海带、粉条等食材一起煮,既有肉的味道,又清淡爽口,相当解馋,是我此后许多年心心念念的美味。
妈妈的美食,不但是我们一家人味觉的享受,而且是大家可以分享的“美食”。每当做了差样儿的饭菜,妈妈总是招呼我:“去你家北大爷家一趟,把这些吃的给他送去。”家北大爷,是个单身汉子,带着五个光棍儿子过活。日子清苦,艰难度日。每次我去送吃的,大爷总忘不了嘱咐:“给你娘问好!”还有就是村北梨行的大爷,轻度精神残疾,孤身一人,每次我送去吃的,大爷总忘不了送些瓜果梨桃。对那些上门乞讨的人,妈妈也毫不吝啬。
妈妈最独到的手艺,也可以说是“绝活”,是她的手工。除了日常给我做的鞋啊、袜啊,还有那些又美观又实用,既可以说是工艺品,又可以说是生活实用品的“营生”。先说妈妈做的门帘,夏天的农村蚊虫多,妈妈就找一些旧的画报、挂历,用旧的曲别针做钩,一层一层包卷起来,再请人做好底画挂在墙上。就这样,妈妈把事先卷好的五颜六色的纸卷,按照底画配置起来,几天时间,就做成一幅很有画面感的挂帘。我记得我家最初那幅挂帘,是盛开的荷花和两只引吭高歌的大白鹅,清新、亮丽、高雅。真是一幅美景、美图、美画!
妈妈给予我最独特的记忆是她做的灯笼。每到元宵节的时候,是孩子们假期狂欢最后的时光,也是最欢乐的日子。妈妈给我做的小灯笼,或是一个冬瓜,或是一只小鸟,或是一柄火炬。有一次,妈妈用两天工夫,给我做了一架飞机,光源没有用蜡烛,而是用的小灯泡。我拿出去、走在街上,小伙伴们纷纷围拢过来,好不威风。
妈妈的手艺,对于我来说,既是亲情、是陪伴,也是教诲、是启迪。妈妈的百般手艺中,我最难忘的,是她缝纫的手艺。我想,这既是生活给予她的磨难,也是赠予。
妈妈缝纫的手艺远近闻名,即使到了晚年,她还一直脚踏那台老式的缝纫机,缝缝补补。我记得,我家那台缝纫机是20世纪70年代时,妈妈托人从北京买来的“北京牌”缝纫机,这台机器至今我还作为宝贝珍藏着。自从我家有了这台缝纫机,村里村外、工厂学校的人们,只要认识或能认识妈妈的,都会拿着手中的活儿,让妈妈来缝纫、织补。我记得,来得最多的是“公社”的王叔叔、闫阿姨和附近中学的穆老师、张老师。对他们拿来的活计,妈妈总是牵针搭线、不计报酬。
妈妈缝纫的手艺,是我一生中对亲情、对生活最温暖的感知,也是我生命中对母爱、对离别最揪心,然而又是最不敢忘却的回忆。
从我六岁开始,也就是我家盖上新房子、买了缝纫机的那一年,每一年的春节,妈妈都会给我买一块崭新的绿色棉布,亲手裁剪,日夜赶工,给我做一身合体的新“军装”。一到妈妈赶工做衣服时,我的心情总是复杂的。一方面是对新年、对新衣服的焦急期待。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妈妈做的衣服,总是先手工缝上,上身试了又试,等觉得合体满意了才上缝纫机加工。试衣服的新奇感,夹杂着穿了脱、脱了又穿的焦躁不耐,真是一言难尽。
妈妈总是赶在年前,就把这身绿色的、崭新的衣服做好,再把过节穿的新棉衣、新棉裤都套进衣服里。等年三十的时候,都打包放在炕头,等到初一,就可以上身穿了。
大年初一的时候,穿上妈妈做的“绿军装”,既是对妈妈手艺的展示,又是我一年中最欣喜、最满足、最抢眼的日子。因为这身“绿军装”,我是三里五庄的“名人”,总是被别人称赞、效仿。有一年,还发生了一点小变故。因为没有买到绿色的棉布,只好买了一块蓝色的布。妈妈做出衣服来,给我试穿,说:“还好,看着还行,出门如果有人问你,你就说‘当兵转业’了。”
妈妈的手艺,是我今生最难忘却的记忆。妈妈,是我此生最仰望的高山。
作者:朱洪志 编辑:李耀荣







 广告
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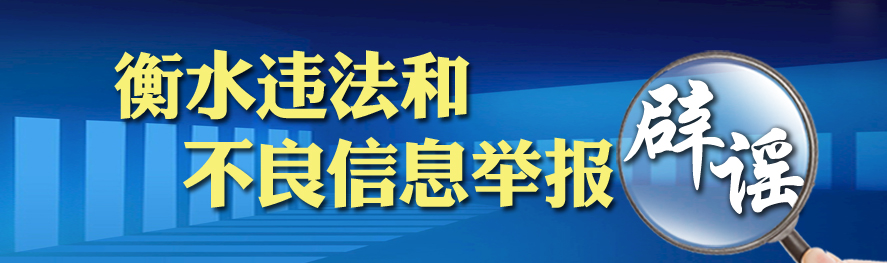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