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许多人的梦想,是希望有个院子。在周窝小镇,这却乎平常。距离衡水不近、武强不远——以乐器制造闻名的周窝,乡村与时尚兼有的地方。应小镇主理人的邀约,我欣然而至。
这次来,是打算常住。加盟小镇的文化部落,蹭点热度,也发挥余热。疫情几年,重塑了经济架构,许多时候,人们不得不思考,生存不易,发展更难,逆水行舟,进退如何才能有度。
周窝音乐小镇,十几年来因为音乐的提振,从平原上最寻常的村落,涅槃重生,麦田果蔬之外,有了乐器博物馆、艺术学校、各类手工作坊、培训机构,也多了书店,酒吧和咖啡屋。
疫情封控的日子里,小镇的生活也没有停顿。柳芽绿了,蒲公英黄了,炊烟袅袅,萨克斯曲调悠扬,掠过田野上层层麦浪。走过路过,不如遇见。临街铺面,门口的石头狮子,守望着长长的街巷。
眼前这个院落,刚好遇到。进门,迎面的巨石镌刻“雁渡寒潭”几个大字,也是不落俗套,与寻常农家院落迥异。雁渡寒潭,取意于《菜根谭》中的一句古诗“雁渡寒潭,雁过而潭不留影;风来疏竹,风过而竹不留声。”
显然,院子经过设计整修,疏枝淡叶,清雅有加。虽然未见竹子,也是有些味道了。正房三间,左右两间,一间辟为茶室,另一间作为陈列,功能都有了。此次,我亦有备而来。品茗赏器多年,略有心得,借个小店,着些个美器,守在街巷,闲看日月流逝。
时光荏苒,大风大浪见过,人间烟火可亲。茶室,挂上我的自拟对联——谁言清欢留不住?掌上器物慰平生。对联由衡水紫砂收藏及书法大家孙老挥毫而成,浪漫飘逸,浑柔洒脱,为茶室及院落增色不少。
“翠竹黄花皆佛性,清池皓月照禅心。”北方长大,却爱竹成癖,几番种植而不得。所幸周窝气候暖和,适宜竹子成活,终可圆我赏竹之梦了。有朋友成全,挖几丛自家培植的翠竹,并亲自运来周窝小院,抡镐挥锹,帮我种植。从此,竹影窗前静,无风也清幽。
“后海有树的院子,夏代有工的玉,此时此刻的云,二十来岁的你。”冯唐的诗《可遇不可求的事》,尽出他的心绪。周窝的院落,早就在那儿。而我萌生到此驻足的想法,也才是最近的事情。
音乐我是外行,但街巷里充斥的韵律感,确与寻常村落不同。喝过这里纯粹的手冲咖啡,你会忘了置身乡野。先期入驻的音乐人和手工达人,与麦田里劳作的庄家汉,奇妙的混搭,至少在这里,并不违和。
有树的院子,之所以稀缺,那是后海,而周窝这样的院子,则随处可见。不仅有树,还有各色的花儿,争奇斗艳。平原上,没有山势起伏的绝美,篱笆墙边凝着露珠的牵牛花,就是风景了。修篱种菊,晴耕雨读,更称得上骨子里的基因。
或许,前世今生,该有这一次的默契。随着部落里文化人的聚集,陌生的面孔会熟悉,熟悉的声音会更多。倏忽而过,多日不见,又来周窝。暮秋时节,小院还在,我的驻足小院的心思,也在。虽然不懂音乐,但音乐小镇的氛围我还是喜欢的。
补充些器物,都是些茶器之类,不知道,在平原上的村镇,会不会有同道中人。不过,守着个小店度余生,这样的日子,倒是我梦里的渴望。虽然说上了年纪,但驾车几十里,平坦的道路,对于习惯了山路崎岖的我来说,堪称闲庭信步了。
心中时有不解,这里的人们出城几十里就是乡村,何苦久困都市,不偶尔出来休闲呢?喜欢摆弄茶器,时间久了,有些心得,其实是愿意与人分享交流的。熟悉或不熟悉的人,与茶与器会友,也是个赏心悦目的事儿。
蚂蚁搬家,总在路上,这几乎就是我现在的状态。那又怎样呢?再好的梦想,也需要落到实处,总要做点事儿,心中才不空虚。在草原、在平原,亦或在乡村古镇,有人的地方就有可以邂逅的未来,不是吗?
寂静的小镇,周窝。十字街西,那扇红色的大门,就是我守候的店铺。说是店铺,却未必有什么生意,不过就是凑些器物,与熟悉或不熟悉的朋友聊聊天的地方。
得益于周窝的主人,免费提供的院落,美轮美奂,静谧异常,倒也符合我的心境。按说,这一段,许多事情并没有着落,还不到躺平的时候,但与其等待,不如做点事情,哪怕只是这种发呆的事儿。
也许,这种状态,就是我今后的常态,本色出演,有一搭无一搭,喝着茶,聊着天,卖着也许并不一定好卖的东西。愿者上钩,我倒不急,喜欢的东西,多在身边停留,也是求之不得呢。
周窝没有山,也没有水,但音乐的缭绕,也聚集了些许人气,许多艺术青年或中老年人,也间或过来打卡。咖啡的香气,与红砖铺就的街道并不违和。谁说美景都是自然,有人的地方就有故事,合适的人才是最美的风景。
生活在别处,也把他乡当故乡。认识些谈得来的朋友,茶也好喝了。下午市区的朋友远道而来,相谈甚欢,暮色苍茫时,返回的路上,满是充实的感觉。头顶上那轮夕阳,跟着我好长一段路,刹那间,暖意顿生。
作者:王俊清 编辑:李耀荣







 广告
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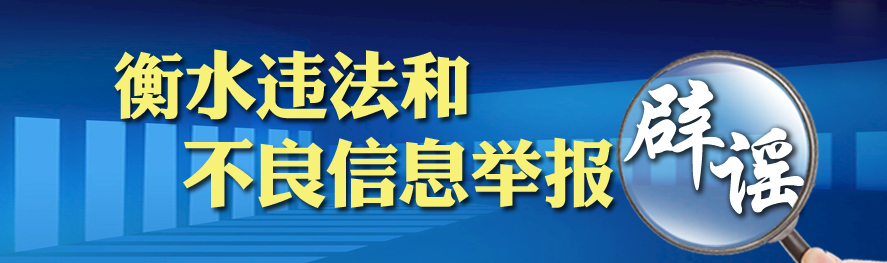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