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学要写出普遍的、深刻的人性。
这是我一直秉持的观点。我所有写作都以此为纲。无论小说、散文还是诗歌,我用写作发掘人性之良美,揭露人性之丑恶。早年间我读到沈从文先生在《习作选集代序》中讲到他以“供奉‘人性’”为主旨进行文学创作,慨然在书页空白处写下:任何人、任何团体出于任何需要编撰的文学史,都无法掩盖您作品中散发出的人性的光辉!
铁凝在一篇谈论写作的文章中提及:“伟大的文学应该是直逼人性的,而且应该具有对时代和社会的超越性的特征。好的文学要关注人类,关注人性的含量、审美和创造,好的文学也应该是人类思想最重要也最宝贵的活动之一,能够代表作家所处时代对人性认知的最高水平。”
鲁迅、索尔仁尼琴、川端康成、纪伯伦……文学的伟大之处,正在于关注人类,关注人性。
二
法国批评家埃斯卡皮为文学之门制定了一个门槛:“作家死后10年、20年或30年,总要到‘忘却’那里去报到。如果某个作家跨越了这条可怕的门槛,他就踏进了文学入口的圈子,同时几乎可能流芳百世……”
1942年9月8日,沈从文在他写给大哥的一封长信中对自己的作品做了充满自信的判断。“我正想好好地来个新的十年工作计划,每年来写一两本好书。我总若预感到我这工作,在另外一时,是不会为历史所忽略遗忘的,我的作品,在百年内会对于中国文学运动有影响的,我的读者,会从我作品中取得一点教育的。”
接下来,他以自己和某些人对比,自然讲到了文学的功用。“眼看到并世许多人都受不住这个困难(前文提到日子穷苦寒酸)试验,改了业,或把一支笔用到为三等政客捧场技术上,谋个一官半职,以为得计,惟有我尚能充满骄傲,心怀宏愿与坚信,来从学习上讨经验,死紧捏住这支笔,且预备用这支笔来与流行风气和历史陈旧习惯、腐败势力作战,虽对面是全个社会,我在俨然孤立中还能平平静静来从事我的事业。我倒很为我自己这点强韧气概慰快满意!”
我愿意预言,沈先生的作品定会跨越那条可怕的门槛,而同时代诟病、批判他的那些“高明”的作家们,也定会到“忘却”之处去报到。
三
对于这道门槛,中国的文学评论家们直接选择无视。作家李国文在一篇探讨如何评价文学作品的文章中写道:不知道什么原因,现如今,公允的评论越来越不多见,怀着私心,揣着私货,泄着私愤,拿着私房钱的不公允评论却越来越泛滥。当代文学评论家们最消极的一面,就是将文字当作“花露水”,遮掩所评作品的不足;将文章当作“雪花膏”,为一些并不值得推介的作品涂脂抹粉。
某女赋诗,不走寻常路,诸位大家力捧其独树一帜(竟有几位是我原本较为喜爱的评论家,看到他们跻身其间,与有荣焉,目疼之极)。鲁奖泛滥,钞票选票互为交易,令嫉恶如仇的先生泉下结舌(某年去到绍兴参观鲁迅故里,临街迎面是先生擎烟沉思的画墙。想到鲁奖近些年的喧嚣热闹,竟然还敢厚颜无耻地在先生注视之下搭台颁奖,真想替先生大爆粗口)。此类事例稍一罗列,即可著一部《二十年目睹文坛之怪现状》。
作家残雪恰好在一篇《文坛跟黑帮团体差不多》的文章中给出了答案:“许多作家都在文坛混,同那些所谓批评家抱成一团来欺骗读者。因为现在大多数读者还不够成熟,分不出作品的好坏。”残雪一直被视为文坛另类,除了她作品的先锋意味,还有她不吐不快的耿直秉性。文章最后,她破天荒地举了几个在文坛上将“混”称之为“转型”的名作家(太过有名,不便转述于此),措辞颇为犀利,毫无情面可言。诚然,这仅为她的一家之言,可惜的是没有一家报刊将不同的声音释放出来,供读者自行评判。
熊培云在《月光中》有句:“人生痛苦之源不外乎两种:一是恶挥之不去,二是美求之不得。”我借用一下,文学世界的苦痛莫不如是。
四
文学要为特定人群服务吗?文学一旦丧失其独立性,就毫无价值可言了。如果非要给出答案,我讲,文学应为人民(整个人类)服务。一城一池,一门一派,一家一族,一朝一代,都不足以让文学臣服。无论时间还是空间,文学若是主动从属于某种局部利益,那它速朽的命运便早已注定。
夏坚勇教授在《大运河传》中有一段事关文学的论述。以隋代为例,别有见地。抄录如下。
“我们都知道隋代没有文学,这固然与它立国时间太短有关,但最重要的还在于统治者对心灵的扼杀。”“知识界也弥漫着一股玩知丧志的实用主义风气,文化人纷纷挥刀自宫,把心灵变成敲开利禄之门的石头。他们写诗作文是为了拍皇上的马屁。歌功颂德,献媚讨好,成为当时文学艺术的主旋律。这种主旋律实际上是一种大棒加胡萝卜的文化专制,作为政治专制的派生物,它当然也不会比政治专制宽厚和温柔。它使一切有尊严的人贱卖自己去摧眉折腰,沦落为招招实惠的文坛阿混;它给所有的作品都强行抹上‘盛世’的油彩,在一片‘吾皇圣明’的颂歌中搔首弄姿发羊痫疯。可以想见,这样的作品怎么能散发出激情的血温,怎么能燃烧起生命的光彩,又怎么能用来讨论深刻和崇高?”
其实无论什么时代,都要以此为鉴。文学艺术尤甚。
五
依照我的阅读经验,作家大致可分为两类:值得认识的与后悔认识的。
关于这个话题,钱钟书先生有言在先。《围城》一经出版,短时间内重印数次,还被译成多国语言,受到世界各地读者的追捧。有人鸿雁传书,有人登门拜访,先生不胜其扰,苦不堪言。某日接到越洋电话,一位英国女士求见甚急。钱先生天性幽默地回绝道:“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不错,又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诚然,先生的“母鸡”一说并无褒贬。但仔细分析,其中又不乏“值得”与“后悔”的分别之意。先生淡泊名利,甘愿“板凳要坐十年冷”地做一门学问,厌烦了一切抛头露面的事。殊不知,此一时彼一时,市面上总不乏那样一群相当活跃的作家。
巴金在一封给他“粉丝”的回信中写道:“对于作家,还是看他的文章有意思。我自己也有这个经验,有时因为认识了这个人,连他的文章也不想读了。自然伟大的作家不在此列。他们的生活与思想是一致的。不过我够不上。因此我还是希望你读我的文章。”
二位先生行事低调,说话委婉。再来看看那群市面上活跃的作家,总像一只下了蛋的母鸡那样“咯咯”叫着出现在一个又一个曝光的镜头里。上文中,沈先生评价这类人只用了四个字——以为得计。他们永远不知道文学世界里有一条“忘却的门槛”,这正是令我后悔与之相识的原因。
作者:贾九峰 编辑:李耀荣






 广告
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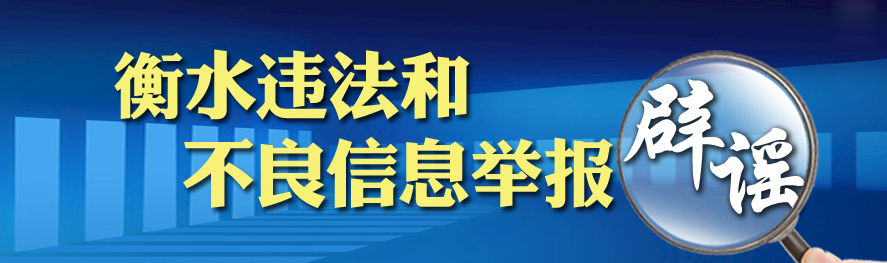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