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麻糖是老姜家祖传的营生。相传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外逃,老姜的祖上曾救过一个御厨,方学得了这门手艺。老姜右腿有疾,干不了农活,每日在家研磨,更是把这门手艺发挥到极致,人送绰号“麻糖姜”。
每逢子午镇四九大集,麻糖摊前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手里举着票子,把胳膊伸得老长,俨然古时候粥棚前饥民讨粥的模样。老姜不紧不慢地用那半米多长的大筷子,给油锅里的麻糖翻着个儿,待到两面金黄时,才夹起来抖抖上面的油,挨个放在案板上。
一声吆喝,别挤,别挤,都有份儿。老姜开张了。
老姜的麻糖有三绝:一是好吃,外酥里嫩,颜色金黄,香甜可口,唇齿留香;二是麻糖论斤卖,论个拿,斤两不差分毫;三是集日只做30斤面,炸完就收摊(按今天的话说,这叫饥饿营销)。
一个外乡赶集的大嫂拿着四个麻糖问,“老板,你也不称?够一斤吗?”
“大嫂,您不放心,咱过下秤,您看正好一斤。”
“老板,给俺换个大点的行不?”“大嫂,你自己挑,随便换。”
大嫂连着换了几个,还是正好一斤,她不可思议地张大嘴巴。老姜狡黠地笑着,好像在说,论斤卖,论个儿拿,这是俺苦练的本事,俺不亏你,你也别想沾俺的光。
这年的七月雨水勤,隔三差五就会来一场,像泼,像洒。子午镇村边的坑里、沟里早就灌得满满的。老人们说,老天爷这是把天下漏了。
第二天又是大集的日子,到傍晚雨还没停。唉,老姜心里堵个疙瘩,涝了好几个集,半月不开张了。他拖着那条跛腿,在屋里晃过来晃过去,晃得他老婆直心烦,骂他是墙头上的高粱没出息。
半夜里,雨停了。老姜才爬上炕打起呼噜。
天刚朦朦亮,村里的高音喇叭就嘶吼起来。老姜坐起身子,揉着眼睛嘟囔道,大清早的发什么神经?
“全体社员注意啦!滹沱河里下来大水了,所有青壮年带着铁锨到大队门口集合。”老姜惊了,提上裤子就往门口跑,可还没迈出两步,那只跛脚一侧歪就摔倒在地上。
老姜爬起来不出去了,他开始和面。
够了,够了,够30斤了。媳妇在旁边喊着。
今天人们吃得多,咱要多和点。
那你不破了规矩?
咱今天就得破破规矩!
天亮了,老姜的麻糖摊孤零零地摆在大街上。他站在油案前,看看翻滚的油锅,回头就抓起案上的面团,一拍,一垛,再在上面划个口子,两只手抻起来拧个花,倒提着放进锅里,滋溜一声,麻糖在油锅里扎个猛子,又钻出来。
陆陆续续从大堤上传回消息:昨天夜里村里的干部党员就上堤了,水来得那个猛,眼看着漫出河槽,跟着人们的脚来到大堤下,不停地往上涨,真让人害怕。
大喇叭广播时水离堤顶还有一米多,可当十里八村的人们赶到时,水几乎平了堤顶。人们一看就急眼了,背着土袋子吼吼叫着往上冲,愣是在堤顶垒起一条宽一米高半米的土埝子。
“哗,哗……”五龙堂通大堤的车道处冲开个口子,南王庄赶来的200多名乡亲一声呐喊冲过去,决口挡住了。
水一点一点地往上涨着,眼看就要没过才挡的土埝。有人吓坏了,绝望地扔下铁锨就想跑。轰隆隆,轰隆隆,堤下开过来几辆大卡车,从车上跳下一队队的解放军战士。他们二话不说,拿起口袋就装土,背的背,扛的扛,不一会儿土埝又加高了一层。
大街上冷冷清清的,男人们都上了堤,女人们也没心思出来逛。看着案板上小山似的麻糖,媳妇埋怨道,你看都没人买,让你少和点面,你还不听。老姜撇撇嘴,有人等着吃呢!赶紧拉你的风箱。
正午的阳光直射在河面上,河水泛着金光。一个跛脚的汉子推车来到堤顶,麻糖的香味飘出老远老远。
迎面走来两名解放军战士,大叔,麻糖能不能卖给我们?我是部队的炊事班长。
汉子提起两袋麻糖,这些先拿去吃,不够还来拿。
大叔太感谢您了,您先过个数,一会儿好算账。
不用过,我心里有数。
他支起一个小木牌,上写“麻糖免费吃”。
作者:孟海涛 编辑:李耀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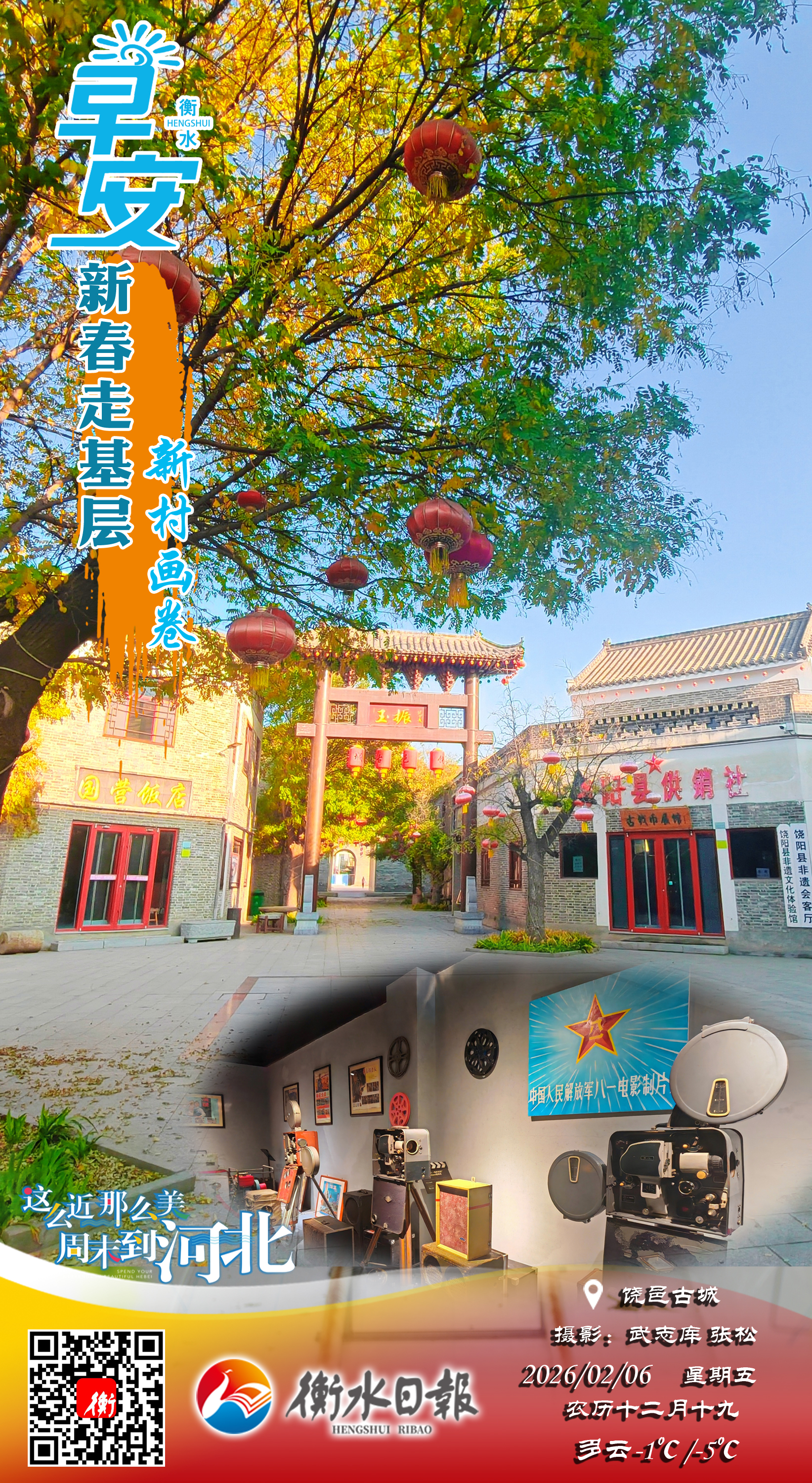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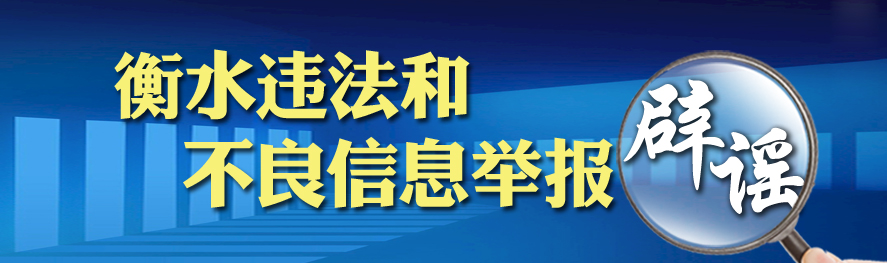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