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不是《直播衡水》新增了版块《美食·美客》,我差一点忘了一直以来对美食的暗恋。
我本布衣,甘愿过桑麻小径、绳床听蛙的散淡生活,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但是,对于美食还是有一点点儿思慕,因为那对于我犹如一个暗香中的梦影。
多年前,一个肚子里颇有点儿墨水的远房亲戚在乡镇上开了家茶饭馆儿,名“柳林居”,一篷老大垂杨,三架灰砖瓦屋,专做烧麦,远近有名。堂屋正中高悬他自己写的字,粗粗裱过,秃笔写在青纸上,字大如拳,书法怯如新妇,词儿还行:“小村小民小日子,小茶馆配小茶壶,老头子弹老弦子;小菜园小葱小筐小镰刀,老旧歌老词老调老脑筋;虽小绝无小人心,虽老不做老狐狸”——小村小民心怀大,一丘一壑也风流。我徘徊良久。
当时,我因为神经衰弱从衡中休学半年,心里正是至暗的时节,诸事纠缠,急火攻心,总想撞墙,干脆坐上红面包公交回老家,一头扎进了柳林居。正当六月天,垂杨枝条像风中的青衣水袖,树下两只土狗看见生人抬抬眼皮接着睡下,它们的饭盆里还有一堆油肥散碎烧麦,狗吃饱了也不多管闲事儿。在屋里坐下,穿堂风阵阵,清凉洗心,让人暂时忘却营营。
在这里,第一次品尝烧麦,油酥皮儿十八褶,汤水鲜肥,羊肉大葱味儿袅袅,像飘春榭的游丝一样粘人,一点不比扬州冶春包子差。酱醋麻油蘸蘸,大口大口吞了,顿时觉得天底下没有一件不好事。四周春深似海,海上春天还在生长,清清徐徐,深浅红绿,恍恍惚惚像潜沉到梦中。
吃饱了,泡上壶花茶沫子,粗瓷碗盛了,滋滋吸着喝。打量着油光瓦亮的老桌和老板凳,发呆。外边天轻阴下来,雨细筛子筛过似的落下,地皮渐湿,潮意顺着青砖缝淌进屋里,又顺着老板凳腿爬上来,带着点土腥味儿,也有地里的麦香,倦怠就来了。倦和累不同,在衡水是累,好比天天跑马拉松,肌肉里最后的劲儿也被一丝一丝抽出来,身体就越来越滞重。而倦呢,是精神的感伤,是灵台无计可施,是明镜染尘埃。在柳林居,倦了,这倦如湖上的水葫芦,疯长,让我对学业和明天开始迷航。
柳林居生意尚好,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农村正处在苏醒的阶段,四五十岁的人开始尝试着享受一点汁水渐少的干涩人生,八毛钱一碟儿猪头肉,六毛钱一盘烧麦,两毛钱一小锡壶老白干儿,就是生活对一个庄稼人的犒赏。当年的农村并不像很多人想得那么苍白,它一次次一年年向你展示着希望,心里火苗刚被压弯腰的辛苦浇灭,转眼春风吹又生,如地里的草和庄稼。乡村有饥荒年饥肠百结的莫言啃煤块的酸楚,也有下雨天孙犁结良缘的人间喜剧,乡村把庄稼人揉搓着,也按摩着,摔打着,也呵护着。仔细看看,美好无处不在。比如,很多人觉得驴丑,面如长瓜,嘶鸣如哭。但你如果细察,它双眼皮,大眼睛,澄澈如秋水,看见它,我常想到《红灯记》里的铁梅,没错,大眼睛一样秀美。
天天三杯软饱,一枕黑甜,我无事可做,什么也不会做,只能静静地做一名看客,听食客们东拉西扯,盖房娶媳妇儿,某家娃娃考上了隆尧师范,某家闺女和相好私奔,骂娃娃打老婆,或者被老婆追着满街打,最怕老婆的田六竟然让老婆追得不是上房就是上树……全是井台闲话,却也是乡村全景。乡下故事俚俗,却能养心,和豆子小米养人、陌上花开养心一个道理。坡地上的野菊花健硕生长,无需老天特別眷顾,只要随便两三场雨,几阵和风,就悄然一片金黄,难管难收地自由摇摆,一副世事与我何干的模样。
我吃饱喝足了也四处闲逛,在柳林居旁边,郭西乡有个供销社,踱进去发现除了油盐酱醋,居然有个砖头垒的书架,《三国志》等书赫然蹲在里面,售货员正在读书,是一本《桃花扇》,这让我很诧异。八十年代,是个理想丰满的年代,一株荠菜、一丛麦苗也有春天,钱穆能从店员成为大师,那束鹿县郭西乡的店员也可以带着梦想向未来。
我买下了一套三册的《三国志》,天天头不晕的时候读。随后又把大伯在老屋大木柜里的1950年版《红楼梦》四册、《战争与和平》、《郁达夫诗钞》等装了半麻袋,美食也不吃了,如同一个得手的山贼,一声“扯呼”,跑了。
30多年过去了,这绑票一样搞来的书一直静气地住在我的书房里,已经算是我的镇宅之宝,是多代同堂中的老爷爷老奶奶,当年如果不是烧麦,我和这些书或许无缘。
这些年见过很多美食,香色卓卓者众,但当年的烧麦之美,在我看来,一直没有任何美食可以超越。
作者:程愉昶 编辑:李耀荣







 广告
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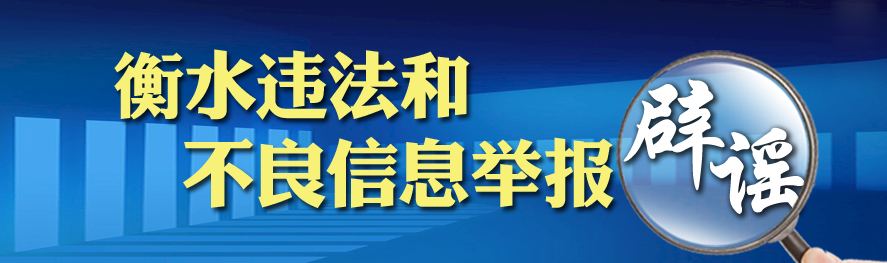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