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又到了苜蓿萌芽的季节。在春风的撩拨下,仿佛一夜之间,隐忍了整整一个冬天的苜蓿的宿根,迫不及待地萌发出一簇簇、一丛丛的嫩芽。昨天还显得有些干枯荒凉的苜蓿地,今天覆盖上一层娇艳欲滴的绿色。
童年的这个时节,又该偷苜蓿了。
孔乙己说:偷书不算偷。
家乡人说:偷苜蓿不算偷。
其实,都有些强词夺理。偷书不必说了,苜蓿虽然只是一种饲草,但毕竟不是你家的,你趁人不注意,悄悄占有,怎么能不算偷呢。可是,大家真的不把偷苜蓿视为一种劣迹。在农村,小偷小摸被叫作“三只手”,哪怕你只拿了人家一个窝窝头、偷了人家一毛钱,也等于干了见不得人的事,一辈子被人瞧不起。唯有偷苜蓿,不仅互不隐瞒,甚至把偷来的苜蓿当做礼物送人。最有意思的是,多数时候都是成群结队、若干人一块去偷。但这“成群结队”又丝毫没有团伙作案的嫌疑,在文化生活枯燥的农村,有时候倒像是一种集体娱乐,一种派对。
为什么偷苜蓿不算偷?我思忖:其一,苜蓿毕竟只是一种草;其二,苜蓿是多年生的草本植物,一年至少可以收割三茬。人们一般只偷头茬苜蓿的嫩芽来吃,只要采摘的时候不伤及根部,很快又会长出新叶来,并无大碍;其三,在温饱问题没有解决的年代,偷苜蓿的目的纯粹,是为了果腹。民以食为天,偷点苜蓿在道义上并未完全失守。
春天对于人们来说,是最美好的字眼。但在当年,春天还有一种表述,叫作“青黄不接”。去年秋天的粮食已经吃完了,今年的麦收时节还未到,是一年当中最难熬的季节。半年糠菜半年粮,说的是野菜。那时候形容因为吃不饱而面黄肌瘦的人,有个成语叫“面有菜色”。可春寒料峭的时分,连野菜都没有,好容易盼着苜蓿发芽了,你真让我只是眼巴巴地看着?
参加偷苜蓿的,多数是妇女和孩子,很少看到过成年男子去偷苜蓿。即使被看苜蓿的人发现了,面对一群妇女、孩子,也不好处理。另外,干这种活,男人不如女人手快。一位堂婶就是偷苜蓿的高手,我亲眼看到她两只手同时采摘,快得如同刀割一般。
男孩子都喜欢玩打仗的游戏,但再怎么玩,毕竟是游戏。真正能找到感觉的,是偷苜蓿。因此,小伙伴们特别热衷于跟着自己母亲去偷苜蓿。你想想,漆黑的夜幕下,既要采摘苜蓿,又不能弄出动静来,以免惊扰了看苜蓿的人,确有几分刺激。每次出发之前,母亲们照例要叮嘱一番,“跟着去玩可以,但去了绝对不能乱跑乱叫”。可一旦到了苜蓿地里,熊孩子们哪里还控制得住,不一会便互相打闹起来,有一次竟然打开了“坷垃仗”,一个力气大的孩子一不小心,居然把坷垃投进了看苜蓿人的棚子里。看苜蓿的人忍无可忍,冲出棚子,高喊一声:“逮住偷苜蓿的!”
几十个妇女、孩子起身便跑,黑压压一片,如夜晚惊鸿。
这一次,我们的行为确实欺人太甚了,否则一般情况下,看苜蓿的人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时候,即使被看到了也可以通融。记得有一次我和母亲赶集归来,路过邻村的苜蓿地,母亲对看苜蓿的老爷爷说:叔,我想捋点苜蓿。老爷爷环视了一下周围,说:“快点捋,别让村干部来了看见。”于是,母亲迅速地捋了一篮子苜蓿。
虽然在集上转了半天,什么也没有舍得买,母亲又㧟个空篮子回来了。但半道上捋了一篮子苜蓿芽,便有了满满的成就感,觉得阳光都灿烂了许多。
★ ★ ★ ★ ★ ★
苜蓿的原产地并不是中国。它是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时带回来的。不仅苜蓿,小麦的起源地也不在中国,玉米更是明朝嘉靖年间才从中亚引入的。当然,早在周朝时中国的水稻种植技术就传到了国外,大豆的种植技术也是由中国输出的。当代,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引入、输出的物种、技术更是数不胜数。除去刻意引入的之外,还有“偷渡”进来的,比如擅自闯入中国的小龙虾。也有“偷渡”出去的,比如让美国人头疼不已的亚洲鲤鱼。
一部世界历史说明,整个人类是名副其实的“命运共同体”。只不过越是接近现代,相互依存的色彩越发鲜明。在这一点上,绝大多数中国人是包容的、大度的、明白的,不论是罗非鱼、红富士,还是面包、巧克力,只要好吃我就吃。当然,还有苜蓿。
我们曾经以为苜蓿是野生的,其实除去路边、田埂偶有几株野生苜蓿之外,凡是成片的苜蓿都是人工种植的。它的管理非常粗放,又喜欢微碱土壤,我们家乡一带便成了苜蓿的宜居之地。
苜蓿是作为饲草引进的。在所有的饲草中,它属于营养最为丰富的高档饲草之一。曾经有一位养牛的老板对我说:“不能让牛吃太多苜蓿。”我问:“为什么?”他说:“营养太丰富,就像人不能一天三顿都吃红烧肉一样。用低档饲草搭配少许苜蓿即可。”
什么时候发现苜蓿这东西人也可以吃?无从考证。不论人吃苜蓿有多少年的历史,在我的记忆中只有一种吃法,就是洗干净之后,拌上一些玉米面,上锅蒸熟了吃。家乡叫“拿糕”,深州一带叫“蒸菜”,辛集那边叫“苦类”。对于“拿糕”,我实在想象不出它和我们印象中的“糕”有什么共同之处。而“苦类”则容易让人理解,穷人吃的东西嘛,但又拿不准是“类”呢,还是“泪”或“累”呢。比较而言,“蒸菜”最为形象,也不容易产生歧义。所以,在我的文章中,多数时候叫它“蒸菜”。
尽管苜蓿是人工种植的,人们还是习惯把它归类为野菜,而且它是春天发芽最早的野菜之一。几乎与它同时,金黄色的榆钱争先恐后串满枝头,紧接着所有的野菜陆陆续续破土而出。刚开始还是“草色遥看近却无”,转眼之间,星星点点的生命之色就会染绿整个原野。因此,小时候每当看到苜蓿发芽,心中就会涌起难以言喻的欣喜,至少有野菜可以吃了。
对于农民来说,所有无毒的野菜都可以用来做蒸菜,其中苜蓿芽做的蒸菜最好吃。虽然好吃,但如果天天吃蒸菜,且一顿饭只有一篦子蒸菜,再好吃的美味也成了“苦类”!所以,当一个人面对着天空发呆的时候,常常想:如果有一天能够吃上奶奶和母亲盼望的那种净米净面的饭食,就再也不吃野菜了。
谁料想,不仅吃饱了而且吃好了之后,更加怀念野菜,特别是苜蓿。街头居然有了作为商品出售的苜蓿芽,甚至星级饭店里也有了苜蓿做的蒸菜,只不过还配有一盘蒜泥、香油和醋合成的调料,把蒸菜蘸了调料吃。当年我们没有见过这种吃法,只是听说财主家为了尝鲜,也会吃苜蓿芽蒸菜,是蘸了调料吃的。
有样学样。在饭店里吃过蘸调料的蒸菜之后,回到家里如法炮制,果然好吃。我们也享受了一番财主生活。
如果说当年吃苜蓿是为了充饥,今天确实是为了享受。
前些日子,正在想不知今年还能不能享受到苜蓿蒸菜,恰有朋友送来一些。尽管出身农家,吃惯了野菜,也没有见过这么鲜嫩的苜蓿芽。朋友还晒出一张照片——和煦的阳光下,一片嫩绿、绿得还稍稍有点鹅黄的苜蓿地里,几位秀气的女士在埋头采摘苜蓿。那情景真好!经过两个多月的疫情,经过两个多月的宅家生活,经过两个多月的沉寂,看到那一地绿色,仿佛重新萌发的不是苜蓿,是我们复苏的生命。那一双双巧手采摘的不是野菜,是春天。
遗憾的是几位女士的衣服比较朴素,颜色与苜蓿反差较小。武强从事木版年画的老艺人总结出一条着色经验:红配绿,一台戏。如果在碧绿的苜蓿地里,每人穿一件红色的衣服,那一份靓丽,一定能让照片获得摄影金奖。
对于苜蓿真有说不尽的感情。如果让我写诗,我会把“春在溪头荠菜花”写为“春在路边苜蓿芽”。
作者:任之初 编辑:王常荣








 广告
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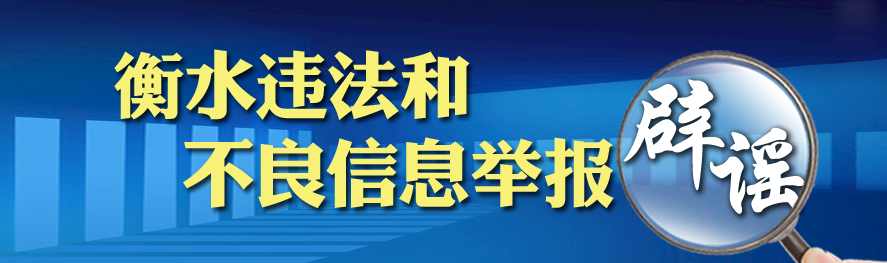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