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舅爷(下)
王国华(深圳)
我小时候从王过庄村去郭里阳村拜年,坑坑洼洼的土道,骑自行车差不多都要一个多小时,如果步行,估计至少需要半天。郭玉贞走这么远的路去见姐姐,不知是顺路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或者是在家里受了委屈,到姐姐这里来寻求一点儿安慰。十七八岁,本质上还是个孩子。
但这里有个大问题,郭玉兰生于1920年,郭玉贞比郭玉兰小4岁,资料上却说郭玉贞生于1914年,这是怎么回事?
我思前想后,豁然开朗,这有可能是记录错误,把“1924”写成了“1914”,或者是书写时字迹模糊,后人整理到电脑上时,辨认不清,输入成1914年。王素珍认同这个猜测。生于1924年,一切都合理了,那时候人们记录年龄都用虚岁,1940年牺牲时虚岁正好是17岁。生日大的人,比如正月或者二月出生,还要在周岁上加两岁,所以说他18岁牺牲也没错。这与老人们传递下来的信息相吻合。
再想,那些年的战争中牺牲了那么多年轻人,一定还有不少像郭玉贞这样的人,名字、年龄、事迹只是被粗疏地记录一下,信息模糊。有的甚至连记录都没有。这需要和他们有血缘关系的、知情的人尽快查找。
好在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烈士。
年轻的郭玉贞到底经历了什么?
根据阜城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提供的几句话,我找到了郭玉贞所在部队“冀中十六团”的一些资料,从中摘录若干信息如下:
第十六团原是冀中(军区)一分区第三团,于一九三八年初在束鹿县(现为辛集市)旧城镇组建,同年四月间,改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第七支队第二十一大队。
一九三九年九月整训结束,返回冀中,奉命开赴景(县)阜(城),交(河)新区工作。在阜城、故城两个日寇据点之间高十二屯进行伏击战,激战半小时获全胜,缴获了骡马大车、迫击炮、轻机关枪、步枪、子弹等军用物资,毙伤一部分日寇。同时在滏阳河以东、献县西南打了一个袭击战;在阜城以东,打了一个伏击战,均取得胜利。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李家洼战斗,当时十六团和冀中一分区较为庞大的机关直属队从阜城县以东转移到李家洼一带。当地群众基础较差,通讯联络失误,突遭交河县富庄驿之敌的伏击,分区机关与十六团遭受一些伤亡。
接着十六团奉命开赴冀南五分区,在阜城、东光以及一分区的交河、武强、衡水一带活动,袭扰、伏击敌人,开辟、巩固与扩大抗日根据地。连续伏击、歼敌,打了一些胜仗,鼓舞了士气,在群众中扩大了我军的影响力。
一九四〇年五月,十六团奉冀中军区命令,随程子华政委返回冀中军区。六月,冀中军区组织任(邱)、河(间)、大(城)战役,开辟、扩大抗日根据地。十六团归八分区指挥,与八分区二十三团等部配合向任、河、大一带挺进。十六团奉命打大章日军据点……全歼日军小队长以下共卅余人。
大章战斗后,十六团开赴沧石路,在深县大由庄、铁儿庄、南北旺头等地伏击、袭击、反击日寇,接连打了几个小仗,均有所获。
十六团于一九四〇年八月充实装备与兵力后再次赴晋察冀军区参加了“百团大战”,属聂荣臻司令员统率的三个纵队中的中央纵队,归杨成武同志指挥。十六团攻占娘子关以东之南峪、北峪车站,破坏了铁路。炸毁北峪铁桥时,先用黑色炸药效率差,聂荣臻司令员亲临十六团二营阵地视察,调来黄色炸药,将铁桥炸毁,使正太铁路一个月不能通车。
从这个有限的资料中可以看出,郭玉贞参加的是八路军,一年多的军旅生涯中经历了多次战役,基本都是在和日军作战。活动范围主要在家乡阜城县及周围区域,其间,回村探亲应在情理之中。他在1940年8月牺牲,正好是十六团去参加“百团大战”的时候,途经曲阳县。合理推测,应是遭遇了小型战役,或是行军时不幸失足。结合奶奶对郭玉贞坠崖的记忆,我特意查了下,曲阳县是个山区,素有“六山一水三分田”之说,紧挨着五壮士跳崖的狼牙山。半夜部队急行军,发生意外的概率不低。
我的脑子里出现了一个画面。硝烟、战壕、冲锋号、背包、步枪、稚嫩清秀的面庞……一个人的形象渐渐清晰起来。
郭玉贞牺牲后,奶奶每年清明节回娘家都要给两个弟弟上坟。郭玉凤好歹还有一座孤坟,郭玉贞却连个坟头都没有。奶奶对弟弟的思念,那个远方的年轻战士应该能收到吧。
一定。
我们这些后人也一定好好过日子,给牺牲的前辈、给我们的亲人最大的安慰。







 广告
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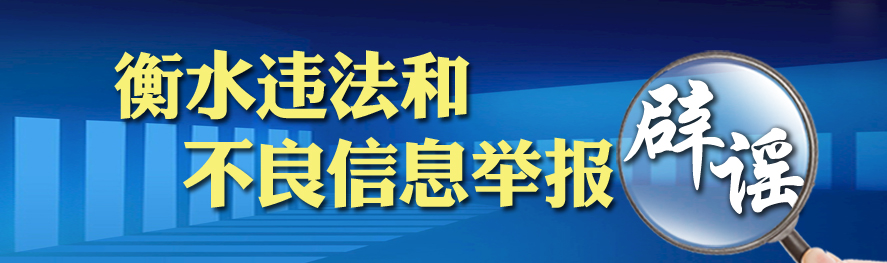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