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退九霄净,秋澄万景清。”暑气退去的秋天,天空明净而高远,凉风习习,万物清丽。
中秋时节的故乡正是农忙时节,一望无际的田野硕果累累,丰收在望。沉甸甸的谷穗低垂,为防鸟儿啄食,田野里扎了好多伸着手臂的稻草人,随风摇摆。玉米熟透了,那白玉米粒、黄玉米粒似颗颗珍珠般晶亮,手指掐上去光滑坚硬。有喜欢尝鲜的人家,紧着掰下几个玉米穗来,在石碾子上轧了,清甜的香味扑鼻而来,这可是走亲访友的最佳礼品呢。虽说走访的亲友也多在乡村,且也多种有玉米,但是贵在一个“先”,这一兜新玉米面占了先机,价值自然就不同了。
夜晚的田野寂静下来,明月当空,有风吹叶子的沙沙声,那谷穗披了一层银色的光芒,或垂首轻摇或平摊在地上静默无声。成片的高粱挺立,火焰一般的高粱穗在月光下显得柔和了许多,像一幅巨大的油画,引起许多想象的空间。月亮地儿下的棉花地,是寂静的,是刚刚拾过棉朵还是好几天没有来过了,一眼看过去便知。地里的庄稼活儿从来来不得半点虚假,有付出才会有收获。庄稼无言,却一株株表达着年景和收成。
月亮是农人们心目中的月神,静悄悄地洒到每一个角落,房屋村落、沟沟坎坎。人们掐着手指盼着月圆,满月的月亮地儿(月亮在当地俗称“月亮地儿”)是锃明的。有月亮的夜晚,那些庄稼就不怕被偷,走夜路就不怕黑。院子里没有灯,屋子里也常常不掌灯,有月光洒进来,光线清晰又柔和。
从中秋时节的月亮,基本上定下这一年的年景和收成了,一家人晚饭后在院子里剥着玉米皮,那被枝叶划得皴裂的双手,在月光下显得洁白细腻。我快速地拿过一个沉甸甸的玉米棒子,用手掰去外皮,实在掰不动的,就在膝盖上磕下去。一晚上的玉米皮剥下来,穿着单裤的膝盖红了一片。
水瓮边的枣树,大马莲枣红透了,酥脆,在月光下闪着光。有时顺手摘下几个,仰头看着明月吃枣,好像是在馋月宫中的嫦娥。
最喜欢的,是中秋夜。母亲拿出梨和月饼在院子里的窗台下供月神,母亲嘴里念叨着吉祥话,请月亮爷爷普照一家人的生活和收成,祈求风调雨顺、平平安安,家人们谁也不敢出声,走路都是小心翼翼的。
过一会儿,母亲拿出两个鸭梨,两块月饼,都是切成小块,一人一块,那薄片的梨和月饼没有塞满嘴巴,甚至来不及细细咀嚼就咽了下去,回味无穷,迫切的等待下一块。母亲就会说剥完多大一堆玉米就再切一块,对此我们充满了期待,手里也更加快了速度。月亮看着一家人,在树梢的上空慢慢移动,陪着我们直到回屋休息。
有一年的中秋时节,10多岁的我在15公里外的姨家帮忙看孩子。那几天的月亮又圆又亮,姨家的熏鸡生意也越来越忙。她家20多亩地,分散在村南、村东、村西七八个地方,道路崎岖不平,我常常坐着姨的牛车去地里拾棉花。那老牛走得太慢了,过一会儿姨就用小棍儿在牛的屁股上轻轻敲一下,说声“跶”,那老牛依旧不紧不慢地往前走。在当街遇到闲散的妇女,对方问一句去干什么活,车厢里坐的是谁,姨回应两声,那人一直往车身瞅,话已聊完,那牛车还没有完全从那人身旁走过去,我尴尬地把头埋在了胸前。
那田地的名字有“四方”、有“七方”。多是旱地,杂草丛生,有一次姨让我独自回家去,一手指着方向让我抄近道,从一条土沟里爬了过去。晚上,姨在柴灶的锅头前常常忙到半夜,一地鸡毛顾不上打扫,浓烈的腥味让我食欲不振。
闲下来,我会站在那个不大的院子里看一会儿月亮。我瞅酸了双眼,瞅到泪流,感觉这不是我家乡那样的月亮。月亮移过的树梢和屋顶都是我陌生的,这月亮是清冷的,阵阵孤独感袭来,我在心底悄悄地问:我的爹娘,可否把我思念?
多年后,我走过了许多地方,见到了草原的月亮、海边的月亮、山区的月亮,秦淮河畔的月亮,京城的月亮……那月亮都好美。但我也只是一个匆匆过客,那月亮都不属于我,属于我的只有故乡那轮明月。
在小城的家中,我常常于楼房的窗前遥望十公里外故乡的方向。窗前是大片的树林,透过树梢,我似乎看到了故乡家园,举头望一轮明月,柔和而亲切,像是无声的信使,传递着故乡多年的消息。
作者:刘兰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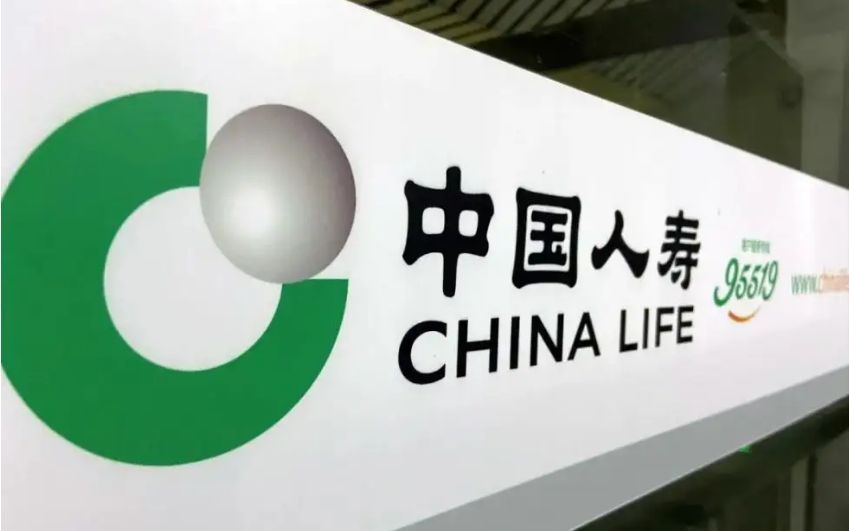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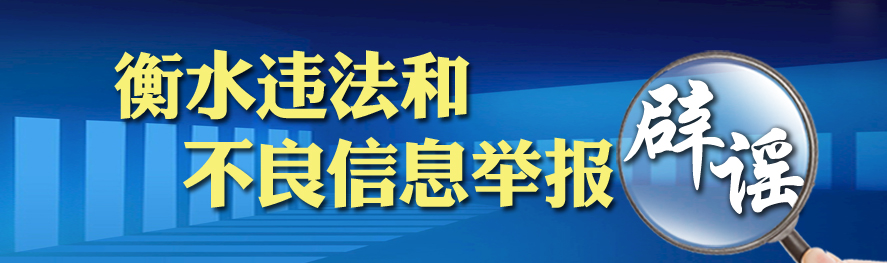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