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月份。
我的生日,是1952年的8月2日(当年农历六月十二),时值酷暑,所以每年生日,家里总吃顿凉面。
记得小时候有次生日,人们都在阴凉歇着,娘却汗流浃背地擀面条,我过去傻傻问了一句:“生我那天也这么热?”娘瞅着我呵呵一笑:“不热,不热,咱这窗户有枣树遮凉,屋里凉快着哩。”
我家北房根,有棵枝繁叶茂的老枣树,俗称“妈妈枣”,结的果实脆甜,不裂纹儿,是生吃和做醉枣的好品种。
及至老年,每逢走回这个院落,我总要在刨掉这棵老树的旧址伫立良久,想到我降生时那个夏季,想到任劳任怨含辛茹苦的老娘。
一个生在陋室土炕的农家孩子,刚满二十却有幸被选调为正式的国家干部,时间恰是1972年的8月中旬。
当时我的很多同龄人都想跳出农门,或保送上学,或招工进厂,自己虽然艳羡却也毫无机会。有次高寒地带的部队来此征兵,村里才允许报名,但因竞争激烈也未能入伍。所以突然接到去县里宣传科上班的通知,我自然就像范进中举一样如临梦境。
对我这次命运的转折,亲朋好友都认为是天上掉馅饼的喜事。儿时姥姥常帮我洗脑袋,曾几次逗我说过“耳朵大有福”的话。我去辞行时,她拍打着我喜极而泣,眼噙泪花,反复念叨:“我没白说吧,我没白说吧……”
我娘倒没表现得特别高兴,还似乎有些发愁地说:“那你要先借钱买辆车子。”之前在县里参加通讯员培训的几个月,我都是借骑堂兄的车子。于是就想法到安平集上买回一辆“永久”牌的旧车。
我村地处安平、深县和饶阳的接壤部位,距深、安两个县城皆为25华里,但离所属的饶阳县城却有40里之遥。自己在县里没有亲友和故旧,能参加学习培训,只是因为喜欢写作,经常给报社电台投稿。那次培训,没有专职老师,只是分头跟宣传科的同志们下乡采写稿件。所以能够“转正”入职,我能想到的“背景关系”就是宣传科几个人。
当时负责报道的是副科长王启元。他时常给我们开会,每次都用几句顺口溜提出要求:“衡水报,天天见,河北报,不断线。各级电台经常念,人民日报敢登攀!”我做不到“天天见”和“不断线”,“人民报”更没登过一篇,所以并不出色。细想倒有一次文艺征稿似乎稍露头角。
那年恰逢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三十周年,带队下乡的顾彦莹老师叫突击写些文学作品,此事不知是报社征文,还是上头文化部门的任务。顾老师还写了首诗歌作为示范。我对此有些基础,就连夜写了三首诗和一篇千字小说,顾老师看后非常高兴地说:“你比我写的还好呢!”他把稿子收齐后回县交差,返回后认真对我说:“我向两位科长汇报了,说数你写得好!”
时隔不久,宣传科长田双宝叫我去他的办公室。他见我就说:“你现在正写什么,叫我看看。”他平时不苟言笑,和我几乎从没说过话,我有些紧张地赶紧掏出一份刚写的报道初稿。他仔细看了一遍,用钢笔修改几个字说:“这导语写得不行!”然后说“你去找ⅹⅹ填张履历表。”后来明白是那两张单薄的表格改变了我的人生,但他们究竟怎样商定录用自己,作为当事人,我却至今一无所知。
宣传科领导和老师是我命中的贵人,但任何人却从没说过揽功卖好的只言片语。王启元老师去世时,田双宝同志已从县人大主任岗位退休。在悼念归来的路上,我感慨地说:“要不是你和王老师,我八成儿还在家里种地。”他沉思良久,慢悠悠地说:“那时的宣传科,你岁数最小!”就再也没接这个话茬。
“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这是古人崇尚的君子信条。恩施于人不求回报,甚至在受施者面前不提一字,这种品质和美德是何等难能可贵。
1974年的8月22日,是我入党宣誓的日子。这是自己政治生命的重要一天,多年来始终刻骨铭心。
初入职场,我在县委机关的干部职工中年龄最小,因此1973年被调入刚组建不久的团县委。
团县委当时的格局是仨官一卒。团委书记是县委委员,还有一名副书记是县委候补委员。我虽是唯一一兵,却也“大权在握”——负责保管公章接转关系。期间写过几次汇报,起草过一次“五四”大会的报告,均受领导好评,因之被列为培养对象,好几次被推荐到机关支部。
机关支部书记是组织部副部长刘顺通,系老资格的“三八”干部。他白发满头,为人和蔼,和我谈话时中肯地说:“我们研究了你的情况,认为你有两个特点,一是老实,二是能写。”我从不敢自认“能写”,但“老实”之名伴随一生。尽管“老实人”现在很大程度受到误读,但我始终认为党组织看人论事准确深刻,实事求是。即将入党之前,我又调到刚组建的县委宣传部。团县委副书记宋久晓说:“同桂是我们培养的积极分子,我还要做他的介绍人!”宣传部则认为本单位应有人介绍,确定的是秘书张尊贤同志。
说到8月,总让人想到惊心动魄的“96▪8”洪水。
那年滹沱河超量泄洪,致使南堤决口,受到较大损失。我因抗灾中的表现,曾被市政府记二等功一次。本人涉政多年,寸功未建,这成为平生唯一一次受到的市级奖励。为鼓舞全县重建家园的信心,我在抗洪间隙写了长诗《饶阳三字歌》,还有幸受到时任市委副书记郭华同志的来信肯定,并配发长文见于报端。第二年县级换届时,县委把我作为提拔人选上报,据说意向是担任宣传部长。虽后来情况有变,但我始终服从安排,未找组织和领导提过任何要求。我认为无条件地服从组织,应该是对一个党员的起码要求。多年以后,郭华同志到饶阳参观冀中导报博物馆,我那时已退休多年,在陪他吃饭时顺便谈及此事,他幽默地笑着说:“那你算得过提名奖!”
我这次“提名奖”,竟也与炽热的8月有关。
作者:何同桂 编辑:李耀荣






 广告
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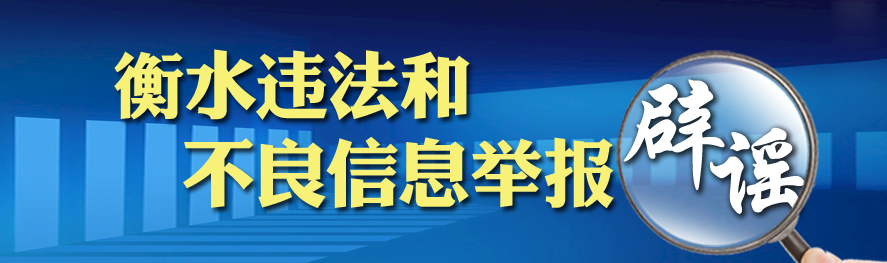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