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评张爱玲
闲翻书,翻到杨绛先生在给友人的信中评述张爱玲的一段文字,照录如下。
“我觉得你们都过高看待张爱玲了,我对她有偏见,我的外甥女和张同是圣玛利女校学生,我的外甥女说张爱玲死要出风头,故意奇装异服,想吸引人,但她相貌难看……她的文笔不错,但意境卑下。”
这本来是一段写在私人信件中的文字,属于私人交流的范畴。不管什么原因,最早拿出来公之于众的人有失厚道。
在我们印象之中,钱、杨二位先生自甘寂寞,关起门来钻研学问,板凳甘坐十年冷,是从来不对外发表议论的。但这并不代表他们没有性格,不发独抒之见。好多登门求见的高官吃了他们的闭门羹,犹见其个性之强之烈。但他们的确从不将学术之外的意见发表出来,以免祸从口出。有一年某出版社邀请杨先生撰写她父亲的生平事迹,编辑特意提醒文中可以写写她的姑母杨荫榆,让更多的读者了解其在苏州沦陷后骂敌遇害的彪炳晚节。杨先生在同一篇文章中辟出段落,简要写了姑母的婚姻、求学和最后遇害的情节。语气淡定是杨先生文字的一贯风格,但其中少有北师大风潮的故实,更无一笔牵涉到那篇著名的文章。
信中这段评价写于张爱玲去世之后,此时杨先生来到了百岁门槛,可能看到大陆上重又掀起的张爱玲热,一时略有感慨,才于私下同相知的朋友唠叨两句。有喜欢张爱玲的读者可能会因为这样的评价讨厌杨绛先生,这实在是没有必要的。
巧合的是张爱玲也曾在私人信件中谈到过钱锺书和杨绛。夏志清教授在美国从事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研究,是他最早将沈从文、钱锺书和张爱玲从一众埋没的作家中挖掘出来并给予他们相应的文学地位。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张爱玲在与夏的通信中,分别在误闻钱的噩耗和得知钱劫后余生之时,两次称许了钱先生的学问很好。因为信非常短,她没有旁涉钱的小说及家庭。从年龄上看,张要年轻十多岁,严格来说他们可以算是两代人,双方都不长于交际,没有太多的交集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张爱玲曾在写给台湾《联合文学》前总编辑丘彦明一信中写道:“新近的杨绛‘六记’真好,那么冲淡幽默,而有昏蒙怪异的别有天地非人间之感。”编辑远隔重洋给自己寄书过来,对于这一份辛苦与好心,张爱玲习惯性地抱有一种疏离的客气。这同样是她的风格,不能完全看作是真心话。
《霹雳舞》
1987年,贾樟柯还是一名17岁的山西汾阳县城的小青年。他挤在电影院里看了不下八遍的美国电影《霹雳舞》,然后忙着跟他的哥哥姐姐学跳霹雳舞,准备同他们一起去“走穴”。
现在我们知道,他并没能如愿地走上“走穴”之路。可是《霹雳舞》却为他打开了电影之门。就像电影中那些个性张扬、特立独行的男孩子们一样,贾樟柯在电影艺术道路上始终在做特立独行的自己。
万斯同
清初的万斯同,知之者几人?
万斯同为明代遗民,他不肯做清廷的官,既不应试科举,也不应试博学鸿词科。后因清朝要修明史,他才怀抱“以任故国之史事报故国”之心,答应入清史馆。万斯同的老师是明末著名史学家黄宗羲。在学生决定入京修史之时,老师赠诗有曰:“四方身价归明水,一代奸贤托布衣。”
他拒受任何官职俸,以布衣之身撰修明史,著有《明史稿》500卷。孰知明史馆总裁王鸿绪命人将《明史稿》重新抄录,却署上他自己的名字,上呈康熙皇帝。一名不学无术的官僚,靠偷书偷成了大学问家。同时代另一大学问家徐乾学,官至内阁学士、刑部尚书。他的大作《读礼通考》一百二十卷,几乎也是万斯同一人捉笔完成。
对于偷或趸的行为,老百姓有句话说得最为透彻:别人的肉长不到自己身上。
陈德征
《上海市通志馆筹备始末》一书中记载一事:《民国日报》曾在1930年发起了一次选举“中国伟人”的民意测验。答案揭晓,孙中山位居第一,蒋介石排名第三。力压蒋介石的人名叫陈德征。
陈何许人?
1930年,陈德征被任命为通志馆筹备委员,同时任上海市教育局长、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兼宣传部长、《民国日报》总编,掌握着上海的文教与宣传大权。一时的飞黄腾达难免冲昏头脑,在自己的报纸上发起选举并暗中做了手脚,竟然让自己跻身于孙、蒋之间。蒋介石一怒之下,将陈传至南京拘押数月,最后一个“永远不得叙用”的处分使其政治生涯潦草结束。
《陈德征的真面目》有记:1949年之后,已经远离政治舞台的“没有当汉奸,还有些人气”的陈德征,所遭受的恰恰是他自己早年主张过的“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的政治待遇,最终死于劳动改造。
这是一则“求名得名”的笑话。陈还算幸运,如今对他已是少有人知了。身家性命事小,千古笑柄事大。
作者:贾九峰 编辑:李耀荣


 广告
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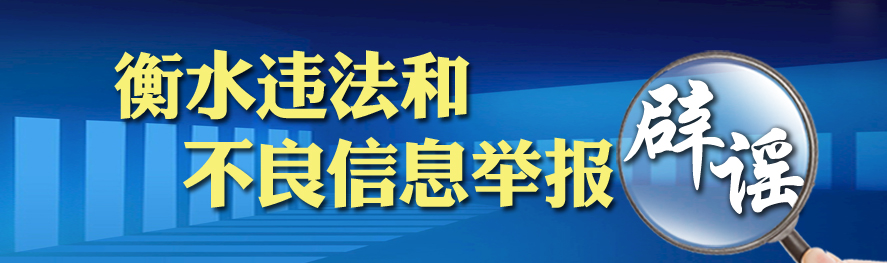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