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22日,在陕西丹凤县武关镇毛坪村原第一书记段海波陪同下走进“贾平凹故乡”棣花古镇。这里是作家贾平凹生活了19年的故乡,也是他获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秦腔》的原型地,小说里的清风老街就是棣花古镇。
棣花在山里,在比秦岭低一些的商山里。它“北通秦晋,南连吴楚”,曾是商於古道的重要驿站。早年因盛产棣棠花而得名,唐代诗人白居易曾三过棣花,留下了“遥闻旅宿梦兄弟,应为邮亭名棣华”的名句。在小说《秦腔》中,贾平凹把棣花镇的风土人情和山水景色写进了书里,吸引各地的“粉丝”纷至沓来。
走进古镇“宋金边城”大门,扑面而来的是尘封已久的秦、楚、宋、金、当代等多种文化形态的交织和融合,既有先秦文化的温柔婉转,又有大宋汉民的含蓄内敛,更有金人游牧民族的粗犷豪迈。流经棣花的丹江水哗哗作响,伴着老人嘶吼的秦腔,和贾平凹一样,有着迷人的多面性,引我深入探寻。
在一个地势较高的地方,是“平凹老宅”和“贾平凹文学馆”。迎面是仿铜浮雕墙,贾平凹坐在椅子上,上面有他创作的那些大部头作品《商州》《废都》《白夜》《土门》《高老庄》《古炉》《极花》《秦腔》《高兴》《老生》《山本》《暂坐》等书籍的封面。贾平凹曾经说过:“当初我自己爱上了文学,就决定一生投奔它,朝夕厮守,相依为命。”他的这种“不忘初心”的执着理念,数十年笔耕不辍的精神,令人敬佩不已。
“平凹老宅”是典型的商洛民间土坯房,起脊瓦房,屋内摆设古朴简单,再现了贾平凹儿时的生活场景。“贾平凹文学馆”展示了贾平凹70余年的成长经历,包括他的童年和少年、求学经历、文学创作过程、书画艺术方面取得的成就和荣誉,生动描绘出一个人多姿多彩的人生画面。
平凹先生家宽阔的大门口上方,悬挂着他自书“嘉祥延集”四个字的木牌匾。圆木门槛自西向东,斜出有30度,两尊雕纹抱鼓石跟着斜角对称,大门也顺着斜过去。我问段海波这是什么寓意?他说,之所以门口斜着,是为了与对面的笔架山正面相对,这是他心中的神山,一座带给贾平凹泉涌文思的山。由于对面的山峰被绿树遮挡住了,所以我们在此看不到笔架山。
径直走进东面的“平凹之家”,房里挂着一幅平凹先生身穿乳白色风衣的画像。他抬脚走路,坦荡从容,眉藏万端忧思,眼纳八面来风。下面摆着一圈玻璃柜,里面放着他从小到大的各种生活学习用品:儿时戴过的帽子、穿过的草鞋、用过的算盘、拉过的二胡、手写的语录牌牌……
“平凹之家”左侧的一间小屋里,住着贾平凹的弟弟贾栽凹老人,他和陪同我来棣花的段海波是老熟人。他比哥哥个子要高一些,温文儒雅,不卑不亢,热情地招呼我们坐下,喝茶,吃樱桃。交谈中得知,贾栽凹1954年生人,比贾平凹小两岁,中学语文教师出身,后改行从政,到退休一直在丹凤工作。段海波说:“栽凹老师现在是贾平凹研究专家。”栽凹老师谦逊地笑笑:“哪里,哪里。”房间里的书柜、桌子上摆放着贾平凹各种版本的著作,像个书店。我买了一本2005年作家出版社出版、2023年12月第50次印刷的长篇小说《秦腔》,扉页有平凹先生的亲笔签字。我请栽凹老师也签上名,他提笔写下了“好读书一生受益”,并在贾平凹的名字下面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走出平凹老家向右手边看,只见墙上写着“去高兴家”几个字。我们带着好奇,按照箭头指引的方向走过去。院子里有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只见他身穿红色唐装,头戴凉帽,眼神狡黠,满脸的喜庆。海波介绍说:“这位是贾平凹小说《高兴》里的主人公刘高兴。”刘高兴与贾平凹是同村、同学、同桌的发小,比贾平凹大一岁,一起耍尿泥、割草、背柴、上学、挣工分。刘高兴以务农为生,因生活所迫,农闲时打工于西安等地,在西安走街串巷卖蜂窝煤和收破烂度日。他虽是社会底层人士,但生性乐观豁达,热爱生活,唱着秦腔种着地,乐乐呵呵去打工,把平凡琐碎的日子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在西安,贾平凹到过刘高兴打工的工地和父子俩居住的工棚,感触于大时代下每个人的命运,要用他的笔致敬那些从农村到城市来的打工者们。于是,贾平凹以刘高兴为原型,以生活花絮为主要内容,历时三年创作出了长篇小说《高兴》,并于2007年出版。主人公刘高兴工于心计,善于做事,热爱生活,喜欢整洁,又颇具爱心和责任感、正义感,且有儒雅风度。小说被导演阿甘拍成同名电影,走红于《疯狂的石头》的演员郭涛饰演刘高兴。一时间,刘高兴火了,自己也拿起笔来写了一部五万字长篇小说《我与平凹》。刘高兴成了大名人,棣花街标有“刘高兴家”的导向牌,凡到棣花古镇旅游的人必去寻找刘高兴。他屋子正中间挂着贾平凹给他写的书法“哥俩好”,墙上贴满了他与贾平凹的合影。我买了一本刘高兴编著、商洛市文联编辑出版的《我和平凹》,虽是内部出版,也算有史料价值。我请他在扉页上题字,他用毛笔欣然写下了“读书是福”。
从刘高兴家出来向西,下坡,过桥,就是贾平凹长篇小说《秦腔》里的清风老街。小说采用疯子引生的视角来叙述。清风街有两家大户:白家和夏家,白家早已衰败,因此夏家家族的变迁演变成了清风街、陕西乃至中国农村的象征。小说通过清风街近二十年来的演变和街上芸芸众生的生老病死、悲欢离合,生动地表现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型给农村带来的震荡和变化。
此时已临近中午,清风街上的游人并不多,大清堂药铺、白雪家、引生家、万宝酒楼……和《秦腔》里一模一样,脑海里不时浮现《秦腔》中动人的故事情节。慷慨激昂的秦腔,穿越千年历史而来,在棣花古镇翻开《秦腔》,对照那些写入书里的原型和对话,你会忍不住微笑,这样鸡零狗碎的日子是多么美好。
和清风街一起“活”过来的还有宋金街。过了宋金桥,走进宋金街,一脚踩两朝。宋街最显眼的方块状装饰表现出大汉民族的温和本质,金街竖条形则表现出大金民族的好战特性。南宋时期,这里是宋金议和的地方,二郎庙与关帝庙并排而立,是陕西省现存唯一金代建筑,也是全国仅存的3座金代庙宇之一。当年二郎庙前有一魁星楼,魁星之笔尖恰恰指到贾平凹家房脊,故乡人传说贾平凹是魁星点出的“商山文曲星”。
走在大桥上,我终于看清了面对贾平凹家大门口的笔架山。翠绿的山峰呈现出笔架一样连绵起伏的形状,殷殷期待着贾平凹和与他同时代的作家们,拿起如椽巨笔,记录新时代的“山乡巨变”,描绘更壮美的风光,书写更恢弘的气象。
作者:杨万宁 编辑:李耀荣







 广告
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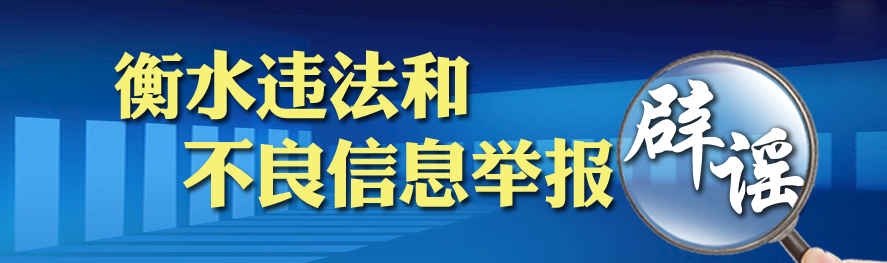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