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商业街到大学门口有十七条斑马线,三条已经斑驳,白线沾着零星黑块,大小各异,微微凸起……”罗淑欣就是这样以寥寥数语将我们带入她写的《斑马线》的。现在,我姑且就把故事的主人公傅睛与罗淑新当成一个人。
陈旧、平常的斑马线,城市中屡见不鲜,但总是让人视而不见,然而,这等微不足道的物象与能说会写的罗淑新成为知己后,便有了她“千车装也装不完,万船载也载不尽”的写作素材和写作可能。
斑马线也不是平白无故地与罗淑新交好的。父亲带她去舞蹈班,外婆陪她去上学,她和母亲提着半米高的卷纸回家……可以说,很早以前罗淑新就与斑马线建立了关系,也正因这由来已久的关系和印象,又巧合了她居住的楼上每每打开窗子那组斑马线便成了她推也推不出去的风景。于是乎,看到斑马线,想到斑马线,哪怕是在某个时间她忘记了斑马线,但在意识世界里,那斑马线,都如嘀嗒不停的钟表,始终存在她的左右。这当然也成了罗淑新写作故事的源泉和动力。
外婆蚝油炒生菜的味道她要写,不呛人的蒜香她要写,饭菜的热气让眼镜蒙雾她要写,甚至是她撩起睡衫的小细节。这些再平常不过的生活细节,换一般人不会产生半点感觉的现象,缘何会引来罗淑新大珠小珠落玉盘似的笔下生花呢?我想这一定与她走过的、学习累了(或是说烦闷了)站到窗前能让她看上很长时间的斑马线有关。那斑马线是罗淑新擦燃灵感火柴的磷面,是罗淑新聚拢材料,剥离嘈杂的隔音墙,是罗淑新避免伤及眼睛的防蓝光眼镜。在这里,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核心内容得到了充分体现,即条件反射。
由此以来,她与母亲、姥姥的代沟叠加;她与英语补课老师美思间的心理感应,以及深深浅浅、走走停停、颠三倒四的思维碰撞;她与父亲的“心照不宣”;她在成长过程中看到、听到、想到,甚至是一闪而过的东西,无不接受着斑马线的暗示或牵引,甚至是恰如其分地煽动。因此,我不能说斑马线给了罗淑新什么,但我能说斑马线是罗淑新的一小时生活圈。
以利益获得为标准,谁给了谁什么不好说清;以达到某种目的为标准,谁给了谁什么同样不好说清。就如斑马线,它真的成就了罗淑新的写作吗?它真的让罗淑新完成了绝对想要的文学表达吗?我觉得没有。虽然这组斑马线在小说的行进中时隐时现,但它并没有像有脊椎动物的脊椎一样,支撑和架构着整篇小说的灵魂和取向——我们没有看到能让人物为之伤心劳力的悲痛,也没有看到能让人物因此兴奋而念念不忘的恩惠。它只是有意无意做了罗淑新的依靠,或是说它是导致罗淑新自言自语的始作俑者。一如罗淑新写过的自己那样——当“想说却不知道怎么说清楚的话,小说替我说”。
话又说回来,我们为什么要时刻守着“人物性格、背景事件、历史站位、精神面貌与时代意义”的小说主题定义不变呢?为什么不可以,从轻生活的角度出发创造一种“轻文学”呢?如果这个设想成立,我认为罗淑新作出了尝试,而且很成功。她让人想起了20世纪80年代“哗啦啦下雨了,看到大家都在跑,叭叭叭计程车,他们的生意是特别好……”的《雨中即景》。还让人想到了那首诙谐风趣的歌曲《不老的爸爸》。虽然,小说与歌曲没有可比性,但文学记录本真生活的轻松写法,完全能够作为枝叶充实在文学的大榕树上,从而让时代的文学更加枝繁叶茂。
等宽等长等距的斑马线,从写作的角度去谈论似乎有点垃圾,但面对写作高手,它似乎又是很好的能源,这正应了人们所说的,世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儿的能源。小说素材的能源何尝又不是呢?我祝愿年轻的罗淑新在写作的道路上不断开发新的能源。
作者:吕乃华 编辑:李耀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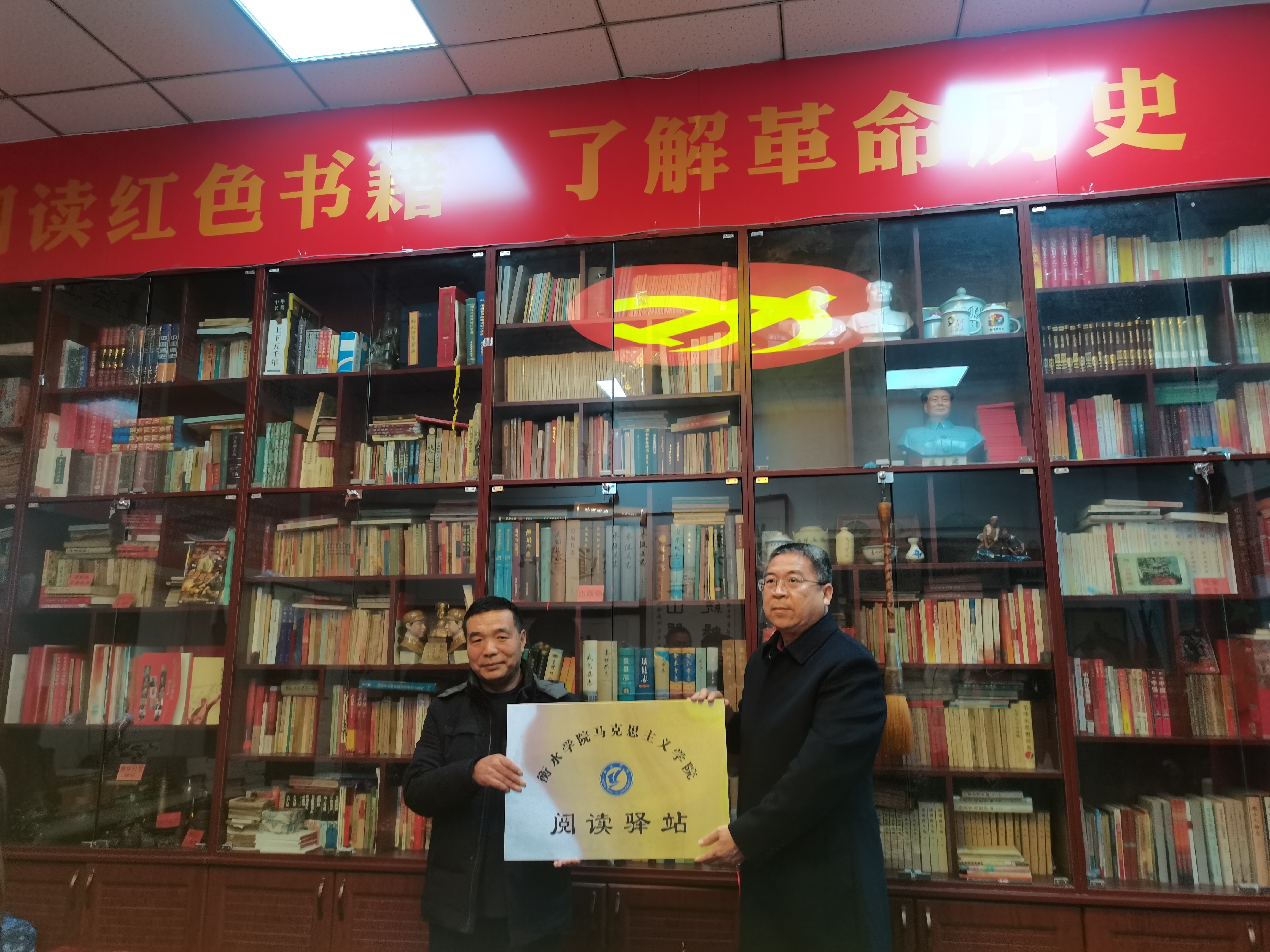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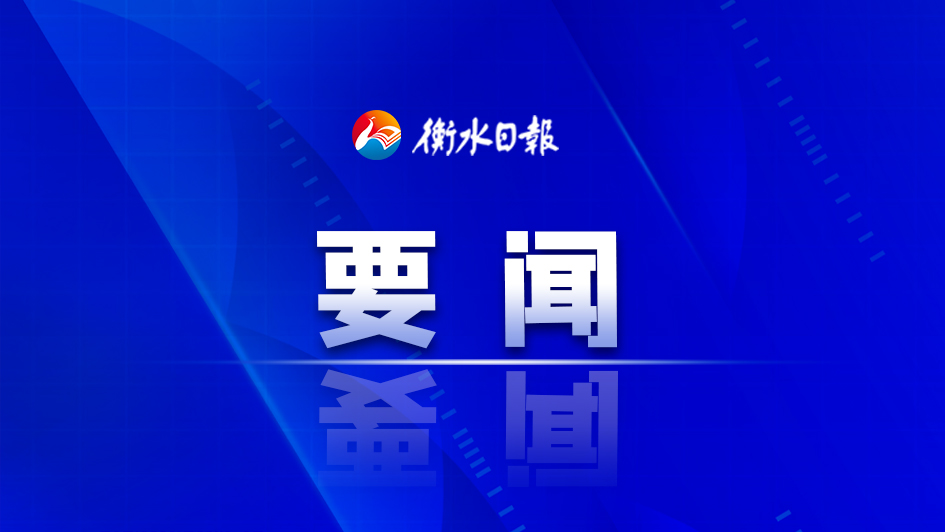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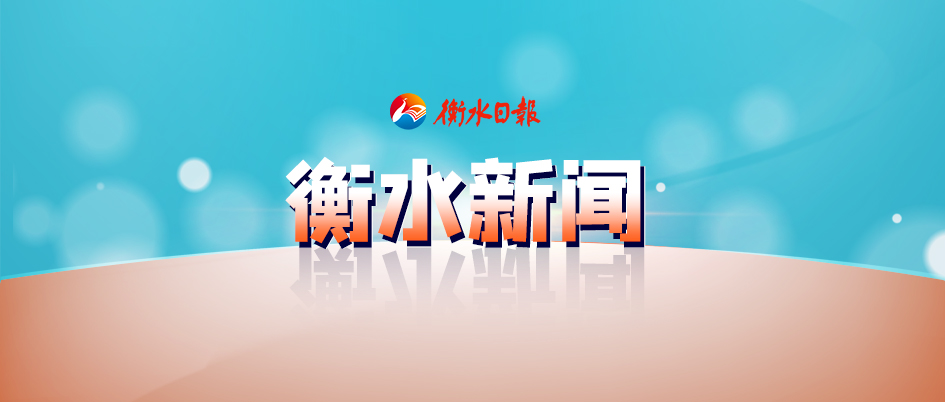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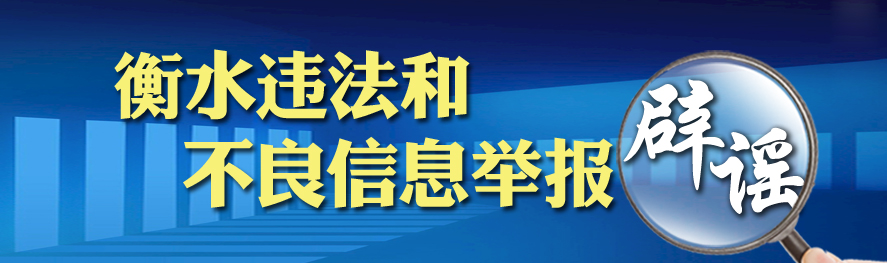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