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去世两个月后,父亲也走了。
两个月的同一天,仅相差了两个时辰。
人们都说,这是老两口感情亲近,不愿先走的那一个在地下等待太久。
回到老屋子,物件景色依然,却再难觅熟悉的身影。在心底最深处,有一方天地永远陷入了黑暗,他们就在那里永远沉睡,无论我怎样呼唤,都不再醒来。
散落满桌的药品,零乱的沙发床铺,不再运转的输氧机,都记忆着他们与病痛的斗争和离开的匆忙。
老家的院子里,父亲亲手栽种的数十株树木,在渐暖的春风中茁立,却再也见不到赋予它们生命的那个人。
整齐的家庭电话号码簿上,写满了母亲的正楷小字,那是母亲从小练毛笔字的童子功。而今,字迹依然,握笔的人已沓然远去。
长明灯轻轻晃动,仿佛在诉说着一生的苦痛。
柱香烟雾缓缓飘散,像在追忆生命的各个片段。
叠满花圈的新坟,宣告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金庸在《倚天屠龙记》后记里写道:“张三丰见到张翠山自刎时的悲痛,谢逊听到张无忌死讯时的伤心,书中写得太也肤浅了,真实人生中不是这样的。因为那时候我还不明白。”
在生命的四十多个年轮里,我也曾数次参加亲朋好友的葬礼,见过了许多生离死别,还曾在文章中描写过一些类似场景,可当父母真正离开的那一刻,我才知道,曾经的理解是那样的肤浅而苍白。
花谢会再开,春去还复来,可人生的永别,就是那个人和那个人的一切,都永远地消失在岁月深处,可关于他们的记忆,却亘久地镌刻在当事人的脑海。在午夜梦回,在阳光高照,在阴雨连绵,在大雪纷飞,只要一转念,那张脸孔就扑面而来,那关注的眼神就凝满泪水,那些熟悉的细节就不断重放。对他们的思念,已成为生命后半程最牢固的生活习惯,直到最后自己与这个世界永别的那一刻。
而生命,或许就是一场接一场的永别,一场接一场的记忆接力。
父亲临走前三个月的一个早上,我过去看他,他正蜷缩着坐在门口外一张破旧椅子上,微闭着双眼,神情倦怠而萧索。瘦弱的身体在寒风中轻轻颤栗,仿佛深秋挂在树梢的一枚枯黄叶子。
我问他是否想吃东西?他说去打份豆浆吧,别的也吃不下。
买回来,他却只喝了几口。他说吃得少,身体弱,或许走时就不那么疼了。
生命的尽头是谁也逃不掉的,这尽头的前端,便是无尽的伤痛。
他说如果能帮他找到一种方法,能够没有疼痛地离开,最好。如果实在找不到,那就和病痛熬着,他亦不惧。
熬着,是父亲的一种生活态度。熬着,就是平视、就是对峙、就是坚持,无论是面对生命的坎坷、身体上的病痛,还是生活的变故,父亲从未低头,从无畏惧。
他一生刚强,独个支撑,做成了许多大事。知我性情柔软,还曾告诫我,不坚强,难做檩和梁。
其实,在孩子的心中,父母就是孩子心房的檩和梁。
父亲伤病最痛苦时,曾数次呼喊母亲的名字。
那些呼唤,或许母亲已听见。或许在另一个维度里,父亲也听到了母亲的回应。
梁已离开,檩岂独在?
而今,坚强的檩梁已断。
但檩梁虽断,信念永续。
他们留在尘世间的血脉,也已长成了独挡风雨的檩梁。
父亲临走前和我说:“我走后,你会给我写篇文章吗?”
我推脱,别想那些事儿,一切还早着呐!等明年开春儿天暖和了,我带您回老家去!
可谁承想,最寒冷的冬天忽然就来了。
我带他回到了老家,不过是以另外一种方式。
望着窗外明媚的阳光、轻掠的飞鸟、渐暖的春意,我闭上眼睛。
不敢一转念。
作者:何 童 编辑:李耀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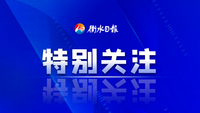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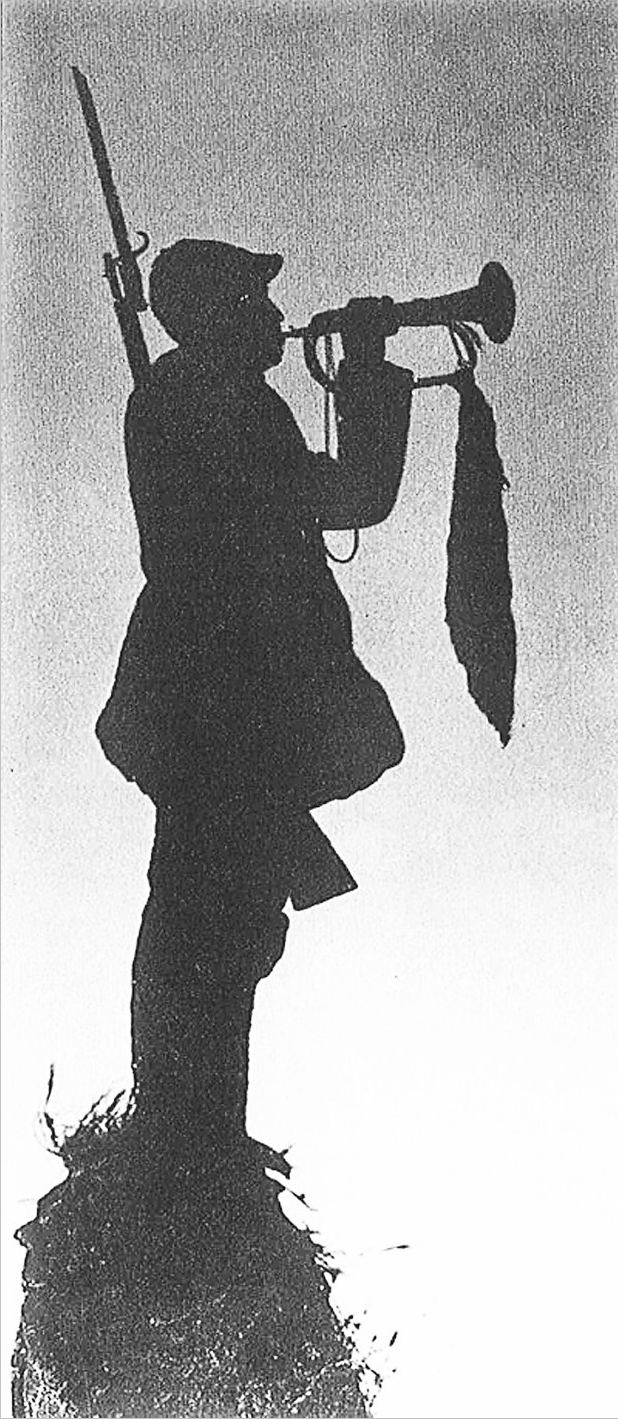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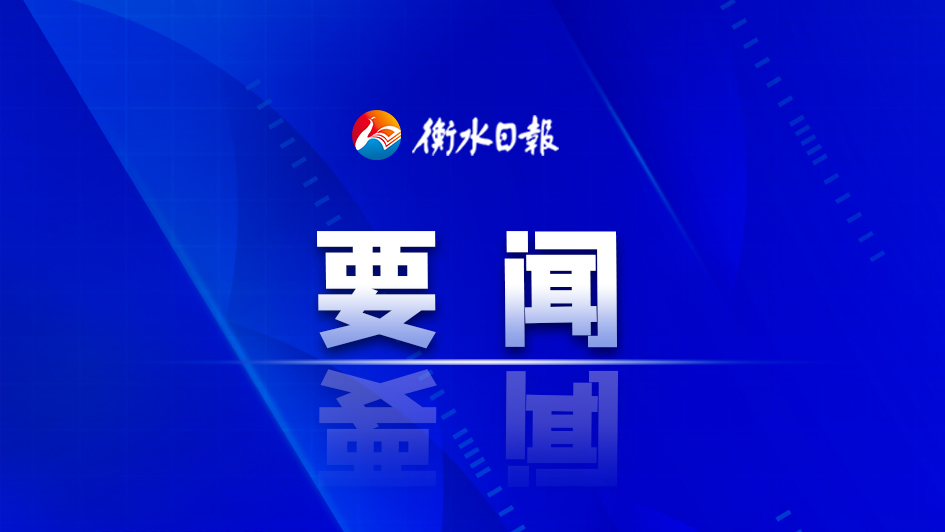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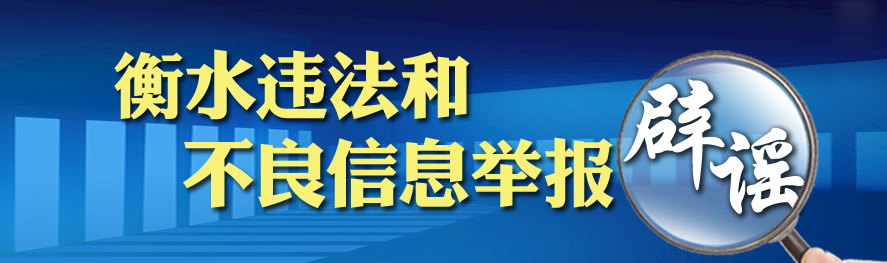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