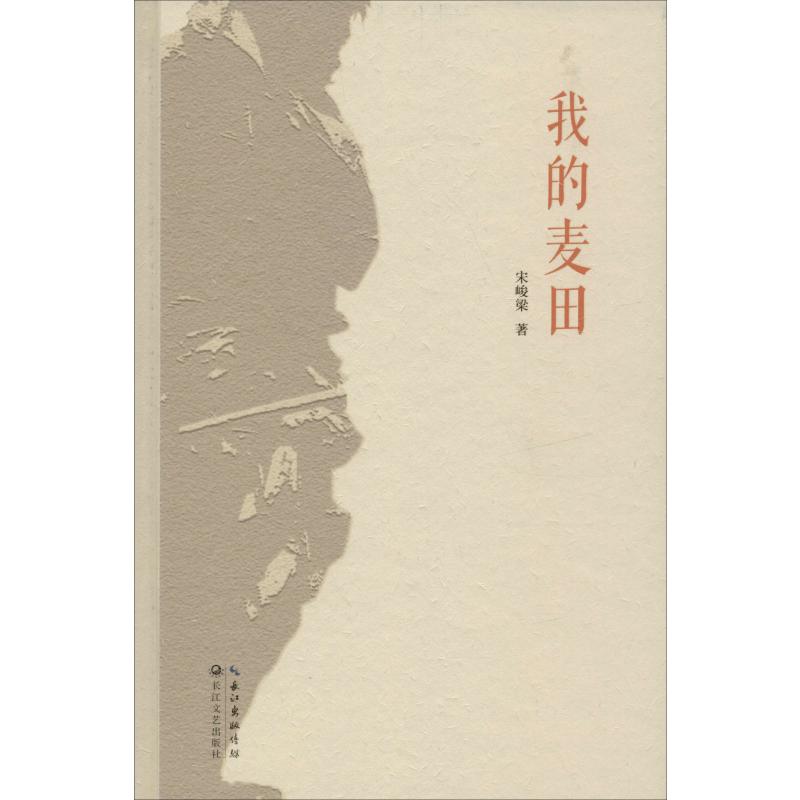
对乡土的讲述,我们的诗人和小说家都走过了辽远而多歧的道路,他们曾经漂泊异域,用田园牧歌似的优美笔调赞美咏叹乡土的生活秩序、自然风光和被加工过的人情人世;也曾站在现代文明的立场上,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地批判那些前现代的落后和愚昧;还曾在思想意识的路上跑得更远,乡土只是他们安放作品的三脚架,在种种解构之后,他们用变形和夸张的形式,写出藏匿在乡间的暗黑和魔幻。宋峻梁显然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要在这三者之间寻找更加适合当下时代和作者愿望的表达方式,他把乡土与梵高、海子的诗意想象结合在一起,与个人的成长经历和社会变迁紧紧相连。在他的笔下,乡土并不是自维的,甚至也不是客观的存在,它是被文学、艺术、历史建构的存在,是自我的语境,个体在这里发现并辨认自我。
宋峻梁的诗集《我的麦田》尽管作者自称是“献给我的父亲母亲,献给我的故乡”,似乎是直指诗人的童年记忆或者乡土书写,但仔细阅读后会发现,“我的麦田”虽然把乡土作为了所指之一,却早已超越了这种一般意义上的惯性指称,而指向更多元,更含混的象征。要在梵高的《太阳下的麦田和人》《麦田上的鸦群》等作品与这部诗集之间建立联系并不是一件牵强的事情,二者都在“麦田”的表层意象之上用色彩和语词描绘了生命、力量,并试图在有限的表现领域内探索个体与周遭世界的关系。另一个关于麦田的著名意象来自海子。《我的麦田》显然有向海子致敬之意,第三章《村庄史》扉页上就引了海子《熟了麦子》一诗:“有人背着粮食,夜里推门进来”。基于此,我们大可以把宋峻梁的“麦田”延伸向乡土、历史乃至人类文明发端之处。
诗集一共六章,首尾相连,贯通一气,叙事性与抒情性、思辨性兼顾,既是“我”外出、游荡、返回的个人史,也是人与乡土,与历史在不断讲述中重建联系的发现史。诗人在传统史诗所惯用的游历、寻找母题中注入了更多思考和诘问,将传统史诗的讲述故事转向讲述自我,在漫长的寻找中完成对自我的讲述和发现。第一章《游荡者》为全书的叙述带入了一位在城乡间“游荡”的主人公“我”,他将成为全书在幕前活动的最重要角色,成为观察、感知、讲述的主体,为诗人代言。关于“游荡者”的命名很容易令人联想到现代派诗歌中的“流亡者”形象,但与“流亡者”将流亡作为反抗确定性和意义感的存在方式不同,宋峻梁的“游荡者”显然已经走过了那种决绝而轻率的否定,他说:“我没有迷失/我保存各种可能和怀疑/我一直走在路上”。
我们随着“游荡者”,走在人生所有可能的地方。他在田野,看“村庄很远又很近”;他回到南方的租住地,“在大片的废墟边徘徊”;他“曾坐在山顶/俯视下面的万家灯火”,“也曾在大海边听着潮声入睡”;他“骑着骆驼奔跑过荒废的都城”把“曾经生活的城市的方向”作为“那一刻我奔跑的方向”。为什么要这样游荡呢?诗人既无意在浪漫主义美丽的大旗下寻找远方,也没有致力于在游荡的过程中验证现代主义或者后现代主义的虚无颓废,他说:“我想反复确认这个世界/每个地方都与我有关。”毫无疑问,这句话非常关键。这既是“游荡者”的自白,也是诗人有意点出的全书主旨。在游历中寻找自我,在讲述中确认自我,在历史中重建当下。
叙述从《游荡者》开始,当“我在土地里翻身醒来”,第二部分《影子》开始了。《影子》宣告了“我”在城乡间游荡的结束,这一部分的表述空间被基本限定在村庄外围。“我”在这里观察、窥视着村庄和附属于村庄的土地、动物、植物,最重要的是“我”在这里发现了另一个“自我”:“你是神么/是什么神/三头六臂/火眼金睛/或者只是一只猴子/只是浑身尘土的风/挂在树上不下来”。“他”亦即影子,回答说:“我是你啊/傻大个”。宋峻梁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讲述“我”与“影子”的对话,在对话中不难看出,“我”对以“影子”角色出现的另一个自我充满了怀疑、讽刺、不屑;而“影子”则毫无芥蒂地致力于缓解“我”与环境的龃龉。影子说:“在你入睡后/我星夜赶路/到你曾经去过的地方/见你曾经见过的人们/帮你向每个你辜负的人道歉/向每个帮过你的人道谢/也许我会请他们喝杯小酒/我会掏一元纸币/给过街天桥上/残疾的乞丐/你曾经视而不见/硬着心肠走开/我也会走进你痛恨的/曾经带给你屈辱的人的梦里/替你打他一巴掌/让他忽然醒悟你的善良”。显然这是自我一体两面的分裂与对话,二者之间的互否令人不安却并不违和。
第五章《我的麦田》无疑是全书最华彩的部分。诗剧的形式为本节带来最多样的表现手段和最丰富的表达内容。众多人物被诗人召唤到“麦田”,在这里上演了一幕幕充满自白和诘问的活剧。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歌德的大型诗剧《浮士德》,尽管从体量上来说二者并没有可比性,但诗人向前辈致敬之意还是有迹可循的。诗剧共分六幕,以“贼”的闯入始,以关于“稻草人”的旁白终。稻草人是最熟悉麦田的人,却并不是麦田的拥有者,农夫农妇才是,他说:“我自己已经成了/一座正在发芽的十字架/或腐朽的十字架/成了麦田里最高的墓地/只不过谁也不会感到害怕/也不会对我肃然起敬”。在第二幕中,他为贼讲述自己,“城市里我生活过,爱过/甚至死亡过/大街上众人如一/没有人知道我是谁”;第三幕中,他引贼去看那些“夜间的事物”,“我看到一群人正从麦田起身/借着月光/擦拭身上的液体……”那里,有盗墓人、有鬼魂们、有死去的国王、有财神、有判官。稻草人和贼的对话在第二幕中还主要是对自我的讲述和怀疑,到了第三幕,他们的诘问和怀疑扩展到了神的存在。贼在追问:“神在哪里?我从未见过/谁是神/你是否能一一指认”?稻草人的回答并不像回答,他说:“未来的孩子们……他们一出生/便介于神与人之间”;说:“那些早早被封为神的人/一直没有被推翻过……我知道他并不太信这一套/只是做做样子骗一下”。实际上,诗人在这里谈到的神并不明晰,是指代来自印度或者西方的宗教信仰,还是中国民间的鬼神崇拜?但不管怎样,在稻草人和贼的对话中神被调侃,被怀疑,被一一解构,神并不能为人带来精神皈依,甚至不能使他们感到平静安全。正如宋峻梁在《后记》中说:“是前往神的寓所,还是还乡?人的精神皈依问题是个大问题。《我的麦田》选择了后者。”
第四幕的《小舞台》算得上剧中剧,无论是唱歌的女学生们、还是拍照的新婚夫妇,都在向我们展示生活美好、热情、充满阳光的一面。自从“希望”最后一个被从潘多拉盒子中释放出来,它就支撑起了人类面对未知的勇气。诗人也许是借着青春少女和处在最大幸福中的新娘来表达他对世界的美的赞赏和爱意,但他甚至不能让这种赞赏保持到这一幕结束,“一个满脸污垢的女子闯进麦田,头上插满鲜艳的花朵”。大概就像鲁迅在《药》的末尾,给夏瑜坟上添一个花环,是要在一片晦暗中增加一些希望和亮色;诗人让疯女人闯入,正是在一片光明美好中添一些绝望和凄厉,让所有的肯定中生长出否定的元素。
第六幕麦田复归宁静,但这宁静里有喧嚣之后的荒凉沉寂。稻草人的自我束缚和贼的不断逃离俨然是人类的一体两面,他们不断怀疑,不断诘问,在现实面前溃不成军,却又强大无比地始终不肯放弃思考:“这里不是你的/也不再是我的/空空荡荡的大地上游荡的全是/未曾安息的灵魂/我爱过的依然会爱/恨过的依然会恨/烙印就像皱纹一样堆积在我心里/无法改变的事情太多了/这骚动而又寂静的大地/仿佛绝境/仿佛一只巨大的手掌/这就是我的故乡/这片土地也曾经是祖先们的废墟/然而我无法拍打家门/我回来了,可是我想住在麦壳里/虫洞里,我想住在/我自己的身体里/这些草这些花枝这些破布/我也厌了/麦田是我的怀抱,忽然消失/土地是我的墙,它横亘在那里/趁着夜色,我们离开吧/去哪里不重要。”当稻草人有了离开的念头时,贼说:“我要做你的背影,你在这里/我就在这里/做你的另一面/我克服了惧怕/但我还没有克服孤独。”他们的表演结束了。麦田曾经容纳了人类一切的历史和现实,悲哀和快乐,也必将继续容纳人类的未来。人类一直不断地从麦田出发又回到麦田死去,却从来不肯安静地待在原地。他们不能停止流浪,不能停止探索,他们既是麦田的稻草人又是被追索的贼,麦田束缚他们又包容他们,他们只有在跟自己和麦田的对话中才能真正找回自己。
于是,就有全书终篇《我在》。在这里,所有人和物都成过眼云烟,只有村庄和“我”依然:“村庄的中间是一条道路/一个方向通往城市/另一个方向通往没有墓碑的坟场”;而我:“我在同所有陆续到来的和曾经相遇的事物妥协”“作为一个消失过的人/我在重新嫁接生活”。
现代社会发展到今天,个体的现代性焦虑已经成为一个普遍问题。人成为了“原子化”的自我,在宇宙人生中茕茕孑立,只能活在当下,对历史与未来都充满了茫然之感。与之相伴的是新时期以来文学对“人”的重新发现逐渐演变成对“自我”的过度迷恋,现实中的自我中心主义与诗歌中的私人化叙事相呼应,诗歌成为表现自我的手段,自我迷失在诗歌语言的迷宫中。我们一直在追问,我是谁?《我的麦田》虽然有部分“村庄史”的属性,但归根结底还是一部关于“自我”的游历和发现史。麦金太尔提出了“叙事性的自我”的概念,他认为,一个人的人格构成表现为这个人一生中首尾一贯、意义明确的各种活动及其叙事,这是在特定的历史传统中或社会脉络当中展开的,个人的生命意义感的形成也是与这种历史和社会密不可分。每个人都是有故事的自我。《我的麦田》完美演绎了麦金太尔“叙事性的自我”的论述,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表达方式,一种把乡土和所有经历作为个体记忆和存在方式的亲切的表达。
作者:吴媛 编辑:李耀荣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