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诗词的力量不容易被发现。一部词曲俱佳、美轮美奂的《西厢记》,不仅让普救寺史上留名,还将四大皆空的佛门净地演绎成为老百姓心目中的爱情主题公园。
峨嵋塬头高达三十米,脚下是一条自东而西、直达蒲津古渡的马路。正是因为马路的关系,如今游人们无法从山门进入普救寺前的广场,只能在小镇的街口下车,沿着一排商贩摊位喧嚣而过。正面的山门反倒只可从背面约略参观,再回转身来细细端详刻有“普救寺”大字的歇山飞檐式照壁。照壁之后,广场中央立着一把涂金的同心大锁,锁上毫无避讳地直书“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天下寺院不谈情,唯有山西普救寺。毋须进门,仅此一语就道明了伟大的爱情主题。
根据出土文物考证,普救寺或初建于南北朝末年,名西永清院。隋唐两代多有修葺。至五代后汉时,河东节度使叛乱,郭威领兵征讨,围蒲州城而久攻不克。寺中问计,僧人直言:善待百姓,城池可下。郭威折箭为誓,果然攻破州城。有誓为先,城中百姓得以保全。因此禅院更名普救寺。普救寺得名的由来,坊间大都采信此说。值得一问的是,《莺莺传》原文中已写有普救寺名,而此篇传奇作者元稹生活于唐大历至太和年间,与后汉政权建立前后相差近一百五十年。这又如何解释?《莺莺传》最早见于宋太平兴国三年成书的《太平广记》,难道有宋人因普救寺名而篡改原文?此说显然缺乏说服力。经查,《太平广记》收录《莺莺传》一文转自唐末陈翰编著的《异闻集》,故事原题《传奇》。既然是唐末成书,其地名差讹当不复存在。可唐末原著《异闻集》已佚,宋代所见《异闻集》一书中,偏又混入了宋人故事,其可信程度已严重降低。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一书中指出:“《莺莺传》为微之(元稹)自叙之作,其所谓张生即微之之化名,此固无可疑。”显然他的考证重点不在普救寺名称的由来,这是不是也从侧面说明普救寺名出现在元稹的笔下已是合情合理的事情了呢?
入得寺门,小行片刻,便依塬而上,第一个平台即到“勾心斗角”、气势雄伟的大钟楼。从此地开始,我们每到一处,都可与《西厢记》彼此对应。比如这座大钟楼,正是《西厢记》“白马解围”一折中的观阵台。张生为解普救寺之围,特搬来好友白马将军救急。两军交战之时,张生邀请老夫人和法本长老等僧众共登大钟楼观战助威,为大破敌阵生擒孙飞虎齐声喝彩。
经过塔院回廊,攀登中一昂首,眼前一座高塔直插云天。在我旧有的印象中,佛塔总是出现在寺院的最后方(因为供奉着佛祖舍利),至少要建在大雄宝殿之后。另有一旧识——只有建有大雄宝殿的寺院方可筑塔,此说忘了出处,又一时无从查考,先行记在这里,待专业人士指正。此塔建于塬顶最高处,更是建在大雄宝殿之前,令我破除陈规。该塔初名舍利塔,后因《西厢记》名声大躁,只得依照世人俗称莺莺塔。夕照昏黄,镀塔成金。塔尖之上,有一群暮归的乌鹊盘桓回旋,晚风中时起时落,短啼长鸣。“鹧鸪声声不堪闻,莺莺塔前月影深。西厢院外有情痴,一本传奇唱到今。”居高临下、俯察一切的宝塔想必也见证了张君瑞与崔莺莺的爱欲交结与悲欢离合吧。
莺莺塔的奇妙之处在其匪夷所思的回声效果。据传在塔周围十五米左右的距离内拍手或击石,就能听到从塔底传来清脆悦耳的蛙鸣声。如果再退后五米,蛙鸣声又自塔顶传来,仿佛金蟾忽上忽下,与人嬉戏。若是在夜深人静之时,扣石一声,神蛙三鸣,且来自三个不同的方向。莺莺塔与天坛回音壁、三门峡宝轮寺塔、潼南大佛寺的石磴琴声并称为中国古园林中四大回音建筑。我伫立塔下,任三两游人击掌或扣石,咯哇咯哇,果然灵验。
香烟缭绕之中,我从众多善男信女跪拜的身后走过大雄宝殿,径直奔向大殿东侧的梨花深院。如果不是耳畔时有诵经声隐约拂过,站在小院天井里,真会疑心是闯入了某一富贵缙绅的私宅。宅门楹联是晏殊小词《无题》中的一联: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细细品味,有市井气,有脂粉气,有七分雅静,又有三分暧昧,这副对联恐怕也是天下寺庙绝无仅有的吧。精致的小院完全依照《西厢记》中的描写建造,任何细节都做足了功课。在东厢房南侧的粉墙之下,一丛翠竹环抱着玲珑湖石,正可做逾墙人的垫脚。墙外是一株高矮恰好的杏树,如此一里一外,共同成就了戏文中的千古绝唱:“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安立在西厢南侧的出土文物“金代诗偈”,诗名刻“普救寺莺莺故居”,跋文载诗作于金代大定年间,最为直接地证实了崔张故事在宋金时就已广为流传。“无据塞鸿沉信息,为谁红燕自归来。”从颔联所传达的诗意可知,崔张的爱情结局并非如戏中所唱那般圆满。
拥有原创版权的元稹的确不是怜香惜玉之人。《莺莺传》的真实结尾是“文战不胜,张遂止于京。”始乱终弃的张生最后以卫道士的口吻四处宣告:“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何其冠冕堂皇!何其大言不惭!这简直是要置莺莺于死地!陈寅恪先生笃定张生即是元稹,想来早已看穿了元才子的薄幸本质。如果有人以莺莺是虚构人物为之辩白,那么投河自尽的刘采春不正是现实版的崔莺莺吗?刘采春年轻貌美,歌艺俱佳,在唐朝歌坛独树一帜,罕有其匹。越州刺史元稹一见心动,旧病复萌。先是摇笔赠诗,博取芳心,后又动用官场资源,付给对方丈夫一笔银子,买断了刘的婚姻。但等消费完毕,保鲜期一过,便又重拾张生伎俩,打起了道德太极。刘采春留有《啰唝曲》六首,首首都是对负心男人含泪泣血的控诉。其一曰:“不喜秦淮水,生憎江上船。载儿夫婿去,经岁又经年。”可怜无名无分、不清不白的刘采春只得携着一腔痴情赴水东逝。
小院后身,缘阶而下,是玲珑周至的后花园。水榭风池,曲桥花亭,全部是依文附会,意思而已。作为历史悠久的十方禅院,普救寺东区还建有天王殿、菩萨洞、罗汉堂和藏经阁等众多建筑,但这里游人稀落,古殿沉默,分明都做了待月西厢的陪衬。出得寺门,回首仰望,一轮明月高高升起在峨嵋塬头,朗照着长长的蒲坂和雄浑壮阔的黄河水。日月无私,亘古照明。普救众生,非无私无以脱离苦海。同样,爱情的高尚之处亦不在相互占有,而在这“无私”二字。
作者:贾九峰 编辑:李耀荣
 广告
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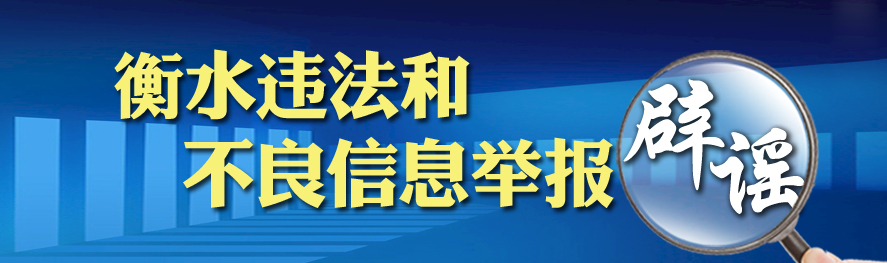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