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童年时家在华北平原一个小镇的南街上,最以为傲的是我家有盏电石灯。
这盏灯“长得”很特别,灯体是用纯铜制造的,粗如胳膊,高有尺余,重达四五斤,通体油光锃亮,一圈洋字码刻在底部。分上下两节,上部为盛水舱,下部为电石舱,用螺丝扣旋紧成为一体,顶部有一个很神奇的“宝贝”,像是刚刚从灯体里长出来含苞待放的花蕾,那是灯芯。它的边侧是一个旋钮,是用来调解灯苗大小的,旋钮螺杆底部呈锥形,正好与上下舱之间的锥形漏洞吻合。此灯制作精美,设计巧妙,对当时的我们来说是个不可多得的宝贝。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农村还没有电,一到夜晚漆黑一片,只有那豆粒大小的煤油灯头能带来些许光亮。那时特别期盼着过年,只有过年才能点亮那盏电石灯。每到农历大年三十的下午,我们兄弟几个就会争着抢着去东耳屋的顶棚上取下那盏灯,把它擦拭得锃亮,再从大号茶色玻璃瓶里取出适量电石,放入灯的电石舱,把盛水舱加满水,上下舱结合后旋紧,待轻轻地打开灯的旋钮,水舱的水会一滴一滴浸入电石舱,电石即刻产生了气体,气体通过灯芯冒出,一见明火,即可变成耀眼的火苗,照得整个房间亮如白昼。
电石灯的火苗是湛蓝色的,风吹不灭,给大年三十的晚上带来一片光明。街坊邻居、大人孩子们会循着那灯光来到我家的院子里,向爷爷奶奶拜年问好,还会羡慕地说上一句:“真好!这灯又点上了……”我们这帮孩子会在灯光下尽情地玩火把、放鞭炮,好不惬意!那些年每当电石灯亮起,爷爷就会讲起抗日战争时期发生在电石灯下的故事,故事里的英雄让人肃然起敬,难以忘怀。
抗日时期,爷爷在自家胡同口北侧开了一家杂货铺,这是南街上唯一的一家杂货铺,因生意兴隆,晚上不打烊,提供照明的就是这盏电石灯。
爷爷说,那时候每当夜幕降临,电石灯一点亮,街坊邻居、亲戚朋友,串门的、经商的、耍手艺的都会奔向我家的杂货铺。人群里也夹杂着日本兵和汉奸,其中,皇协军李大疤拉是常客,他傍着日本兵来铺子里白吃白喝,还随意打人骂人,人们恨得牙根疼。
有天晚上灯又亮啦,爷爷的朋友也是小店的常客,聚源皮货栈账房孙先生来到店里,与爷爷寒暄一下坐在一隅。不一会儿,李大疤拉又像往常一样来了,孙先生若无其事地喝着茶水装作没看见,眼都没瞅他一下。李大疤拉喝了一通后有了醉意,抹抹嘴,拿上烟卷晃晃悠悠地出了门。他出门半袋烟工夫,孙先生突然起身,冷不防地把水杯子扣在了电石灯灯芯上,灯立马灭了,满屋子、满大街一片漆黑,爷爷好生纳闷,孙先生平时是很稳重的人,今天怎会这样呢?他忙问:“孙先生你怎么啦……”孙先生不急不忙地说:“对不起,刚才我的头有些晕乎,不小心把杯子扣灯上了,我现在就把灯给你点着……”灯亮啦,又恢复了平静,就像任何事情都没发生一样。
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一个惊天消息传遍小镇,头天晚上,汉奸李大疤拉被人杀死在西街日本宪兵班的门口,身上还有一张告示,上书“汉奸的下场,八路军枣南游击大队”。爷爷听了这消息觉得很解气,八路军为民除了一害。
解放以后,孙先生变成了我家的邻居,爷爷这才知道他是地下党员。他说,当年经常光顾爷爷的小店是为了搜集日本鬼子的活动信息,灭灯一事,是里应外合向外围的游击队员发出的锄奸信号。哎呀呀!这时爷爷才恍然大悟,当年还在无意中配合了一把锄奸行动啊!嘿嘿嘿,了不起啊!
时至今日,已有了各种各样的灯,那盏电石灯早已被束之高阁,但是,当年在它的照耀下发生的故事我们一直铭记心间,就像那蓝色的火苗一样永不会熄灭!
作者:杨志信 编辑:李耀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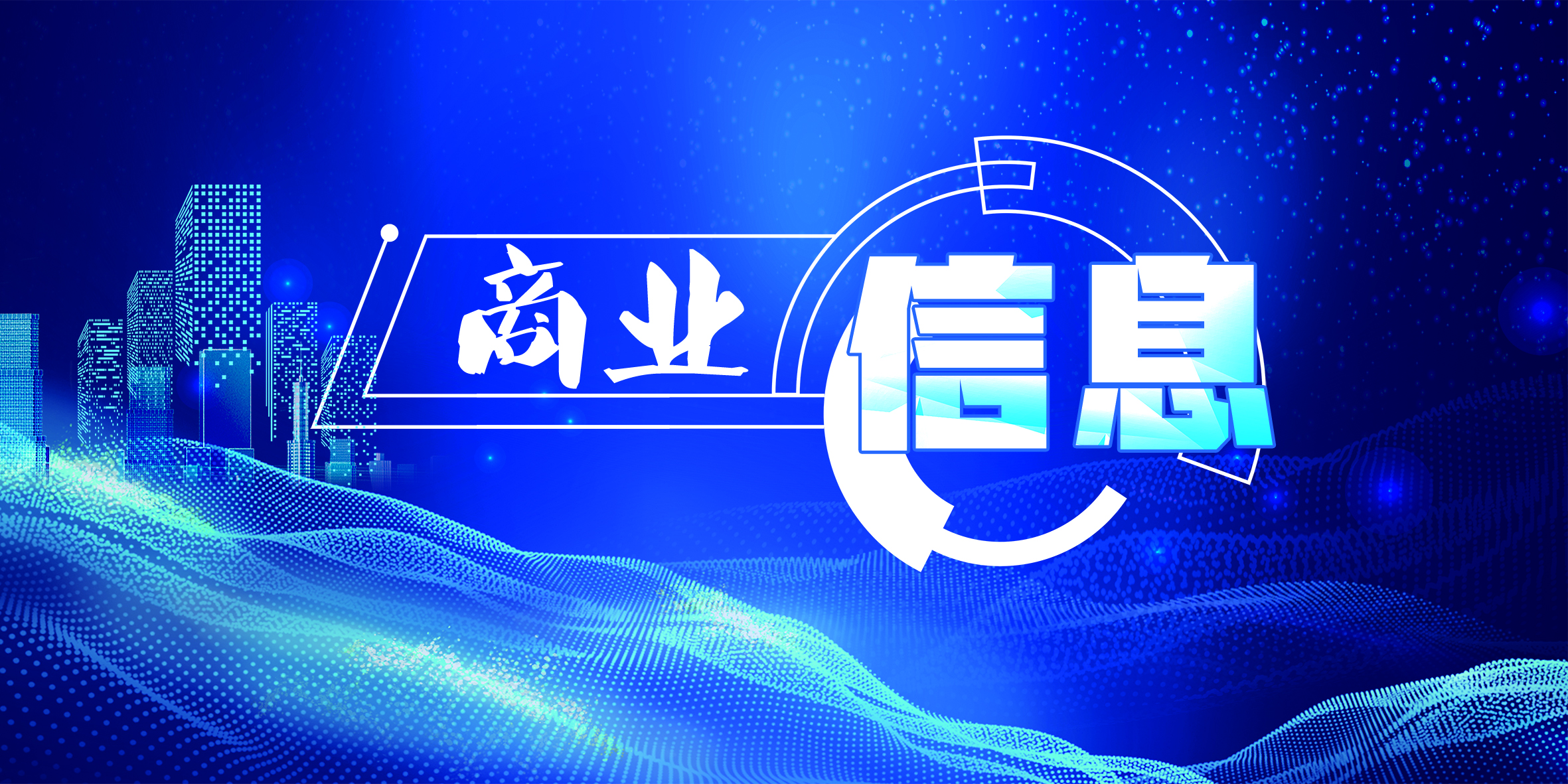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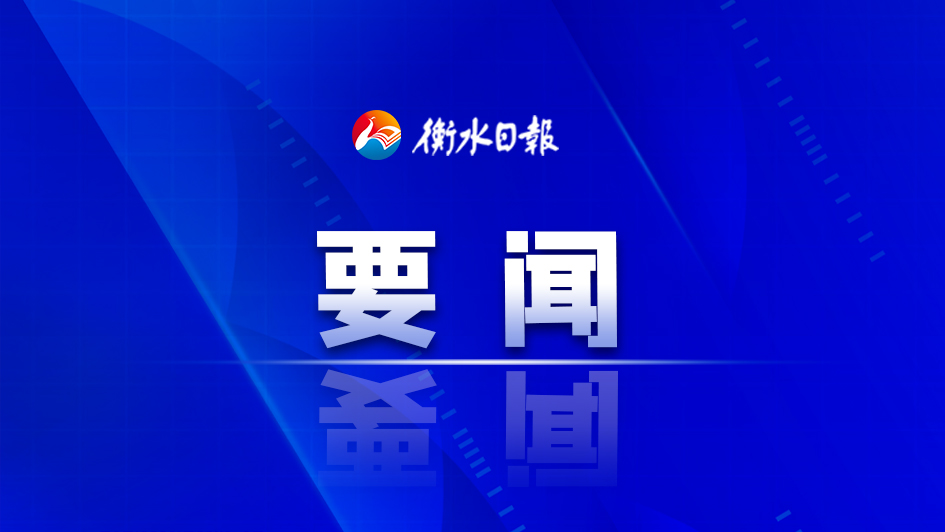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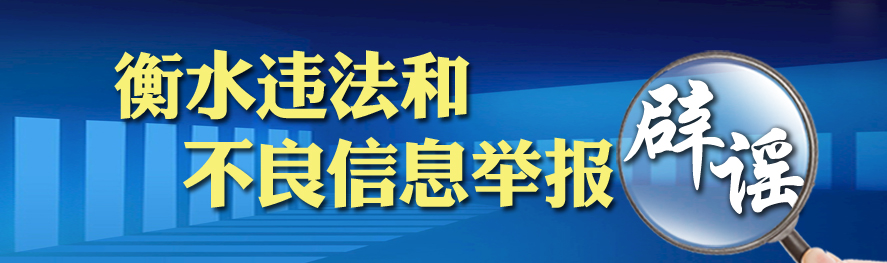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