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村熏肉
滕章申

在武邑县西桑村的晨光里,总晃着个一瘸一拐的身影。谁家娶媳妇摆宴席,哪年除夕宰猪杀羊,这个身影准会出现在烟火最盛处。他是王福来,村里人更爱叫他“王拐子”——不是不敬,是带着疼惜的熟稔。这位伤残军人,虽然腿上还有淮海战役中留下的弹痕,却把日子过成了一炉温吞的烟火。
养伤那几年,王福来跟着师傅学了熏肉的手艺。退伍回村,腿脚沾不得泥土,他便在供销社的食品店里安了身。旁人看他走路蹒跚,可一拿起刀来,腕子稳得像钉在案上;熏起肉来,火候掐得比钟表还准。煺毛、切块、熬汤、熏制,每一步都透着股利落劲儿,仿佛腿上的不便全顺着肉香飘走了。出锅的肉往案板上一搁,油光裹着酱色,咬一口,肥的化在舌尖,瘦的带着嚼劲,连骨头缝里都浸着香料的醇厚。乡亲们总说:“福来的熏肉,吃的是味道,暖的是人心。”
岁月爬上鬓角时,王福来体力渐衰,便喊来侄子王红星搭手。这后生眼亮手勤,看叔切肉时刀与案板的节奏,记熏制时糖烟起的浓淡,没多久就把全套手艺揣进了心里。王福来看着他在灶台前忙碌的背影,眼里的笑意比灶火还暖——手艺有了传人,就像老树根上发了新芽。
改革开放的风一吹,西桑村的集市活了起来。王福来的另一个侄子王红彦,在村口开起“红星饭店”,请了堂弟王红星掌勺。灶台上的火光里,王红彦的儿子王保迎总蹲在旁边看,看堂叔怎么把砂仁、八角的香气融进肉里,怎么让糖烟在铁锅里转着圈儿给肉“上色”。三年时光,他手上的燎泡结了又消,终于能独立把一锅熏肉做得香气绕着村子飘。王红星看侄子的手艺扎实了,笑着辞了职,转身带着儿子在县城开起了“熏肉店”,让那股子烟火气飘得更远。
王保迎两口子守着饭店,没丢了老规矩。凌晨天刚泛白,就去挑带皮的猪肉,猪头要肥得匀,猪蹄得带着筋。泡肉的水换了又换,直到血丝褪尽;香料按祖传的比例配,砂仁增香,白芷去腻,山楂干藏着解油的巧思。汤锅烧开时,蒸气裹着肉香漫过窗棂,街坊邻居就知道,保迎家又在“喂饱日子”了。
最讲究的是最后那道熏制。铁锅烧得发白,撒上白砂糖,滋滋的响声里,琥珀色的烟卷着热浪往上蹿。肉方皮朝下摆在箅子上,盖上锅盖,糖烟就在锅里打着旋儿,把每一寸肌理都染透。十分钟后掀盖的刹那,香气能惊飞檐下的麻雀——那肉红得像浸了晚霞,熏味混着肉香,深吸一口,连骨头都要酥了。
后来,王保迎又琢磨起熏肠。五花肉切成细条,拌上姜碎、香油,裹着不稀不稠的淀粉糊,灌进洗净的肠衣里。用线绳捆出一节节,下锅浸熟,再经糖烟一熏,外皮就成了透亮的棕红,咬开时油星溅在舌尖,香得人直咂嘴。有人说这肠像西桑村的日子,看着朴实,细品全是滋味。
如今,王氏家族的熏肉铺子散在各处,你传我个新配的香料,我教你个省火的熏法。铁锅上的糖烟还在冒,就像王福来当年一瘸一拐走过的路,虽有坎坷,却把日子熏得愈发醇厚。这口从军营传到乡村的香,早成了西桑村最暖的底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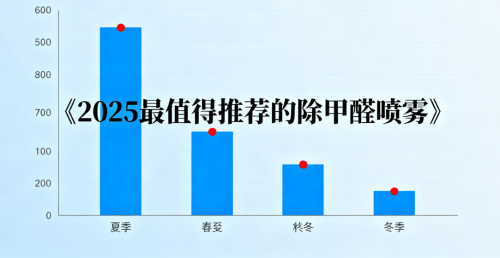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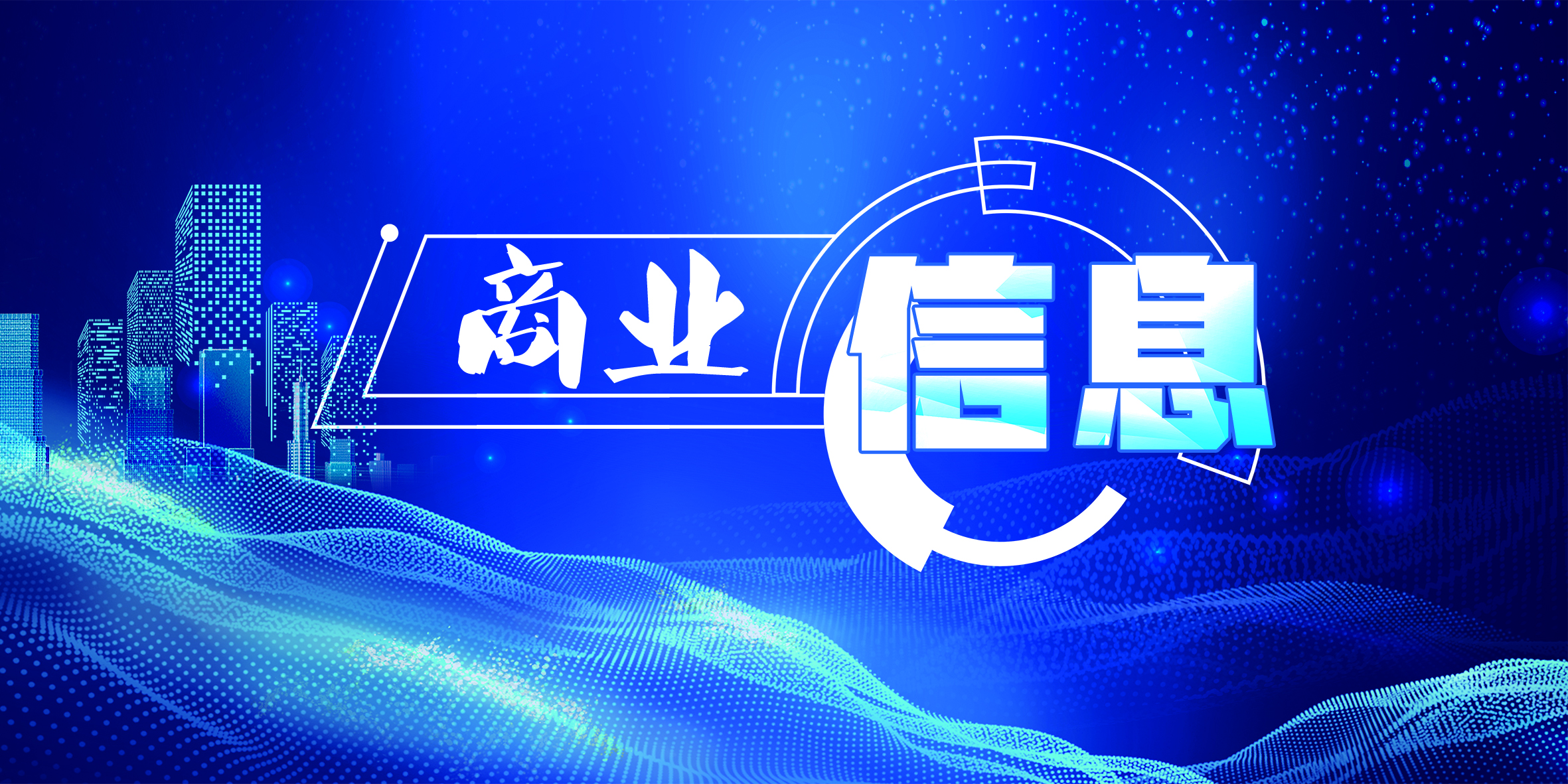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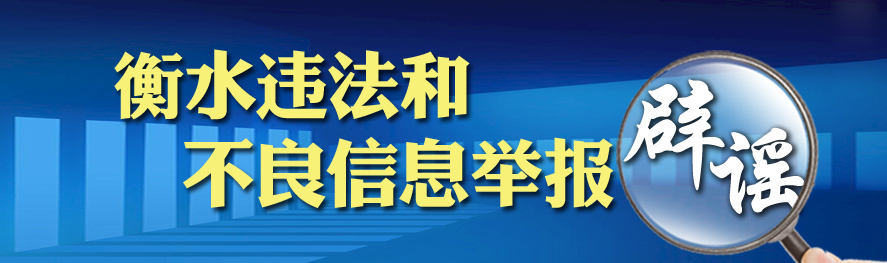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