镌刻乡愁 绵延根脉
——谢继忠和他的“小榆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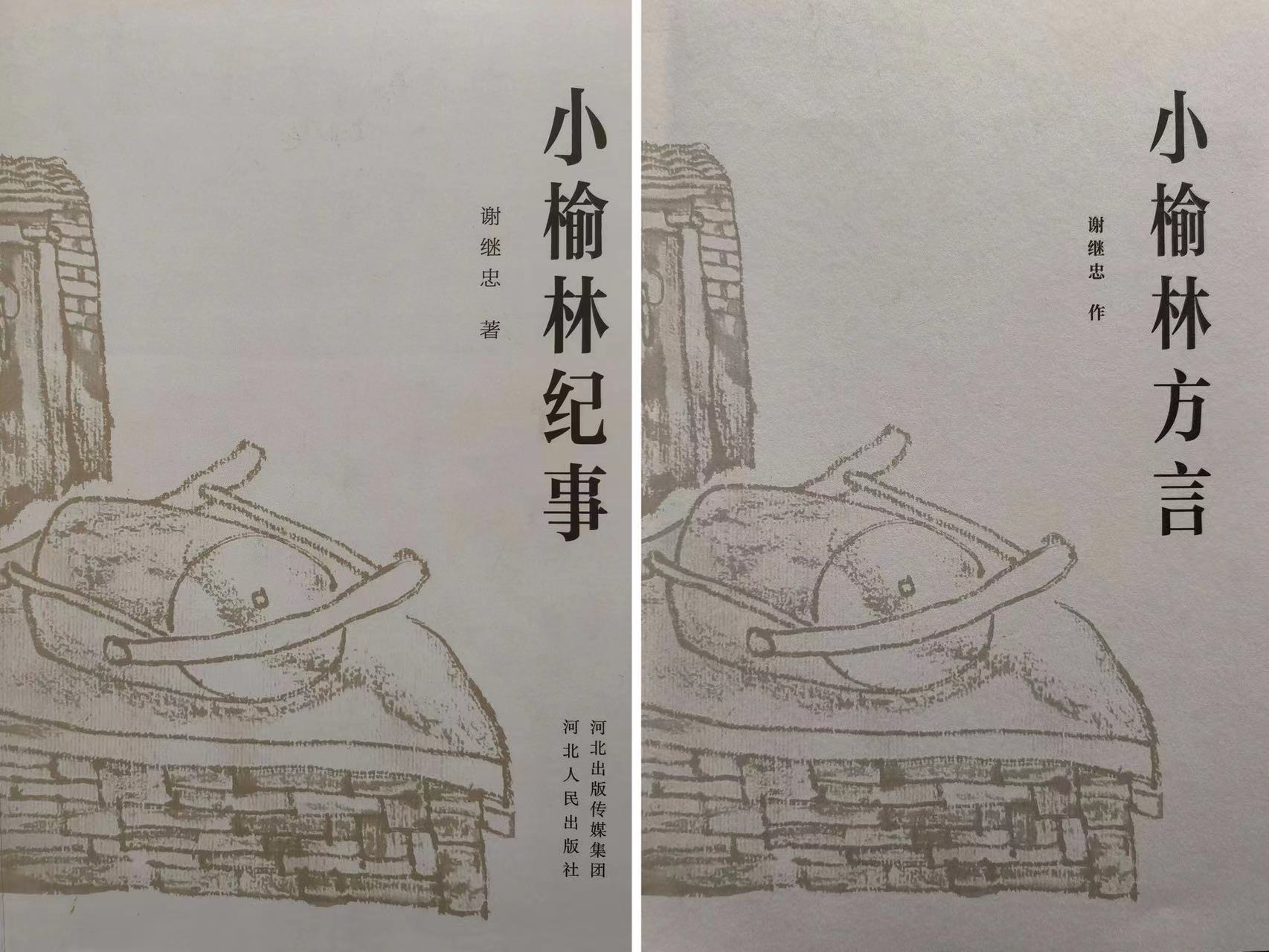
年事已高,87岁的谢继忠老人健康状态让家人很是担忧。他前些年做过两次心脏手术,现在日常起居几乎都在室内,能做的事情变得有限,除了在电脑上浏览资讯、修改书稿文字,就是练习书法,上下午都需要吸氧。这位一辈子没怎么离开过家乡的老人,被人们称作“乡贤”。他曾说,这辈子做了两件事:从教40余年桃李芬芳;70岁起与乡友、亲朋合作,历时10年写了一部村史《小榆林纪事》。不久前,作为“副册”的《小榆林方言》辑印成册,让老人颇感欣慰。可以说,这两本书几乎凝结了他一生的心血。在数十万字的书稿中,记录着乡野民间的文化记忆,作者对故土乡邻的深情厚爱……
抗战烽火里度过童年
1937年12月,谢继忠出生在距深州城东10公里的小榆林村。村子位于滹沱河故道南侧,相传古时候黄河、滹沱河曾流经此处,多年前附近有过不少沙坡、土岗,长着很多枣树、榆树,村庄也因大片茂密繁盛的榆树林而得名。虽然村名中有个“小”字,这里却是个大村,尽管后来被307国道分为了南、北榆林两个村庄,现在合计仍有3500人左右。“小榆林”文化底蕴较为深厚,有过关帝庙、私塾、文武学校、小学堂等,也曾有过架鼓队、子弟班。
谢继忠的长子、北京画院专业画家谢永增说,谢家祖祖辈辈都是庄稼人。他们居住的谢家旮旯在村庄东北,往南走不远是“官坑”。从家里文书匣子中保存的一些祖传地契可以看出,这家人从清初开始陆续购买土地、宅基,经过数代人的积累,慢慢有了一份家业。这家人有着浓重的孝道传承,谢继忠的曾祖父谢斐文曾是村里的“三大贤”之一。然而,谢斐文这辈往下横祸连连。到了谢继忠父亲这辈,家中只剩一名男丁,有20亩土地和一个三家共用的6亩大圈墙院落。当另外两家要卖院子的时候,谢继忠父亲“紧紧腰带”将其买了下来,祖传大院得以“重圆”。那时,他们在村里算是中等人家,房屋都是土坯房。
谢继忠姊妹7人,他是家中长子,上边三个姐姐,下边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在《小榆林纪事》中为数不多感性色彩颇浓的段落中,我们可以看到谢继忠童年的影子——小时候,他和小伙伴曾一起在“官坑”夏天玩水、冬日溜冰,有次不慎落水被乡邻救起;一大家人在一起吃饭,讲究“长幼有序、男女有别”,有很多“规矩”,小孩子想省下点碗底的粥喂猫会被制止,认为是“不爱惜粮食”;晚饭后,姐姐刷完锅小心翼翼把如豆的油灯端进里屋,他趴在炕桌上就着光写字,一大家人围坐闲聊,小猫在脚下“念佛”(打呼噜);一次,年幼的谢继忠读书认不出“佩”字,漆黑的夜晚,父亲提着自制小灯笼送他去附近一位名叫谢金凯的长辈家求教——清末到民国时期,小榆林村的文化人多出自殷实人家,20世纪初村里读过书的不过十几人,绝大多数村民不识字,但对文化都有着天然的敬意与重视。
那些温馨的记忆其实并不多,也很短暂。谢继忠的童年,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里度过的。
1938年,小榆林已有20多名共产党员,成立了党支部,建立村公所,实际掌握村政权,秘密领导村民开展抗日活动。当时,村里还有一个公开的村公所,俗称“维持会”,专门应付日伪军。1941年,日本人把岗楼修到了小榆林村北。“五一扫荡”前,谢继忠的父亲谢志德为保护党的干部,曾和几个村民一起给深县锄奸科特派员挖过藏身的地窖。
1943年,小榆林在村里的杜家爨儿恢复了村小学。孩子们拿的是两套课本,日常学习共产党油印的抗日课本,学唱抗日歌曲,日本人来了就把书藏在脚下,拿出日伪石印教材装样子。年幼的谢继忠曾在这所学校短暂学习过一段时间。
年幼时的经历、见闻,对人的影响是深刻的。耳闻目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感受到亲人乡邻义无反顾投身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激发了谢继忠朴素的爱国热情,埋下了他日后为小榆林留史的情感脉络。
1945年深县解放,村小学搬到了韩家爨儿,谢继忠正式入学读书。这时学校有了正规课本,《国语》《算术》和一本薄薄的《修身》。村小学只有四个年级。小榆林村的孩子们读五六年级上“高小”,要去附近的榆科镇。冬日夜长,“高小”组织学习小组,老师分别包村督导。一次,检查谢继忠所在小组学习情况的,居然是他的父亲……
重重压力下努力求学
深州西面紧邻辛集。地缘上的接近和当时辛集中学在河北省的名气,使得深州学子对那所名牌中学有着热切的向往,甚至有“摸摸辛中砖,死喽也不冤”之说。小榆林在深州城东,距离辛集中学45公里,相对较远。1952年春节第一次报考时,15岁的谢继忠和小伙伴步行前往,走了不到一半路程,脚上就磨出了血泡。更让他遗憾的是,那次成绩并不理想。之后,谢继忠学习更加刻苦,终于在当年6月第二次报考时,如愿被这所“名校”录取。
那年9月,父亲赶着牛车走了一天路,护送谢继忠和同村好友谢平福一起入学。待安顿好,已是暮色深沉。父亲为了让谢继忠安心,说自己找地方休息一晚再回去。后来谢继忠才知道,父亲连夜赶了回去,到家已经是次日清晨,劳累程度可想而知。每每回想起来,谢继忠总是唏嘘不已。
在辛集中学6年的初、高中学习,是谢继忠一生难以忘怀的记忆。强烈的上进心和来自家人的关爱,是他发奋苦读的原动力。当时,学生宿舍条件非常简陋,檩条上的秫秸箔顶棚都发了黑,泥抹的土墙没有光皮,泛着一层土面,铺板长短不齐薄厚不一,卫生条件也不好,让父亲都隐隐担心,生怕出安全问题。不过,他还是一再叮嘱谢继忠,不要太在意生活条件,好好学习是最重要的事。直到初三,谢继忠才搬进了条件较好的宿舍。他记得,北院的新宿舍红瓦尖顶、白灰墙、玻璃窗,地上墁着砖,屋里配了包裹架,宽敞、明亮、舒适。
全新的课程、可敬的师长,严格的校规校纪、丰富的课余生活,让谢继忠开阔眼界、增长见识,也磨砺了品格。聆听朝鲜回国的“排雷英雄”姚排长和战斗英雄李连长讲述战斗经历;观看人生第一场电影《白毛女》;第一次做生物实验;参加学校的长跑队,到了高三下学期还每天坚持锻炼……学校场地有限,他和同学一起奔跑在乡间土路上,迎着风挥洒汗水,回校后一洗一擦浑身舒服,头脑清新,学习效率也提高了。谢继忠是个本分的学生,一直在中游班,也曾得到过老师们的鼓励、夸奖,这让他有了自信的一面。教导主任陈西,语文老师靳荩臣,数学老师王子贞,体育老师曹澄泉,音乐老师贾登,历史老师刘普义,身有残疾的物理女老师郭瑞华,化学老师赵萬安……几十年过去,那些如父如兄的师长们的亲切面容,还常常出现在谢继忠的脑海。
让规矩的学生变得“不规矩”,一定是有不太寻常的原因。1958年,曾有一阵“大辩论”的风气。一次回村,谢继忠见到不善言辞的父亲正在被“批判”。出于少年本能的义愤,他要求上台为父亲辩解,不想却造成了自己的悲剧。村里给学校去信,影响了他的高考成绩。他没能考上心仪的医学院,被山西农学院录取了。
谢继忠在山西学习了几个月,被强烈的失落感压得透不过气来,与一个心境相似的同学作伴,退学了。父亲心情复杂,却没有责怪他一句。
在外求学的这6年,谢继忠锤炼了自己的文化基本功,除了增长知识,更是增长了见识。这样的经历是撰写村史必备的素质。
教学生涯中感悟良多
回家次日,谢继忠得知榆科工委文教部正在找代课教员。从此,他走上了教书育人的道路,在乡村县城的小学、中学工作过,几乎什么学科都教过。
岁月流逝,谢继忠娶妻生子,度过饥荒、经历动荡,有过很多坎坷。在小学支援村里摘棉花时,他领着学生们唱歌,半个村子都能听到。在中学试讲,他的第一堂课是“相似三角形的证明”。老教师提点他:“你就是没上过师范呀,讲课得引导学生动脑,不能代替学生思考”。这话如醍醐灌顶,让他领悟到“教”与“学”的不同。上世纪60年代,他被调到深县教研室任视导员,整理俄语教学经验,培训体育教师,组织参加过衡水地区的运动会,得过第一。慢慢地,他对事业有了自己的体悟:“事业这个‘个体’,具体得琐碎,是对自己毅力和能力的真真切切的考验。若疏于小而不为,就一事无成。不遗余力地干好自己该管的事儿,就叫本分。”
1972年夏,谢继忠调到了榆科中学,最初教高中语文,后来一步步成长为中学校长。他用20年的心血精心打造了一个“宝贝”——全县数一数二的榆科示范初中。这所属于“二类中学”的学校在1990年代初崭露头角,1992年后连续三年初中整体质量超过了重点中学,位居县办中学之首。
随着榆科中学教育教学成果的显现,谢继忠多次受到上级表扬,1995年获得国家教委和人事部颁发的“全国优秀教师”证书证章。他没有留恋岗位,不到60岁就急流勇退,“给年轻人腾地方”,在1996年2月退居二线。
不久,谢继忠接受深县教育局返聘进了县城,相继担任职教中心附中和同仁中学校长,前后有4年。
谢继忠刚到“同仁”时,感觉很不适应。他注意到,有不少“差生”功课跟不上,整天打架,一犯错就“回家反省七天”,好容易回了学校,却依旧没有温暖,落下的功课也没人指导补课,越在家反省,抵触情绪越大,常与老师对抗。
“不要再撵学生回家了。这个反省七天的规矩,废喽吧。”谢继忠下决心改变管理方法,让班主任们报上那些“管不了”的学生名单,给他们开了几次会。讲到“差生”的苦闷时,谢继忠说:“我理解同学们的心情,想学习好,但见不到鼓励的笑脸,得不到细心地指导,抖不起精神来。”这话说到了孩子们的心里,一些学生鼓起掌来,“当学生,学习跟家长种地一个道理,得立足于自力更生,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的帮助上。脑袋是自己的,得积极开动脑筋,越学脑子越灵,坚持下去,咱就不当‘差生’了。”接下来,谢继忠从中挑选了5个需要经常关心的同学,让他们随时可以找自己,并重点指导一个“眼子户”。
谢继忠语重心长地跟相关老师讲:“别歧视功课差的学生。咱的价值首先是为差生服务,脑子灵的学生往往比老师理解得还快。也别要求学生‘一般齐’,都努力学、都进步就好。退一步想,包括我在内,咱们当老师的,上学时有多少是尖子生?那尖子生早到更重要的岗位上去了。无论哪一类学生的未来,都有相应的社会价值,只要敬业就是好学生!”
3个多月后,学校秩序基本稳定下来。2000年,谢继忠查看了全县当年的中考成绩:同仁第一,榆科第二。2001年,还是同仁第一,榆科第二。
回顾20多年的校长生涯,谢继忠认为自己能有所收获是因为坚持了两点。一是“平常心”,二是“一视同仁”,从不歧视功课差的学生。“学生成绩并非一成不变,让每个学生都觉得有奔头,才是正确的管理理念。”
教书育人的生涯,让谢继忠感悟到做人做事的内在底线逻辑,这样的一种平常心与胸怀,让日后的《小榆林纪事》得以平铺直叙,如述家常,带着读者走进小榆林。
盛世修史恰逢其时
谢继忠一辈子在家乡生活工作,对这片土地充满热爱,受父辈和家庭影响,敬畏传统,对过往和历史有种探究的热情。当初他办好“二线”手续后,就开始多方搜集资料,编写榆科中学校史。那时他的心还在榆科中学,一心想让学校好上加好,“成为”自己魂牵梦萦的母校辛集中学。撰写校史,正是记录发展脉络、丰富学校文化底蕴的应时之举。
“修校史”之余,谢继忠开始回忆自己生长的村庄。他每天像上班似的画小榆林村的街道图,还把谢家旮旯的各家庄基演变画成了买卖流程图。可以说,这段经历是谢继忠编写《小榆林纪事》的前奏。
真正离开工作岗位之后,谢继忠有了更为充裕的时间。为过往的记忆“留影”、为自己的村庄“画像”,成为他晚年生活中愈来愈重要的内容。然而,一个人的记忆毕竟有限,力量也略显单薄,如何让心爱的“小榆林”和她走过的历程更加丰满、立体,是谢继忠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2006年1月1日,国家取消了农业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由此告别了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皇粮国税”。这时,距离改革开放已近30年,小榆林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旧事物迅速消失,人们离贫穷越来越远,越来越多的村民萌生了强烈的留史意愿,这让谢继忠有了更多志同道合的伙伴。
国有国史,县有县志,而村史瞩目的是一村之事。“参与的人越多,资料就越全。”谢继忠曾做过一次统计,提供资料的乡亲近百位,其中90岁以上的3人,80岁、70岁、60岁以上的各有30多人,“还有韩钢船、王大于、王大鹏、谢府臣等,若干年轻人。”
“在参与者的心中,这是沉甸甸的历史文化,实实在在的情意。”谢继忠带领村里执著于村事的老者行动起来,说旧事、找素材,翻检家中旧物,相互启发讨论,搜寻着记忆深处中关于“小榆林”的点点滴滴。很快,他们就积累了不少资料。有件康熙年间的文契,是被王大鹏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
“从初见贾新普与其父贾大圈的手抄《杂字本》,到发现笃先生的亲笔《俚语杂字》,用了3年时间。”谢继忠说,百年前私塾先生贾老笃自编过教材,是村民公认的第一本村史,在这次写作过程中被挖掘出来。文字资料还有贾占甫《榆林夜话》中的传说,谢万西回忆录中的家风等。老支书韩庆余写了一沓子手稿,详细叙述土地承包的经过。80多岁的刘双圈、贾双月、韩瑞平,讲述着抗战故事,演唱抗战歌曲,谢继忠想办法用简谱记录下来。
谢继忠很早就学会使用电脑,有自己的QQ号,2010年前后注册了微信。在他的带动下,村里很多老人也开始接触互联网、使用智能手机,跟上了时代的步伐。
通过网络,谢继忠不仅收到了身在异乡的小榆林人发来的资料,还经常和网友交流写作心得,思考调整自己的“史观”。谢继忠认为,盛世难逢,写村史无须多虑,而且人人都该写。“贴身的历史是最鲜活的时代赞歌。村史是基层社会的民情,是上级政策落地的回响。直书史实就是忠于国家,忠于人民。”
“为文之初是无拘无束的,想到哪写到哪,偶尔在QQ空间晒晒笔墨,听听反映。”最初,谢继忠并不知道村史应该是怎样的体例、样式,在梳理资料的过程中,他渐渐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按照史料的属性组织脉络,率意命笔,终于成文——“只是太土气了,没见过这么写的。”
长子谢永增原以为谢继忠做这些事无非是退休在家“找个乐”,并没有放在心上,“久而久之,我发现老爹不光是找乐,而是在做事。”有一年春天,谢永增回家探望父母,晚上睡得早,一觉醒来发现父亲房间还亮着灯。“过去一看,老爹还在电脑前聚精会神。”他说爹快睡觉吧,都12点了,别拿这个当回事。“结果老爹很有力地给了我一句,‘我就是要弄好!’”
那几年,谢继忠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工作状态。睡床上想起一个事、一个词,马上操笔记下来。发现了新情况就立刻转告朋友。半夜或开电脑,凌晨也许打手机。慢慢地,那些以高龄人群的回忆为主体的素材,铺满了小榆林村从贫穷到富裕、从落后到文明的改革过程。
编撰村史让谢继忠体会到,“睁眼都是老师”。他在东郎村的杨兰玉处得知农具犁铧上“铧虚”结构的用途;校工李藏盛告知“扌罪”拼合是“拽”字的“老写”;深州一中杜娜老师协助把简谱顺利转换成PDF版;在南开大学张旭教授帮助下,《俚语杂字》导言中的“焉乌之讹”“元亨利贞之天道”不再费解……“小榆林村史是道地的土特产,是多人心血智慧的结晶,是不掺假的民史、馈赠后世的奶酪。”谢继忠由衷感慨。
历时10年,数易其稿,洋洋洒洒40余万字的《小榆林纪事》初步完成。
2016年腊月的一天,谢永增接到弟弟打来的电话,得知父亲患病。他匆忙赶了回去。躺在病床上的谢继忠说,上午把整个稿子都写完了,心里很松快,结果下午就发烧住院了。
精益求精修订再版
《小榆林纪事》于2018年1月由中华古籍出版社出版,2019年3月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再版;2023年2月,《小榆林方言》辑印成册。2次出版,1次扩容,让谢继忠的“小榆林”越来越精致、越来越丰满,不仅有了“画像”,也让世人“听”到了自己的“声音”。
《小榆林纪事》全书共十五编,前三编主要叙述1937年以前的社会情况,第四至第九编叙述从抗日战争到改革开放这段时间的社会变革,第十至第十四编记述1977年后村庄的改革进程。第十五编是附录,主要体现正文中不便过细交代的资料,包括古文注释、鼓谱、地契、人名列表等。这部村史的初稿曾被命名为《淤埋的村庄》,经过多次讨论推敲,最终定名为《小榆林纪事》。出版时,封面用的是谢永增专门创作的国画,石碾、木门,充满乡土气息。
从书稿到成书,中间有过很多故事。
老辈人记忆中的“小榆林”,如今已被307国道分为了南、北榆林两个村庄。但俩村的新老干部都知道撰写村史的意义,大力支持。谢继忠清楚记得,2015年6月18日,时任北榆林村党支书韩钢船、村长刘明轩,专程开车进城购买打印机和相关用品,随后又请来技术人员指导使用。“韩钢船亲手打印,新老支书共同复印。”2016年2月,为进一步征询意见,韩钢船打印第二稿,韩庆余把复印机搬到家中,晚上加班,复印了60多本,“飞扬的粉末子弄得浑身乌霉灶烟(音,黑乎乎的)。”
谢继忠说,2016年4月,韩庆余带头审核文稿。北京石油的网友王文起挤时间审阅了20页,标点、错别字、土语用字,甚至打字时多了个空格都不放过。5月,深州一中语文教师李庆兴全文审阅,推敲斟酌。2017年,又请4位中学语文教师用8天假期分段看稿。“人们像给学生批改作文似的,多处、多次朗读原文。”
2018年1月27日,《小榆林纪事》首次出版后在微信公众号展示仅4天,1月31日的阅读量就蹿升至10060人,引发了更多的社会关注。
《小榆林纪事》被称作“方言村史”,很多语言表达有着浓郁的深州特色,对身在异乡的深州人来说,有种特殊的吸引力。张永利祖籍深州西蒿科村,毕业于河北大学中文系,是《河北日报》专家组成员,高级记者、编辑。他看到初版的《小榆林纪事》时,心情很是激动,一页页慢慢翻阅,对家乡仿佛又有了新的认识。那些人、那些事,还有那些方言俗语,于他而言,熟悉而亲切。然而,看着看着,他的眉头却渐渐蹙起来。
出于职业习惯,张永利阅读时会像看“报样”一样,不自觉地在页面上勾画。随着标记逐渐增多,张永利陷入了沉思。非专业人士的校订,还是有一些不足。
“《小榆林纪事》是本难得的好书,像一幅长卷,脉络清晰,内容丰富,书写村庄从抗日战争到土地改革、改革开放的历史沿革,是小榆林村的‘清明上河图’……这本书应该做得更好一些。”出于对家乡的热爱,他开始了夜以继日的修订,逐字逐句细看,用红笔一一标记下来,有的人名、地名还需要前后对照。这个过程历时半年多。
勘校完第一遍,张永利在深州一家宾馆与谢继忠见了面,用一整天的时间对接商榷。“书上有的地方我是打问号的,需要跟老人商量,重新订正……老人耳背,交流的时候还得使劲喊。”经过这次“专家级”的修订,又纠正了书中不少谬误,对编排体例也作了一定优化,甚至封面细节都作了调整。
张永利的父亲也是教育工作者,与谢继忠同龄,这让他和老人很有亲近感。在他看来,精神矍铄的谢继忠倔强、幽默、正气,让人很是敬重。“他有一种历史的责任感,也很勤奋,年已高龄笔耕不辍,乐在其中——那时,他基本上醒了就琢磨这件事。这本书可以说是老人的精神支柱和寄托。”
随后,张永利协助联系出版社、对接编辑,再次反复检校。在与同行的交流中,张永利被戏称是“眼睛带钩的”,扫一眼文稿就能看出问题。出版过程颇为繁琐,他却乐此不疲。“编辑的工作相当于美容师,是给这本书‘化妆’。人家本来底子好,但有瑕疵的话,就像是明珠被埋没了一样,应该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再与世人见面。”
2019年3月,《小榆林纪事》由河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入架国家图书馆,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农村发展史”。《衡水晚报》、《燕赵都市报》以及《人民日报》副刊相继报道。人民日报“新书架”栏目对其有这样的评价:“可以说是华北农村的一个特写镜头,体现了编者朴素的爱国爱家情怀。其别具特色的深州方言独树一帜,在语言学、方志学上有着特殊的价值和意义。”
“从头到尾读完这部书,最深刻的感觉只有两句话:这部书确实值得一读;这部书定能传世。”在序言《植根沃土传承薪火》中,作家郭华写道,其语言之生动已经不仅仅是接地气,它本身就是地气的凝聚,从里到外都洋溢着浓浓的地气。但这种地气并不是土气,不是农民的局限,而是站在历史的高地、道义的高地,审视并评判原汁原味的农村历史……《小榆林纪事》就是一部记载与传承中国农耕文化的“农村宝典”。
南开大学张旭教授认为,《小榆林纪事》是一部“良史”,“不仅向读者宣讲了有关我国乡村在前进道路上不断除旧布新的活生生的社会知识,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为我国国史研究提供了最具真实和最有说服力的历史资料。”
河北省政府研究室一级调研员王雪梅看到《小榆林纪事》后,出于对这本村史的敬意,参与到相关研究当中。她曾多次前往小榆林拜访谢继忠,深入交流,写下调研报告《乡村振兴需要村史——<小榆林纪事>带来的启示》。“作者用现代人的目光审视过去的一切,不以拙笔为羞,大胆为文,展现活灵活现的乡村生活情景,也带着我穿越了回去。”王雪梅认为,这本书好就好在是记得住乡愁的村史。“其村史式的描写,本身就是小榆林的情景剧,客观、真实、翔实,没有半点马虎。不仅能成为热心农村题材影视工作者的创作蓝本,更能成为农村题材剧目真实与否的判定标准。《小榆林纪事》找到了村史撰写的好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小榆林纪事》从村子是怎么来的、居住格局是怎样形成的、语言特色渊源、一年四季什么样,以及劳动方式及场面、集市情景、日常生活细节……方方面面,都通过村民的音容笑貌、肢体动作点点滴滴展示出来。王雪梅说,在国内编纂村志正如火如荼之时,《小榆林纪事》创作团队已经呈现给读者40多万字的成果,不仅仅是开了个好头,更对推动村史挖掘与撰写带来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耄耋之年抢救方言
看着全新的《小榆林纪事》,谢继忠觉得言不尽意,还有必要补充内容,将本村方言的认知作个交代,便开始着力编写《小榆林方言》。其实,这部分内容在《纪事》中有所体现,但没有过多展开。张永利形容,“(方言)相当于四合院里的一间小房子,是《纪事》的补充本。”
这间“小房子”,谢继忠一盖就是三年多。王雪梅和他一直保持着联系。她说,老先生决定补写《小榆林方言》时,已然八十有余。“补写过程需要反反复复的对比、校对和深入小榆林调研,这对于耄耋之年的老人是何等的考量。”她从不敢说半句“加油”之语,一直说“弄着玩,弄着玩”,甚至曾劝老人放弃。
2022年1月,谢继忠用微信给王雪梅发来一段文字,告诉她自己征求了一些老乡、老同事的意见,收获了一些补充的方言词汇。“前几天,我发给了那位帮助完成村史的张旭教授,请他审阅。张教授挺认真地浏览、挺认真地修改后,发回来了。该发给的朋友,我也给了,请大家品味一下方言的滋味。”
王雪梅在电脑上阅读文稿,“从变音到变调,从语调到情调,从形态到心意……无不表达出对母体语言的敬畏和还原幸福来路的初心,同时接收到老人传递出来的‘老样子’里的浓浓乡音。”
《小榆林方言》看上去体量不大,59页,2万余字。全书分为三章,“方言与村史的缘分”“小榆林方言的特点”“小榆林方言词典”。《方言词典》的字母排序是按照汉语拼音顺序,而不是从A到Z的英文排法。书中有很多歇后语、“土成语”,比较幽默。谢继忠说,这是不同姓氏的先人们传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应该保留,不至于消亡。
这本书的编辑还是张永利。尽管内容专业性强,比较枯燥,他还是耐下心来逐一细看。作为深州人,张永利对方言土语非常熟悉,他觉得自己做这项工作义不容辞。
前不久,一本《小榆林方言》送到了王雪梅的手里,“我反复地翻阅着书面,纸张发出轻微的唰唰声,好似小榆林人在说话。”她又想起老人常说的那句话,“别小看自己,别小看自己的村,别小看村事。自己老了,巧逢盛世,能在历史的丰碑上雕刻下一丝‘幸福’的来路,就无愧先祖与后人。”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