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的冬天依然是清冷的。村里虽然通了天然气,说让用天然气取暖,也有一定的补贴,可是还是太费钱了,况且村里的房子不像城里的楼房那么严实,村里都是单门独户的院子,屋子又都高大、宽阔,甚至透风,要想烧暖和了,很费气,关键是,辛苦节俭了一辈子的父母哪里忍心花那几千块钱。
几千块钱不多,但在父母的心里,那可能会是派上大用场,或者可以花到更重要的地方去的。
不忍年迈的双亲住在那渐已四壁破败的乡下老屋受冻,就把他们接了来,尽管他们再三推辞,说将就一下这个冬天就过去了。
城里的暖气费怎么都是要交的,多一两个人来取暖,利用价值还高呢。
初来的那几天,一向安静的屋子似乎热闹了起来。父亲每天帮忙接送孩子,母亲也积极地张罗着帮忙买菜、做饭,省了我们许多的工夫和精力,一家人和乐融融。只是有些羞惭地觉得这所谓的“天伦之乐”好像不是他们到城里来依附我们取暖,享受儿孙绕膝的满足与欢喜,倒成了我们三个小辈贪图享受他们所给予的那份习惯性的照顾与温暖。于是大把花钱,去超市买回一堆五花八门的好吃的,让父母尽情饱食。直到他们片刻地欢喜之后,直说“浪费、浪费……”我们也获得了大大的“尽了孝心”的满足。
只是没过多久,这份热闹和乐与安逸温暖便骤然地降下温去。
老父倒没什么,每天除了接送孩子,就是到公园去遛弯、听人唱戏、看人下棋,回到家里吃饭、睡觉,多余的话一句不说。倒是一向嘴和身子都闲不住的母亲,已开始唠叨起这、唠叨起那来,“指手划脚”地要当家。
不是今儿嫌我买的菜贵,就是明儿又说我费电、费水,不会过日子……难得她一片好心,我倒也可省些力气。可令人头疼的是,我没有原则的“放权”和母亲的“一手包揽”,渐渐让这个本来平静的小家里起了“硝烟”。
首先是上中学的儿子,一到吃饭的时候就吊着个苦瓜脸说:“奶奶,咱见天儿的白菜、土豆,土豆、白菜,吃得我一看见这两样儿都想吐了……”
母亲却拿着筷子轻敲儿子的头说:“你小孩子家家的懂什么?超市里那种不应季的西红柿、豆角都是温室大棚里种的,吃不对身体不好……”
但第二天,端上桌的菜还是换了,却不得不让我们大眼瞪小眼地哭笑不得:白菜、土豆换成了萝卜、豆腐。
炒菜的时候,母亲不开抽油烟机。她说:“每天开好几回这机器,不知要费多少电?”
省倒是省了,却弄得屋子里老是有一股油烟味儿;她用洗菜、洗衣服的水拖地、冲厕所,不仅摆得厨房、卫生间里到处大盆小罐,像是布满了地雷,让人难以落脚,还搞得屋子里不是青菜味儿就是洗衣粉味儿。
我劝母亲:“钱不是靠省的,是靠挣的。就算你真的省下十块、八块,也顶不了什么大用,何苦累这份心?”
不料母亲却拉下脸来说:“我不管你们挣多、挣少,反正我看见这么浪费就心疼。东西也好、钱也好,有的时候你们不在意,没有的时候你们就干着急了。那些年,要不是我抠门儿剔缝儿地省,你和你妹妹的大学能上成?!”
我便没话反驳她了。的确,那些年,为了供前后只差一年都上大学的我和妹妹,母亲和父亲吃粗粮、挖野菜,买粗盐、种豆子换油吃,家里15瓦的白炽灯泡都舍不得常开。母亲几年不添新衣、穿了补了补丁的袜子去走亲戚,脱鞋上炕坐席(方言:宴席)吃饭,让人家笑话……这才把我们都供进了城里,落下脚来。
母亲每天把地板擦得一尘不染,窗帘、沙发罩一律都卸下来洗一个遍,甚至把我们的好几条被子、褥子都拆洗一新,而这些,我竟然从来没想起来是要勤洗的。
洗衣机母亲也不肯用,而是跑去土产门店花二十块钱买回一个大塑料盆来,每天在阳台上用手搓洗。我说:“你费那么大力干嘛,又省不了几个钱。”母亲却说,“我的力气和工夫都不值钱,闲着也是闲着。”
但自那次“闯祸”事件之后,母亲就再没动水洗过我们的衣服。因为那天她竟然把我们的两件毛料衣服也给泡进了大塑料盆里一并搓洗了,造成衣服一下子严重缩水,根本就穿不得了。
三千多块!就这样被母亲的节省弄没了。
那次我是真着急了。看着我瞪眼珠子、鼓腮帮子的气恼样子,母亲一下子像个犯了错的孩子,小声而怯懦地说:“我哪里知道那两件衣服那么金贵,只是看着脏了,怕你们穿出去叫人笑话……”
接下来的日子,本来风风火火、里里外外忙不停的母亲似乎一下子变得每天都小心谨慎起来,话也明显少了,轻手轻脚、不敢喘大气地像是走在冰上。
她的“阵地”也渐渐从满屋跑缩小到只剩下“厨房”。家里的气氛突然地安静下来,是我所希望的,因为终于可以不被她呼来唤去地抬手抬脚,擦这弄那,我也可以安心在电脑前码我的字了,可奇怪的是我竟然总是一阵阵守着键盘发呆,没思没路、敲不成句……因为一想到,母亲默不作声地躲在那间小屋里,我的心就纷乱难宁:
不知从何时起,对父母竟然越来越漠视了,不是有心,只是我们被太多太多占据,无暇留一丝时光给他们,忙着工作、忙着应对人情世故,回到家和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只剩下坐在一张桌子上草草吃饭,也没想和父母多聊聊家常。
饭毕,我们不是窝在沙发里玩手机,就是钻进书房或卧室打电脑。而父母也不知从何时起变得越来越小心翼翼,每天习惯地问:“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明儿早起是喝豆浆还是煮馄饨”“包饺子,咱包啥馅儿的呀”如此种种,像不断重复的台词,有时问得我们都烦了,随口回他们一句,但自己说出口的,必定到时候他们就兑现了恳求于我们的“旨意”。
我们时常带着宠物去街上、公园里散步,却从没说过一句“爸、妈,咱们今儿晚上去广场玩一圈儿去呀?”我们留给他们的似乎只剩下了那个或早或晚回到家里的身影,我们的眼几乎没离开过手里的手机,却从不注意父母每天的脸色表情。
他们来了,我们有了可以多在外面“野”一会儿的自由空间,甚至有时候总找个什么理由不回家了,去喝酒、去打牌、去唱歌,深夜醉熏熏地回到家,看见母亲手里捏着遥控器歪斜在沙发上打盹,觉得自己也挺不像话的。
一连几天,母亲变得沉默寡言、低眉垂眼,悄无声息地做着她认定要做好的每件事,忙完了便躲进他们的小卧室,与我们互不相干。那天,我风衣掉了枚扣子,找不到针线,去她屋里寻,推门看见她正弓着身子俯在床上正忙活着什么,十分认真的样子,竟然连我走进来也没有察觉。我走到她身后,才看见床上摆着的正是那天被她用水洗过的那两件羊绒衫。她正一丝不苟地用一块硬薄木板慢慢将衣服撑开,拿着熨斗小心地熨烫……
她说,这是从楼下二单元张大妈那里问来的法子,希望能把衣服给重新整回来,好几千块钱呢,总不能就这样扔了……
看着母亲额头上被蒸气熏出的汗珠,还有那汗珠上沾着的丝丝缕缕的花白头发,我一时间有些羞愧。
记得小时候,母亲坐在炕上守着针线笸箩,手里摆弄着那块用5斤鸡蛋换来的小碎花棉布,为我手不停针地赶制过冬的棉衣,用一针一线把对我们的疼爱包括担心,缝得严严实实、密不透风,而我则慵懒地靠在她宽厚温暖的背上翻着童话书。而现在,我和母亲没有了那种身体碰触的亲近,甚至连一句柔软贴心的话都开不了口了……
衣服终究没有整回来。母亲征询我的意见说拿回乡下送给身材小巧一点的亲戚,我欣然同意。但我没想到,晚上,几乎不来我书房的父亲敲门进来,把手里攥着的一叠钱塞给我“再去买两件新的吧,别怪你娘,她也不是故意的。”
那一刻,我慌张羞愧得脸发烫,连忙说“爸,什么大事,快把钱拿回去……”一时间感觉自己像个“罪人”,又恍惚地感觉到:这还是我的父亲吗?这还是那个我小时候,一脸不苟言笑,我没考好,或者“惹事生非”追着我打的父亲吗?他的威严哪里去了呢,他的脾气哪里去了呢?现在的他,俨然安静沉默、小心翼翼地像个来串门儿、不敢张扬的孩子。
快过年了,母亲说要回乡下,怎么也得提前准备准备过年的事。
我说:“还早呢,再住些日子不打紧……”话说出口又觉出后悔。因为习惯性的口气不像是挽留,倒像是送人出门的客套。
母亲说:“我们明天就回吧。也在这楼里憋了一个冬天了,怪闷的。”
其实我看出了母亲要走的急迫心情,我不知道该继续挽留还是痛快地送他们走。好像左右都是“不孝”。或许,我们真真地是犯了错,而他们从未责怪,何谈原谅。
他们老了,他们的爱竟然也变得这般小心翼翼起来,小心翼翼得让儿子的心扎得有点疼……
作者:海波 编辑:李耀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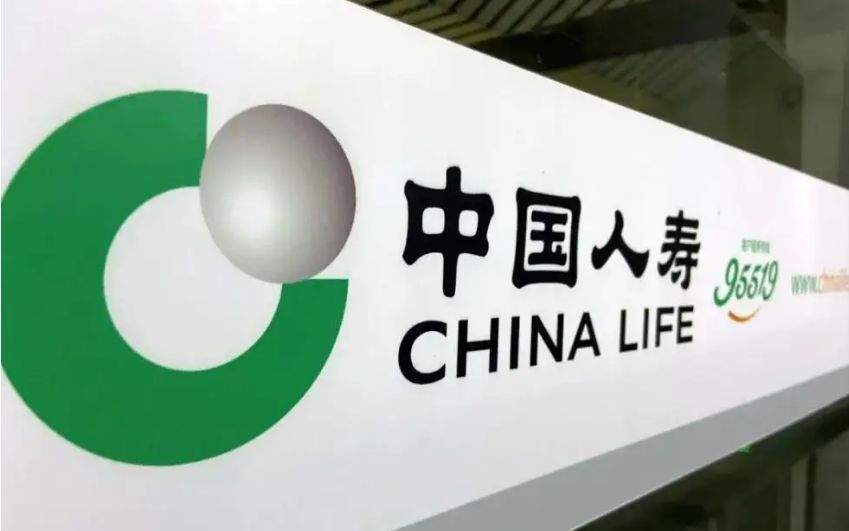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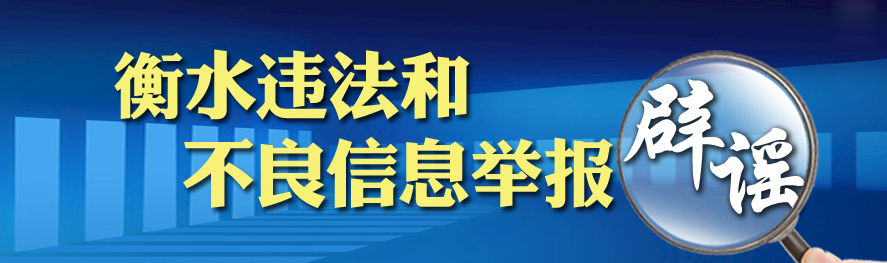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