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条路陌生而又坎坷,他顾自走下去;有一条路茫茫而又遥远,他坚持走到头,那个走着的人是我的父亲,一个无畏的行者。
随着年纪越来越大,父亲经常说起,想去走走年轻时走过的路,去看看那些年奔波过的地方和交往过的朋友,但是,他再也没有年轻时的勇气。他老了,老得不敢独自去远行,却又顾忌着会不会耽误孩子们的工作?便一次次将沸腾的心思按捺住。我能看出父亲眼睛里的渴望,便像当年他的果断一样,在网上订下了机票,这才确定了向北方的行期。
父亲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像那个年代的所有农村人一样,挨过饿,修过河,生产队里拼命挣工分。也曾因嗓音好,被评剧团选上,差点儿脱离农村;也曾学过电工,阴差阳错被换掉;还学过医,差点当上村里的赤脚医生……父亲是智慧而精干的,但是因为种种,父亲在娶到娘之前的日子充满变数。直到善良能干的娘进了家门,又正好赶上改革开放,我和弟弟也相继出生,改革的春风和家庭压力的骤风一起袭来,反而让父亲有了方向和定力。全家一合计,父亲就和我的大爷、叔叔、姑姑们合伙做起了粮保器材生意。1980年,父亲开始了他的“长征”之旅,最远到过黑龙江的黑河,每个月都要去几趟葫芦岛、凌源、平泉、建昌……当时,父亲就凭着地图走进各个地方的山里去找粮库推销产品,那漫长的路啊,是否还记得这样一个年轻人的脚步?那都叫不出名字的已经消失在历史云烟里的粮库,是否还会把爸爸的货品记进历史档案里?长路不言,历史无语,爸爸却执拗地铭记着,记了很多很多年了。
从我记事起,家里家外只有娘一个人忙碌的身影,而父亲则是“出门饺子进门面”的谚语里来去匆匆的影子。直到很多年后,我才知道,那些年饺子、面的记忆是很多同龄人奢侈的回忆,于我,却是平常。在物质生活方面,父亲给了我们太多别人可望而不可及的味蕾上的享受,有一段时间我是厌烦透了吃饺子的,不知那时是否是已经厌烦了和父亲的离别?我想应该是的。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出门,有时是一身黑色正统的中山装,或者是一套威武庄严的军装,单肩背着一个黑色的皮提包,里面必定装着一双娘做的布鞋。那些隐没在山里的粮库,一天只通一辆班车,甚至连车都没有,父亲都是背着行李,徒步去谈生意的。我不敢想象,大雪漫山时,大雨瓢泼时,大风骤袭时,还有夜晚来临时,父亲一个人走在山路上害怕吗?想家吗?后悔吗?我在臆想里,看到一个坚定的背影风雨兼程,没有回头,只是向前!
今天,陪着父亲向北方,我们乘飞机两个小时就飞越了一千五百多公里,到达了哈尔滨。父亲不用那么辛苦,一步步丈量脚下的路,从哈尔滨站走到记忆里的河阳路去看望他的舅舅了。可是,六十多岁的父亲在机场拾阶而下时的疲累,让我心疼。如果可以,我宁愿看到那个负重前行的年轻的父亲!父亲老了,就在我们不知道时间都去哪儿的时间里。尽管父亲还不习惯我的搀扶,可是,我要搀着你走,慢慢地走,就好像时间再不会溜走。
在哈尔滨,父亲和他分别近四十年的表叔、表姑畅聊年轻时的往事,我才知道,在那个信息闭塞的年代,在那个很多人还只知面朝黄土背朝天土里刨食的时候,父亲已经为三个孩子规划了成长的蓝图:一个走教育之路——从事“天底下最光辉的事业”,一个在公安系统“为人民服务”,一个做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他的思想注定了我们的人生与众不同,让我们受益无穷。时至今日,唯有感恩父亲为此对我们进行的严苛要求,才让我们不负时光与自己。
父亲的舅舅很多年前就来到哈尔滨,那时的父亲下了火车,常常步行十余里地去舅舅家里。因为父亲的幽默乐观,深受舅舅一家人喜爱。那条尚志街上,不知留下了父亲多少来来往往的足迹。走在那条街上,是否父亲也曾艳羡过城里人的生活?是否曾把一丝农村人的卑微唱进“三套车”里?而如今,舅舅已然逝去,在墓前,父亲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声声喊舅,唯有墓碑上舅舅的照片笑容以对。如今再别,也许再无相祭,父亲的心是不舍,是很痛的,我看得出来。
离开哈尔滨的那晚,在已不似当年的车站,父亲喋喋不休地念叨着,在他的话语里,我们找到了那年那月哈尔滨站的样子,他都记得。在这里,感受着这个城市交通的便捷快速,父亲也高兴地说起,也许明年他还能来。我也是这样希望的,我希望父亲在寻找从前的日子里越来越年轻,找到越来越多那个年代自己的影子,于晚年的他来说,这是最有意思最有意义的生活。
接下来,我们走过了葫芦岛,去到了凌源。靠着父亲的记忆,我们找到了三十多年前在凌源汽车站站前路上的“兴隆旅社”,只不过现如今已改头换面成了“兴居旅店”。在这里,父亲见到了当年从凌源火车站赶着小马车接送他的店家,两人相见,自是一番感慨。那时的住宿费从一晚八角钱涨到一元钱、一元贰角钱,店家还时不时地给住店的做点儿好吃的,那种淳朴那种乡情,父亲至今难忘。直到今天,店家才收了我们两间房九十元钱,可想而知的简陋,可是能让父亲的心境再回到从前,枕一晚上的回忆安稳入睡,是我们的幸福!试想从前,住宿条件远不如现在,父亲依然怀念,念的就是这份入心的人情世故。
从凌源到承德,再到东光,老家临县的一个小站,多是在山区穿行的路,一路的白云悠悠,一山的翠绿欲滴,还有偶尔的杏花灿烂。但是,父亲的目光并未为它们有所停留,而是经过这个村那个店时,总能熟悉地叫出它们的名字,说起自己在哪条路走了多长时间,说起认识的朋友就住在火车道旁的哪座房子,说起哪座房子没有什么变化,说起哪棵树还在……父亲呀,这漫长的路,在你的记忆里为什么那样清晰呢?我知道,行走着回忆着,那条路上关于你的故事都是深刻的,因为太苦,所以铭记;因为太真,所以难忘……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了,父亲也走过了属于他的光彩夺目的四十多年,向北方,已物是人非,父亲几度热泪盈眶,频频回首。路途迢迢,父亲每一步路都没白走,也不会白走!因为有他的孩子们——我们会像他一样,继续走下去,而且把“走”的精神永远传承下去!
作者:息玲玲 编辑:李耀荣







 广告
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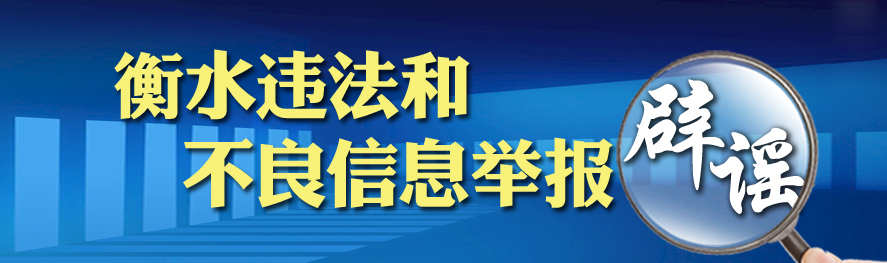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