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舅爷(上)
王国华(深圳)
郭玉贞,在中华英烈网“烈士英名录”中搜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久久地盯着显示屏,眼睛渐渐湿润。
他是我的舅爷,我奶奶的亲弟弟。
小时候,每年春节都跟着父亲和叔叔去舅爷家拜年,但我不知道舅爷的名字。话说回来,又有几个人知道自己舅爷的名字呢?我只知道一个叫大舅爷,一个叫二舅爷。大舅爷胖,二舅爷瘦。
奶奶出生于1920年初,2021年末去世。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跟我提到过,其实我还有两个舅爷——当年奶奶清明节回乡祭扫,都要给她早早死去的另两个弟弟烧纸。
我只是听听,也没往心里去。
奶奶去世后,我怅然若失。父亲去世了,奶奶去世了,他们一生中经过了那么多事,我对他们的过去却知之甚少。而那些更早去世的人,他们到底有什么故事呢?
所以在电话里和我的姑姑王素珍谈到了舅爷,也就是姑姑的亲舅舅。纯属闲聊,结果姑姑一句话却给我惊着了。
她说:“你有一个舅爷是烈士。”
“啊?他是怎么牺牲的?”
“不清楚啊,只记得你奶奶说,他是从山崖上掉下来摔死的。”
我听完,小小地感慨了一下,就去忙自己的工作了,暂时把这件事抛在了脑后。
不知为什么,此后很长时间里,“烈士”两个字时不时在我眼前闪一下。这是一个与我有血缘关系的人。他什么时候牺牲的?在哪里牺牲的?他长什么样子?生前经历了什么?虽然从未见过他,但这一个个问题,仍不知不觉地蹦出来,躲都躲不开。
也许这就是血缘的神秘力量吧。
我给姑姑打电话询问。姑姑说:“你那个舅爷叫郭玉征,征服的征。听说烈士陵园里有他的名字,我也只是听说。”
于是我联系了老同学李靖。她一直在老家阜城县城生活,熟人多。我请她帮忙打听一下。
李靖还真从阜城县退役军人事务局那里查到了。信息如下:
郭玉贞,1914年出生,男,1939年7月参加革命,1940年8月牺牲于曲阳县。牺牲时是冀中十六团二营六连战士。目前安葬在曲阳县。
退役军人事务局的朋友说,这些信息是根据郭里阳村村民过去的口述和回忆整理的,细节或许不准确。如果具体了解,可以再联系一下曲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没错,我舅爷家就是阜城县古城镇郭里阳村的。但“征”为何成了“贞”?李靖说,咱们这里的方言,姓名中“贞”“征”的发音常常混用,那个年代识字的人也不多,记录时随手写上,错误在所难免。想想也是,我们那里一直把“侦察兵”读作“征察兵”。
为求详细资料,我联系了保定市曲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对方热情地帮我查阅,结果是查无此人。想来也正常,那时候兵荒马乱,没人记录这些详细信息。多年前死去的一个外乡的普通战士,被详细记录的可能性更小。资料上的“安葬”于某地,其实可以理解为“家乡无坟”。
要查详细资料,还是得在本乡本土想办法。
郭玉贞如果活下来已经一百多岁,同龄人全部去世,下一代人也渐渐凋零。姑姑王素珍联系了自己72岁的表姐郭素琴,她是我大舅爷的女儿,郭玉贞的侄女。姑姑和表姑都从老一辈人那里零零星星听说过一些事情,还有一些事情则是她们的亲历。经过硕果仅存的两个人的叙述,郭玉贞的面目逐渐清晰(为叙述方便,下文中的当事人都直呼其名)。
郭玉贞,一直被王素珍称为“郭玉征”。因为她小的时候,母亲郭玉兰每年清明节前回娘家上坟,都要让她在一叠纸钱上写上舅舅的名字。母亲说,舅叫“征”,王素珍就写“郭玉征”。但母亲不识字,王素珍写的什么,母亲不知道。久而久之,王素珍的认知中,这三个字就定了型。所以极可能本名就是“郭玉贞”。
同村还有没有另外一个叫郭玉贞的人呢?答案是没有。同时代本村的烈士只有这么一位。1949年后,郭素琴的爷爷奶奶(郭玉贞的父母)被确定为烈士家属。少年时的郭素琴偶尔到古城镇政府替奶奶领取十元钱的烈属补贴。老人领到钱,心里不好受,会哭起来。也许她想到了这钱是用儿子的命换来的。一个普通的战士,却牵连着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
郭玉贞姐弟六人。
老大是郭玉兰(我的奶奶)。大儿子郭玉凤,年轻时亡故,妻子带着孩子另嫁。二儿子郭玉贞,三儿子郭玉顺,四儿子郭玉林,最小的女儿叫郭玉荣。
我小时候经常见到的大舅爷和二舅爷,实为男性中的老三和老四。因为老人想起早亡的两个儿子就难受,所以家人干脆让在世的两个重新排位,一个老大,一个老二。
郭玉兰多次跟王素珍讲:“你那个二舅长得可好了,非常精神。十五岁就在村里演节目,人们都喜欢看。”演什么节目呢?没有记录,成了一个谜。那个时代主动参加革命的,有一些确实是人中龙凤,如果活下来,没准儿当个大干部。
老人们说,郭玉贞参军后曾经回来过一次。他们行军从此路过,回家来看看。他的爷爷以为他当了逃兵,把他骂了一顿,他辩解说只是回家看看,然后哭着走了。
郭玉贞的母亲,如果当时就站在旁边,事后得到儿子牺牲的消息,回想到这一幕,心里会多难受啊。
但,这就是战争的残酷。
郭玉贞归队前又到二十多里外看望自己的姐姐郭玉兰。
姐姐给了他一双鞋。
那是姐弟二人见的最后一面。








 广告
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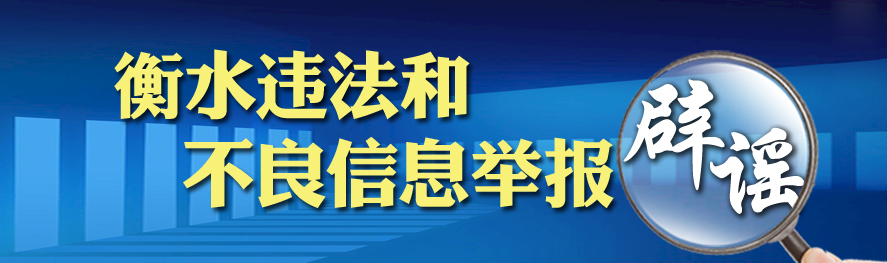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