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是知识的宝库,精神的殿堂,思想的家园,是我生命里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1991年、2012年我两次搬家,所有家具都送了人,只有那十几箱子书籍没舍得扔掉,随我一起来到新居,而且一次比一次多,我没有清点过有多少册书,虽不及古人“学富五车”之多,但至少有两拉车。因为一直没有购置书橱书架,那些书只能堆积在储藏间里。
一
我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生人,印象中读到第一本书应该是在五六岁时。那时还没上小学,父亲去县城开会时买回来一本小人书。那是一本根据现代京剧《红灯记》改编的连环画,从此便开始了我最初的读书生活。那个时候,总是将过年时长辈们给的压岁钱积攒起来,留着买书用,舍不得买零食和鞭炮。村里的代销点不卖书,我都是步行到1.5公里之外的小镇(官道李)上的供销社去买。记得那时候的官道李供销社在村子的东头路南,一座高门楼的大房子里,屋子很宽敞,土地面,东南西三面是柜台,图书专柜就在南面柜台的东南角,有三两个格子,有小人书和“大书”。我一般都是一周去一次,有时候去得太勤,柜台里的小人书还没来得及更新呢,因为供销社要到县城的新华书店购进书籍,也是不定期的。
记得那时的小人书多是《红灯记》《沙家浜》《白毛女》《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等由革命样板戏改编的连环画,还有《半夜鸡叫》《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等。到小学五年级时,我的小人书积攒了足有200多本,在我们那个偏僻的小村里,我能算得上藏书“首富”了。村里的大人小孩都愿意和我交朋友,为的就是借我的小人书看,别的小伙伴家里有过去老的藏书,我就跟他们交换着看。
年岁大了些,小人书对我渐渐失去了诱惑,从父亲带回家来自己看的一本长篇小说《敌后武工队》开始(1958年出版,冯志著),我又转向了不带图画的“大书”,这是我平生读到的第一本长篇小说。跑到镇上,怕的是见到一本好书而兜里的钱又不够,悻悻地回来,一连几天总惦记着。从家里翻箱倒柜搜罗些废铜烂铁卖掉,或者向祖母要几角钱,再跑到镇上把书买回来,心才得安宁。小时候,我一直跟祖母一起居住,晚上就在煤油灯下为祖母读《高玉宝》,每天一章,就像收音机里的长篇小说连播一样。
随着阅读欲望的不断增加,小镇供销社里的书籍已经不能满足我了。而我居住的小村距离冀县县城有35公里之遥,那时到县城只有一条土公路,交通不方便,总去县城的新华书店买书也不现实。前磨头是深县(现深州市)的一个小镇,离我们村约有20公里,那里有一个小火车站,有一个小书店,自然要比供销社的书多很多,而且是文学、历史、政治、科技、军事、教育等分门别类,这是我接触到的第一个书店。所以,我就利用星期天骑自行车去那里买书,一般都是上午去,中午在那里吃点东西,下午再回来,大多数时间都在供销社的书柜前或者书店度过。当我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中,心里也是甜甜的,因为我买到了自己喜欢的书。
我有两个本村同学家里有很多老书,因为一个同学的父亲是小学老师,一个同学的哥哥是衡水师专的老师,我经常用自己买的新书与他们交换着看,先后阅读了《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牛虻》《啼笑因缘》《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如果彼此相中了对方的某一本书,要“谈判”几个回合,才能把自己喜欢的书据为己有。
二
当时对我来讲,书比衣服重要。我把自己买的书都包上书皮,统一编号,登记造册,分别装在两个箱子里。记得有一个是祖母做陪嫁的梳妆盒,能盛五六十本小人书,“大书”则装在父亲修理收音机的一个工具箱里。1976年夏天唐山大地震时,人们都搬到简易的防震窝棚里睡觉,我也不忘挑一些自以为有价值的书拿出来。记得在一个下雨天,我和家人住在院子里用塑料布搭成的窝棚里,突然又想起了有一本书应该拿出来,便冒雨又跑回屋里,全然不顾地震不地震了。
常言道,“买书莫如借书”,所言极是。借来的书日夜兼读,如饥似渴,而买来的书总觉得有的是时间,以后再读吧,以至于有些书至今也没有仔细读过。与小伙伴交换着看书时,一般都有时间限制,有时一个通宵能读完一本20万字的长篇小说,读完了这一本还有下一本等着我去读呢,如果谁不守信用,以后就不用想再借书看了。
1977年我上高中,中国文艺刚刚开始复苏。在语文老师刘长禹的启发下,我才开始了有目的、有选择地读书。高中毕业时,刘老师送给我好几本书,记得有《人间词话》《杜甫诗选》《美学概论》等等,这在当时是我最喜爱的东西了。
三
经过了小人书、“大书”、“唐诗宋词”等读书历程,我已告别校园走向社会。在乡间的农舍里,我几乎是发疯般地读着艾青、臧克家、普希金、拜伦、雨果等人的作品,啃着似懂非懂的美学、心理学专著,整个身心都沐浴在书和知识的海洋中。从毕业到参加工作后的几年间,我曾经自费订阅过《诗刊》《词刊》《星星》《诗神》《诗潮》《萌芽》《青年作家》《青春》《文学青年》《鸭绿江》《歌曲》《大众电影》《文学报》等报刊,最多的一年,我一下子订阅了10样报纸和杂志,这在当时农村是不多见的。也正因此,我与我们村这条线路的邮递员老张成了好朋友。
从那时起,我已不再仅仅满足于做个书的读者了,立志也要拿起笔来写作,让我的名字也走进那些书里。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一个秋天的傍晚,我坐在衡水湖边的草地上,写出了有生以来的第一首变成铅字的诗《衡水湖夜曲》,发表在衡水地区文联主办的1981年第3期《农民文学》上,从此便开始了我的文学创作之路……
四
我是读书的受益者,“读书改变命运”这句话用在我身上最合适不过。我出生在农村,没上过大学,没有学历,正是因为我读了很多书,才有了知识积累,才让我从一个读者变成了一个写作者,从一个农民成为一名国家工作人员。从1982年到1995年,我在冀县化肥厂工作了13年,只是一名合同制工人。正因为我在企业做文秘、搞报道、写公文小有名气,才被调到冀州市工业局,后来又被特批调入冀州市委宣传部,从事了25年的专职新闻外宣工作。
古人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有什么,全凭读者去感觉去体味。历尽千辛万苦终于觅到一本好书,犹如在沙漠中寻到一片绿洲,一整天都会沉浸在愉悦而美好的情绪之中;在冬季一间冰冷的屋子里读一本好书,就像捧着一只火炉,心中充满无限暖意……粮食填饱了我们的肚子,给人以强健的体魄、劳动的力量;书则喂养了我们的精神和头脑,给人以丰富的思想、敏捷的思维。读书,给予人的不只是一门技能,而是潜移默化地提高了人的素养,正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这就是阅读的力量。
家有万贯终会散,唯有书香传家远。最后,让我借用一位诗人的一句话与大家共勉——
读书吧,这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
作者:杨万宁 编辑:李耀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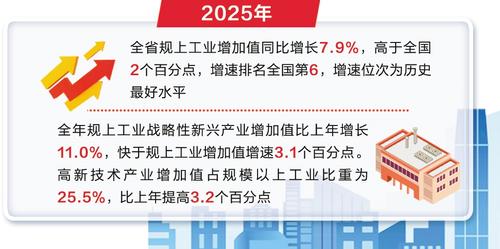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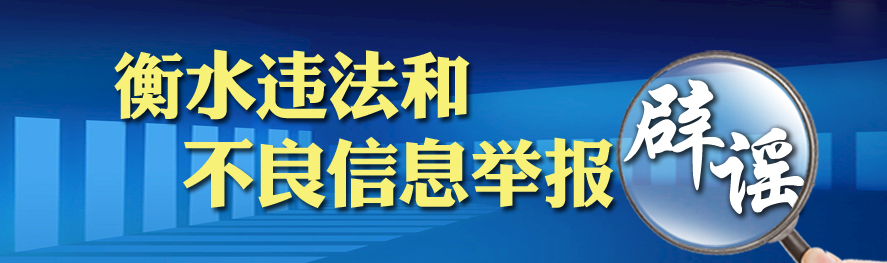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