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5月27日,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九。再有10天就芒种了,我得赶紧去南王庄找老周,不然就耽误事了。
雨淅淅沥沥,不大不小,不急不缓地落在挡风玻璃上,砸出豆大的水花儿。一对雨刷有气无力地晃动着臂膀,一副大病初愈的样子。看着看着,我想起了初见老周的模样。
车外,连绵的麦田已略显微黄。收割完的油菜地种上了玉米,一个个绿色的小喇叭破土而出,贪婪地吮吸雨露,好像朝着天空大声喊着:“娘!”
我和老周并不熟,总共才打过两次交道。第一次是在医院里,我父亲住9床,他住10床。老周脑栓塞,一只胳膊动不了,他就用另一只手托起来,上下、左右、前后地晃。说话还不利落的他,语气中透着自信和豪放。
第二次遇到老周还是在医院,我来检查身体,他来复查。一照面,我看他恢复得还不错,只是走起路来身子有点晃。老周告诉我,他现在种着500多亩地,注册着家庭农场。我看着还没好利落的他,睁大眼睛,露出怀疑的目光。
老周侃侃而谈,他向我推荐高产玉米新品种,看着他那真诚的目光,我相信了他。
到了,到了。我看到了村口铁艺牌坊上的醒目大字——五亿农民的方向。这里就是当年被毛泽东主席高度赞扬的南王庄村,三户贫农办合作社的故事曾经响彻了大江南北。老周住在村东头,临街的三间门面房,门头一块彩钢牌匾,几个大字映入眼帘——安平县峰盛家庭农场。
老周把我让进屋里,又开始推介他的高产玉米和抗旱节水新技术。我说:“老周,我相信你,不信我就不来了。”老周拍着胸脯说:“今年你按我说的试试,每亩肯定多打五六百斤。”
我说:“行。不过,这次我来还有一件事,需要你配合。”
老周望着我,目光中带着诧异。我和他说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冀中一日》,又讲了今天衡水市委宣传部发起的《衡水一日》。老周略显吃惊地说:“你是作家,咱去里屋坐下慢慢说。”
老周说,他就是一个不安分的人,几十年总在“瞎折腾”。
老周是退伍军人,当年是通信兵。1983年退伍后分配到县里机械厂上班,才干了一年,就辞职下海了。东筹西借买了辆拖拉机,开始拉砖、拉沙子、拉石子跑运输。早起晚归,一干就是3年,挣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随后,老周的拖拉机换成了大客车,每天往返于安平和石家庄之间。1991年,老周的客车换成了大货车,跑遍了全国各地。2000年,东奔西走的他想安生几天,回家经营起一家商业门市部。
转眼到了2014年,老周待不住了,他又想“折腾”。他要种地,而且一种就是100多亩。他种的是麻山药,当年就赔了个底朝天。不服输的他,第二年改种小白嘴白山药,不仅补上了去年的窟窿,还净剩十几万。
老周种地尝到了甜头,家里人也开始支持他。可没想到,那年他种了100多亩红薯,因管理不善又赔了。面对挫折他没有倒下,只要他认准的理,他就会一头扎到底。他远赴河南学习种植红薯技术,终于又站了起来。
这几年,老周又迷上了种植小麦和玉米。他多次远赴上海、郑州、大悟等地参观学习,摸索出自己的一套种植方法。他种的玉米,秸秆不死,棒子个大,产量比一般人家的高出三分之一。头两年,他有着自己的小九九。别人问他种的什么玉米品种,他嘿嘿一笑,说:“我种的这种玉米,不能吃,做饲料用的。”
一来二去,大家问得多了,老周的心里开始过意不去。他想:“我一个人富了算什么?大家一起致富才行。”
老周变了,他逢人就说他的种地经。种什么种子,施什么肥,什么时候浇水,什么时候打药,每亩可增加多少收入。慢慢地,在他的带动下,附近各村出现了二十多位种地大户,纷纷成立了家庭农场,总计流转土地一万余亩,年利润几千万元。
这不,今年老周又开始试用节水抗旱免浇的新技术。他种植的400多亩小麦,虽然一水未浇但是长势喜人,预计亩产千斤以上。老周说:“国家在大力推广旱作雨养,我要做咱们这儿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我经历了大水漫灌、喷灌、滴灌等多种灌溉方式的变革,每一次变革都是社会的一次进步。今天免浇技术的应用,将是最彻底的一次变革。”
老周送我到门外,我转身告辞。陡然,我发现门头的牌匾还有两行小字:土地流转,土地入股,统一采购,统一销售。
雨还在下着,雨滴比来时小了,可劲头却猛了。雨点打在挡风玻璃上,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如擂动战鼓一般。那对雨刷也来了精神,快速地舞动起来,像极了冲锋的战士。
雨越来越大,我双手紧紧握住方向盘,在雨雾中穿行,目视前方,找准方向。
作者:孟海涛 编辑:李耀荣







 广告
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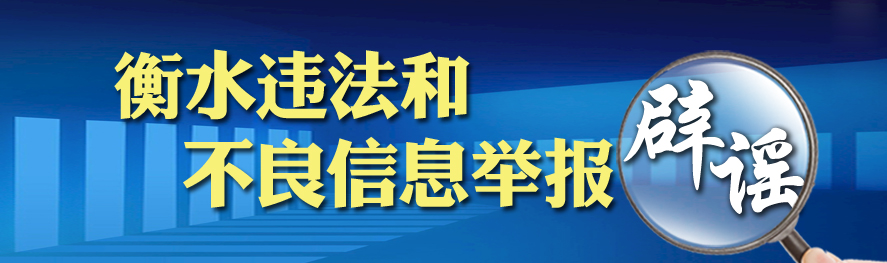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