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62年12月出生,1976年12月刚好满14周岁。就在这一年,我的人生迈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步——我参军了。
那时候,我们一家生活在吉林省延吉市的一所部队大院。1976年12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天,父亲急匆匆地领回一套肥大的男2号棉军服。妈妈手忙脚乱地在缝纫机上一顿紧急操作,把衣服改小后给我穿上,也没来得及嘱咐什么就让我从家里小院的后门出来,坐到停在路旁的一辆军用吉普车上,由王叔叔护送我。大约坐了3个来小时的车,我们到了中朝边界的一座小城——图们市。我们在那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又坐了近一天的火车,来到了黑龙江省穆棱县的一所部队野战医院。就这样,懵懵懂懂地开启了我的军旅生涯。
这所野战医院是一个县团级单位,医院的新兵连安排在距医院所在的穆棱县城200多公里的一座山脚下。这儿原本驻扎着医院下属的一个野战医疗所,整个营房大院有近200亩地,从南向北依次坐落着三排东西约300米长的营房,每排营房中间是一条走廊。走廊两侧是大小功能不同的房间,三排营房中间有一条南北内廊连接。我们新兵连的150多人和野战所原有的几十人,就住在这个不大的营房里。这里紧靠中俄边境的珍宝岛,距离最近的一个村子也有两公里远,真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我们150多人分10个班,年龄则参差不齐,最多的上下要差六七岁。每个班安排一名老兵班长带我们,再从我们中间推选出一名副班长,女兵班大都安排的是女兵班长。我被编在了五班,我们的班长是一位1973年入伍的老兵,名字叫郝丽娜,她的个子足足有1.7米高。郝班长人很开朗很和善,粗门大嗓特别爱笑,对我们很关心。现在我还会清晰地想起她笑呵呵的神情。
新兵连的生活是紧张又枯燥的。主要是军人基本素质的训练,包括队列、紧急集合、正步走以及后期的打靶、刺杀、站岗放哨,还有严格的内务卫生,以及间或学习军史军纪和军歌等。内务训练要求每个人的床单要铺得平平整整,被子要叠得方方正正,牙具、毛巾、脸盆摆放整齐划一。叠被子是新兵连内务训练的一个重点,不但被子横宽折叠要有基本尺寸,最重要的是要把前后左右上下几个面一遍遍地捋出横平竖直的线面,看起来像个切好的豆腐块。东北驻军的被子都比较厚,把一个厚厚的不规则棉被愣是“切成豆腐块”,可想而知是要花多大功夫。没个半月二十天的反复训练和捋顺是做不成的。床单也要求铺得没有一点褶皱。当时我们的军用床单都是纯棉布的,把它弄得平整无褶很不容易。为此,我们经常晚上睡觉时小心翼翼地把床单叠平压在枕头底下,第二天再把压得比较平整,并且带着横平竖直几个折痕的床单铺在床上。为了鼓励大家,新兵连经常评选内务标兵,遗憾的是,尽管我很在意这个荣誉,但从未入选。现在想起来,这个内务训练虽然很严苛,但使我们每一个经受训练的人一生养成了干净整洁的好习惯。
每天早晨六点半,一阵嘹亮的起床号准时把我们叫醒,5分钟后我们就要穿戴整齐地站到操场上排好队。一月份正是黑龙江最冷的时候,我们身穿棉衣棉裤,脚蹬里外全是羊皮的大头鞋,头戴羊皮帽子还要放下遮脸,系紧下巴颏下面的带子,手上也要戴着羊皮手套,这些是当时东北驻军的标配。尽管如此,我们依然被冻得打哆嗦。起床号一响,我们一骨碌爬起来,迅速穿戴整齐往操场上跑,谁也不敢落后,否则是要被严厉训诫并且还要挨罚的。记得当时有人怕早晨穿衣服耽误时间,晚上睡觉时干脆就不脱衣服了。新兵连出早操是很不轻松的,说是叫早操实际上是跑步,而且是男兵在前边带队跑,一跑就是五六公里,速度还比较快。记得那时我总是累得气喘吁吁,跑到半路实在坚持不下来就得掉队。记得新兵连5个多月的早操,我没有能跑完一次全程,当然像我一样的女兵还有几个。好在当时连队管理也比较人性化,我们并没有因此而挨过批,可能连长看我们年龄小而且确实已经尽力了。
当时最难熬的是半夜里站岗,每个人都要轮流站。寒冷都是次要的,主要的就是胆小害怕,好在是两人一组一次一个小时,编组时连队也考虑了年龄胆量等因素。记得第一次轮到我站岗时,尽管和我一组的是一位比我大几岁的战友,胆子比较大做事也很老练,但我还是吓得浑身发抖。那天夜里没有星星,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只有阴森静默的营房门口岗亭上一盏灯发出微微的光亮,呜呜的寒风更增添了几分恐惧。我紧闭双眼咬紧牙关一刻不停地拽着战友的衣角,哆哆嗦嗦地好不容易熬过了记忆中最漫长的60分钟。后来,我的胆子才慢慢大起来。
除了训练上的辛劳,还有生活上的艰苦。由于我们这些人一下子涌入这个小小的野战所,一时还未纳入部队编制,所以,后勤保障很不到位,以至于我们天天都是吃高粱米蒸饭和玉米面发糕,一星期仅会吃到一次馒头和一次大米饭。配菜也是一成不变的清水煮白菜和盐水煮土豆。有意思的是,一到吃馒头的时候总会有人悄悄地往裤兜里揣几个回去,肥大的棉军服倒是成了很好的掩护。后来炊事班发现了这个问题,一到吃馒头时不得不派人严格巡视把守。这样极度艰苦的生活,一下子捧火了附近村里的小卖部。小卖部不管何时进了任何一种食品,肯定会一扫而光。不过,那时候的零食基本上饼干和蛋糕,还经常断货。我们当时还有一个打牙祭的方法就是酱油泡木耳。我们所在的地方正是东北黑木耳产区,周围山上有些朽木会长出木耳。开春后,山上的积雪逐渐褪去,会看到山坡上一些横七竖八的朽木上,长出一朵朵大小不等的黑木耳。我们拿个小刀把它挖下采回来,用热水泡发后再到炊事班要点儿酱油一泡,格外美味。以至于这之后的几十年,我对凉拌木耳这道菜一直有种别样的情愫。
有段时间,我们面临被清退,一时间人心不稳,连队也暂时没有安排学习训练,我们就天天在附近到处跑着玩儿。寒冷的冬天,山脊上覆盖着大约有两三尺厚的积雪,即使摔倒了也不觉得疼。尽管雪山比较滑爬起来很费力,但架不住我们当时的热情,一群十几岁的孩子拽着树杈,相互拉着推着,不一会儿就能爬到半山腰。我们爬上去的主要目的是要享受从雪山上往下滚的过程。选一个地势平整坡度也平缓的山坡,整个人横躺着滚下来,或是蹲坐在雪地上顺着滑下来,好玩儿极了。在那个寂寞的年代,这似乎是我们最开心快乐的记忆了。这些苦中作乐的笑声也排解了我们被“退兵”风潮造成的压力。后来,我们结束了长达5个多月的新兵连生活,有幸被批准正式入伍了。之后,我被组织安排在警卫通信连,历任话务员和报务员。军校恢复考试入学后,我又通过自学以高分考入军医学校,毕业后提干从事医务工作。我在部队服役13年,由一个少不更事的少年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军人。部队的大熔炉锤炼了我的思想意志和行为品质,为我的一生奠定了丰厚扎实的基础。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们的新兵连训练和生活是相当艰苦的。但是,我们150多人,不管年龄大小,竟然没有一人主动退出,都圆满完成了新兵连的训练任务,这该是一种怎样的精神和毅力啊!这就是我们五零后、六零后年轻时顽强的样子!我们懵懵懂懂一路走来,在“我是革命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的思想引导下,沐浴着激情岁月的革命洗礼,走出了自己通往“罗马”的金光大道。
作者:尹爱东 编辑:李耀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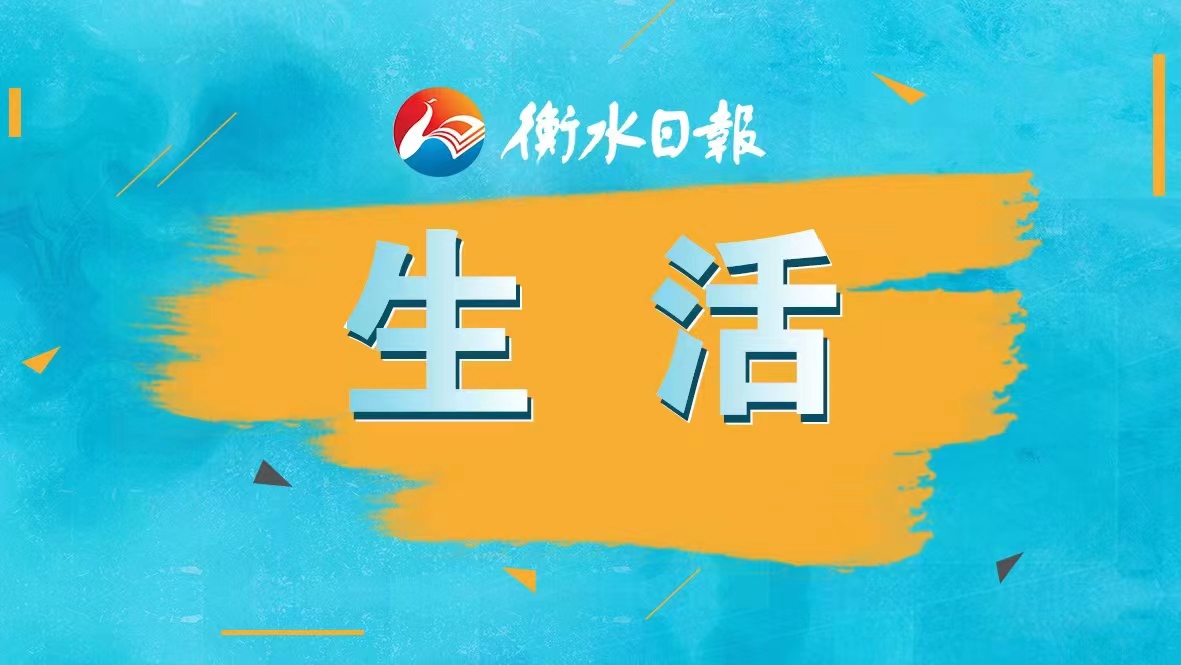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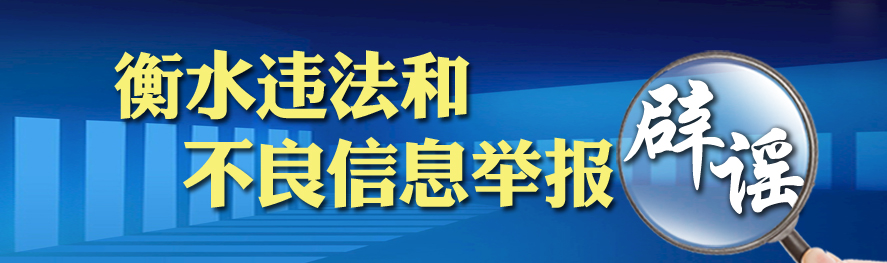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