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家甘肃镇原,人殁了是天大的事,上年岁的从不说死字,都说殁了,有的还说“塌天了”。父母是天,老人殁了,就是天塌了。“殁”字大有讲究,我后来才知道像孔圣人死了,才能叫“殁世”。镇原的泥腿子竟然说了用了上千年,那份彬彬儒雅,让我对生养的那方水土顿生敬意。
镇原的丧葬仪礼缛节繁文,得听阴阳先生的。哪天打墓,何时入殓,几时下葬,放几样用物、烧几次纸钱、吹几遍唢呐……丝毫不能马虎。从“一七”“七七”到百期、头年、三周年的时日,甚至“二七”不哭,出“七”去孝等等,黑字朱批。时时提醒生者,须臾不敢忘却。头年时亲戚族人一起给过,二周年则称为忘周年,可以稍加马虎;但是三年比较隆重,多数还要大过。虽然以后的清明节、寒衣节等都照例要烧纸,但人们仍说三年是给亡人烧的最后一张纸。此后过年时也不用往家里请灵牌了。好似过了三年以后,亡魂就该轮回归位了。
河北似乎不讲这些,有时候又觉过于省事,让怀念都有些苍白。转眼,少华先生殁了竟已四周年了。镇原没有中元节,河北和很多地方都有。中元前日,去她的墓前呆了一阵,念叨了几句,有些莫名的伤感。就像这已经转凉的秋,舒爽中有些清冷,又像是四年前那个秋日的凝咽再次袭上心头。
那天夜里守在她的灵前,墙上的她,笑着,灿烂飞扬;守着的人,哭着,泪眼潸然。犹记那天的夜,漆黑!窗外华灯黯淡,屋里尽是抽泣。我默默地跟她说话,忆起过往点滴,回想漂泊心路,思绪万千。那些没说的话,已不知何处诉说。只能把烛光挑亮,愿它能再照亮一点儿归路。明明知道那一天或早或晚在所难免,甚至深知天堂之路又何尝不是解脱之道,可依旧希望哪怕还有个念想,也好。可她还是殁了,在白露的清风里,在让人扼腕痛惜的年纪。我们一步三回头,可终究还是把她一个人留在了那个永隔的世界。
十四年前大约是个暮春的午后,她说,读过我的文字,一直以为是个老先生,没想到竟是个学生。仓促谋面,就此相识。不久她为挖掘历史文化,约我写写衡水老桥。千余字的《为了忘却的老桥》,很快得到赞赏有加的评价。由此结缘老桥,《我与老石桥的宿缘》后来竟意外获得中国地市报新闻奖二等奖。
步入社会,数载漂泊不定,我的饭碗、家庭,让她焦灼不安。去北漂闯荡,去见大世面,去写大文章,定会有一片天地,她经常这样劝道。又极力推荐给首都、省城等所看好的地方,赞不绝口,如数家珍。生怕这个他乡游子过不上正常的日子,生怕这个被她欣赏的孩子为世所埋没。再后来,总算幸运,机缘巧合,苦尽甘来。我被留在了这里,得以暂时安稳。她得知后兴奋得欢天喜地,逢人便讲,连说老天有眼。
她是这样的,这样的是她。她创办的《滨湖画报》,用十年坚守,为这座城市打开了一扇窗口。她带着我们策划举办老照片展,每一条信息都一丝不苟,每一位故人都极力周全。外出采访时从提问技巧到写作技法,无不悉心讲解,每个字句都不容差错再三斟酌。我们常常深更半夜还在写稿校对,我也常常点灯熬油就章救急,丝毫不敢懈怠,力求完美无憾。
她钟情于传统文化,常说“优秀文化的根脉不能断”。她多年对京城琉璃厂与衡水人的文化渊源,特别上心。尽管捉襟见肘,但三五个人就真的启动了一个不凡的民间工程。我们时不我待地奔波着,京津冀宁,全国多地,一次次一家家地寻访健在的耄耋老人,到处打听联络他们的后人传人。翻看泛黄的故纸旧影,聆听曾经的掌故荣耀,还有留给历史的传奇与不朽。他们是古籍文玩金石器物等古老行当的泰斗耆宿,是埋首秦砖汉瓦故纸书堆的文化良心。她喜欢聆听他们的故事,更要记录他们的人生。他们讲得激动而骄傲,感受到了人生的价值和后人的铭记,还有来自故土的温暖与牵挂。她听得着迷而鼓舞,为术业而惊叹,为精神而钦敬,也为行动而庆幸。
这样的奔忙,有苦有甜。犹记在北京西红门镇找到86岁的文物修复专家刘增喆老人。采访出来,天已大黑,我们徒步一个多小时还打不到车的无奈;但却知道了历史课本上仰韶陶器人面鱼纹盆、秦陵铜车马的复制或修复者,正是这位沧桑老者。这样的挖掘梳理,留下了大量音频照片和数十万字的文稿。那是地域文化的根脉,是前辈明贤的遗照。我也是到后来才真正明白她的这份苦心和价值。很多人在采访后不久就离世了,包括刘增喆,次年就殁了。那些珍贵的记录是他们最后的人生影像,成了难得的存世记忆。大概多因这些跋涉和沉淀,后来我就真的多年没有离开文化的圈子,没有抛下写作的爱好与坚持。
九年前,我上无片瓦下难立锥,为求一檐存身,四下借债。她在本就难以自顾之时,主动提出并挤出两万块钱以解燃眉,说无论如何也要凑些渡过难关。随之还帮我求诸师友周急。而这些大概是她为自己也不曾有过的经历。除了感激和铭记,我不知该说些什么。结婚时,她携子早早地前来,像母亲般幸福地祝福着我们。后来才知道,大概同年底,知我一时无力,或是朋友急用,她便先替我还了一些,而我毫不知情。然而,我们曾是他乡路人,也不过萍水相逢。
七年前,得知她生病的讯息,我大惊失色难以置信。她一直都好好地,除了饭量小、瘦弱些,整天笑声爽朗激情澎湃。然而这是不幸的事实。那段日子正逢妻子临产,她便有意瞒着,忙乱中我对这巨大的变故竟是毫未察觉。犹记当她听闻母子平安,特别高兴。粗心的我也从未多想,每每回想,惭愧无颜!
我急忙赶往北京看她。那天热极了,见面是在韬奋书店,凉快温馨。她说住处很远,怕我折腾,又说许久没出来,幸亏是我来,儿子才允她出门。我们再去医院看望时,她依然坚强而倔强,放不下牵挂的事业和惦念的人们。再后来的一个雨天,我和妻子前去,她明显消瘦多了。陪她回柳林馆的住处,她走得很慢,再也不见风风火火的模样。每次回家后,她也总是悄悄地,生怕麻烦大家。她也总不让我去,更不让带东西,常说“别花钱,要么我也不痛快”。我便索性不打招呼,她欣喜又无奈。身体好些时,我们会聊很长时间,但只能尽量说些愉快的话题。她问工作生活,问家庭孩子,讲育儿的重要和方法,聊自己的经验与得失。我带去的钱她从来不要,老说需要时会拿,可终了也从未张过嘴。有一次我带去母亲为她做的羊肉泡馍,却忘了她不吃羊肉,我悻悻然不知还能为她做些什么。
她把我用旧信笺抄送的《心经》,连同师友赠送的文字、小画一起,悉心保存,精心收藏,满脸的幸福和感动。病中她仍然记挂着朋友,经常找人刻些小印章,买些小物件,几次托我取回分送大家,内容多是读书修身的词句。在外地调养时,一些康复的病友写了很多心得,有的歪歪扭扭,有的甚至字句不通,但字里行间满是对生命的热爱与再生的珍惜。她拍照给我,我再变成规整干净的文字,她给他们分享、鼓励。她说病友们又惊又喜。他们是来自辽宁、上海等各地的陌生人。
那几年,我经常梦见她,有时欣慰,有时惊起,不知好坏。她总说“放心,体重增加,越来越好,勿担忧……”那个腊月,她病情忽重,我们匆匆赶到北京,病榻上羸弱的她依旧兴致极高,文学艺术、剧目音乐,谈天说地。然而刚刚过了十天,清早当我揪着心再次赶到医院,她还仍在重症救治。厚厚的玻璃窗,隔断了呼吸,只有背影,我徘徊许久不忍离开,不敢离开。那个春节,我心里极不踏实,只能祈求上苍佑她渡过此劫。我想待到花开春暖,她一定会好一些的,一定会好起来的!
果然,阳春之时她终于回来了。虽已形销骨立,但精神尚可,每次都会聊好一会儿。当我迷茫沮丧时,还劝我世事维艰,风物长宜,说定有上天顾眷。七月再次入院,起初她还能坐起来,说几句话,每次都说:“你太忙了,别老跑了。”有一次,还吃了一块我带去的哈密瓜。她说挺喜欢,怕凉,不敢多吃。但每次又都嗔怪说,别花钱,别买东西。我一面假装答应,便特别注意,提前买好,多放一会儿,可她再也没有吃过……
八月初,她已骨瘦如柴,腿脚肿胀如纸,被疼痛折磨得坐卧不得。那天在医院守了一宿,她孱弱地说:“你回去吧,孩子小。”见我实在坚持,才不再勉强,昏昏睡去。临近九月时,她已无力坐起来了,每天躺在斗室病房时睡时醒煎熬至极。有时偶尔睁眼看看,可已没有气力说话了。白露的清晨,我正出门去看她,却是噩耗先到……她就是这样,渴望并竭力让每个生命都幸福安好,自己却先走了,只剩锥心的刺痛和回忆。
那些天,很多人为她的离去久久神伤难以释怀,很多人撰文追思凭吊缅怀。大家莫不忆起她的提携教诲,无不言及她的温暖帮扶,都说曾受她人格的影响与明灯的照耀。我一直在回想,她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怎样的一个让人久久怀念和不舍的普通人?有人说善良博爱,有人说坚强高洁,有人说怀瑾握瑜,有人说知性优雅,有人说生活马虎,有人说耿直坚韧,有人说宁折不弯……高兴时开怀大笑,愤怒处义愤填膺,从来直言不讳,可亲,可敬。她是同事敬重的才女大姐,是作者读者的报人伯乐,是后学晚辈的良师益友,是父兄爱子的至亲永怀。她是我一生的恩师和忘年挚友,是一束纯粹而温暖的光。白露,她坐莲而去,绽放天堂,音容永存,成了我再也不忍回忆的秋思!
以前梦到过好些故人,都不说话,恍恍惚惚。几年来,我也多次梦到她,只是前段那次不同。是在某条街上的偶遇。她一身素服,说了好多话,连言语情绪都清清楚楚,终究还是对爱子和我们有很多的牵念。我常想,一些年后,安静的街肆上一个亭亭的姑娘,扎着马尾辫,捧着一本书,静静地不声不响……那会不会就是她的再生?
又到月满中秋,又是白露为霜。回想那些年我竟没能为她做些什么,这几年除了捧一束花,烧几张纸,还是只能写几行字,化作秋天的怀念。这又让我感到更大的悲伤和愧疚。
作者:曹宝武 编辑:李耀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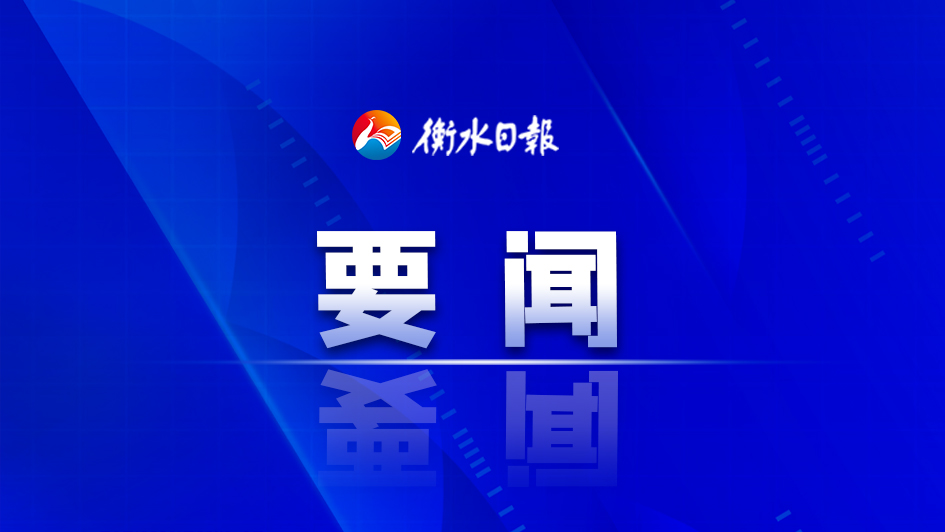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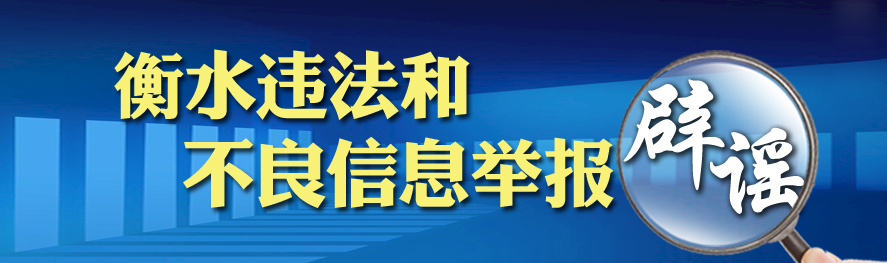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