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7日,收到段华先生寄赠的《孙犁年谱》。此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沈鹏先生题签,煌煌四十三万言,定价198元。
段华是全国著名孙犁研究学者,现居北京。他中学时期即与孙犁通信联系,十八岁因写作才华被南开大学免试录取,得以长年随时拜访孙犁,与之成为忘年之交。他不仅多次聆听大师教诲,还经常帮其查询资料,收发信件,校勘文稿,做过大量服务性工作,参加了《孙犁文集》和《孙犁全集》的校订。他对孙犁所有文章都阅读十遍以上,有些重要作品甚至看过二三十遍。他多年来搜集积累梳理记录有关资料二百多万字,用心血和汗水为写好这部“年谱”打下坚实基础。
曹雪芹《红楼梦》“回前诗”中说:“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而段华这部“年谱”却整整搞了三十年。所以他在《后记》中首句即说:“世界上干什么最孤独和困难——写年谱。谁想体会孤独和困难,就写年谱吧。”
这部《孙犁年谱》一经问世,立即好评如潮,被《文学报》《文汇报》《天津日报》《河北日报》等媒体热情推介和宣传,认为此书“全景展示了孙犁的文艺生活,系统梳理了孙犁的创作脉络”“对孙犁作品的发表、流传、修改、收录等情况进行了全方位立体化的记述”,称此书“是一部研究孙犁的拓荒之作”“是对孙犁先生最好的告慰”。
段华先生惠赠这部“年谱”,是因2009年看过我们写的《孙犁在饶阳》一书。
《孙犁在饶阳》是我与文友牛广欣耗时两年完成的,省作协主席关仁山亲题书名,《文论报》主编封秋昌热情作序,在文学界特别是孙犁研究领域产生一定影响。为“求其友声”,听取意见,我们当时曾冒昧寄赠一些孙犁研究的专家,其中就包括段华先生。那时我看孙犁通信集中有给他的信件达十五封之多,但并不太了解他创作和研究的成就。后来,我们先后收到刘宗武、冉淮舟等人来信,对我们的努力进行了肯定,有的信件还刊发在《衡水晚报》上,但印象中并未见到段华的意见。没想时隔多年,他还对这本小书留有印象,并通过公众号作者刘雅林辗转联系通上微信。他诚恳地说:“感谢您前些年惠赠的《孙犁在饶阳》。后来我去新疆援疆,和您联系少了。拙编《孙犁年谱》出版,拟奉赠一册,不知寄到哪里合适。”见到信息我自然非常感动,表示见书后一定写篇文章。他又表示说:“你别写我个人,要写只写孙犁先生,或者写对《孙犁年谱》的读后感即可。我写这部书,不图名利,只为活的有意义。我把此事当做了生命中的一部分,用这部书为子孙后代提供关于孙犁先生的第一手真实材料。唯此我才坚持三十年做此事!”肺腑之言,倾吐心声,我由衷敬佩,引为知音。
赠书之事令人感叹,另一件事更给我带来意外惊喜:孙犁先生的儿子孙晓达先生允许盖孙犁先生的名章。段华先生所赠之书,即在扉页上盖有孙犁先生印章,让我非常高兴和感慨。
我多年崇尚孙犁先生和“荷花淀派”,也参加过一些纪念活动,但总以未睹大师一面为憾。1983年,趁在津开会之机,我拿着自己在《天津日报》(文艺双月刊)上发的小说,鼓足勇气到报社找过孙犁一次。报社同志告之其家住址后,我又几经犹豫未能成行。这是我平生极度懊悔的一件事。我后来常想,如果找到家里,凭我一腔赤诚和满口乡音,也许会受到孙犁先生的热心点拨或得到一本签赠的著作,那该是何等幸运的事情。虽然今生此梦难圆,但在大师仙逝二十周年之际,却得到钤有孙犁手章的一部珍贵“年谱”,也算对多年遗憾的一种弥补吧。想到这里,我对段华先生的热情如火和细致入微更加深怀谢意。听我表达此意,段华先生却非常谦虚地说:“此书属小众读者之列,你不必刻意去读,翻读孙犁先生作品时,做个参考即可。”我见到书自然爱不释手,逐页逐段认真细读。现在过去几天尚未读完一半,即多处有从未见闻茅塞顿开之感。如书中两次提到毛主席对孙犁的评价,说孙是有独特风格的作家。当事人谈到此事的时间、地点和环境,均史料翔实,记述客观,叫人过目难忘。但此事孙犁先生自己却从未提过,更没付诸文字,文坛耆宿的高风亮节更加令人敬仰,叫人产生想写点什么的冲动。
但我还是想先写下这次赠书的经过。
段华先生刚刚援疆归来,又主持着《中国绿色时报》的编务,公务繁忙可想而知。但恢复联系后即如老友一般关心我的写作,约我有合适稿件可寄他处,并一再说:“有空的时侯,读读书,写点心悦的文章,也是对抗脑衰老的有效办法。”今天这篇“赠书记”,可以说是我近年来最感“心悦”的一篇文字。
作者:何同桂 编辑:李耀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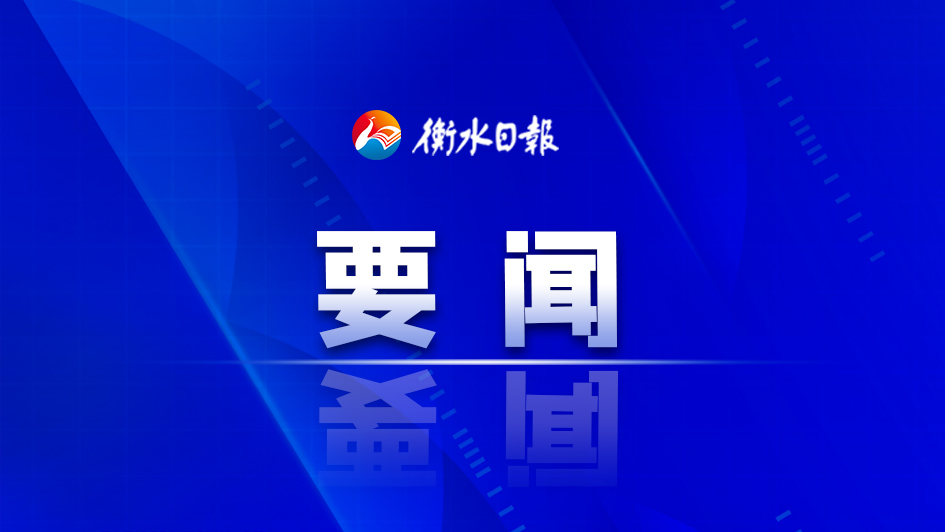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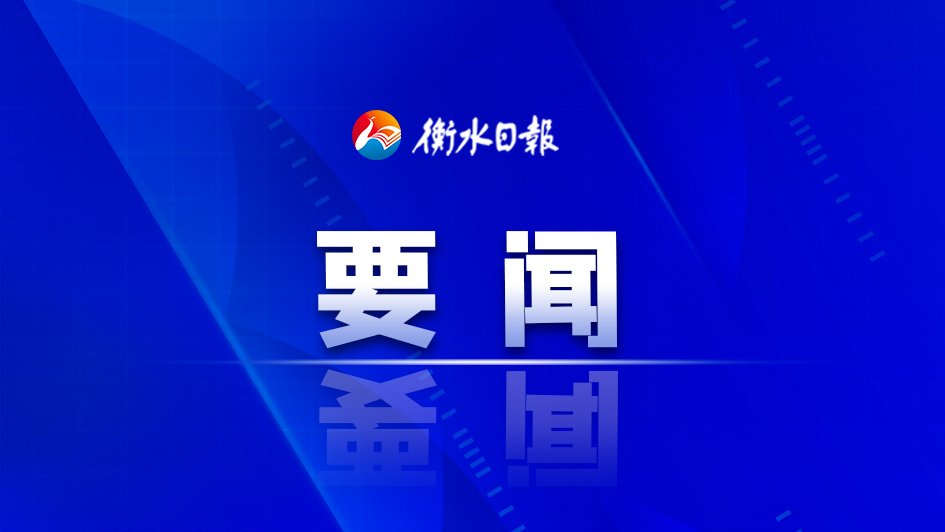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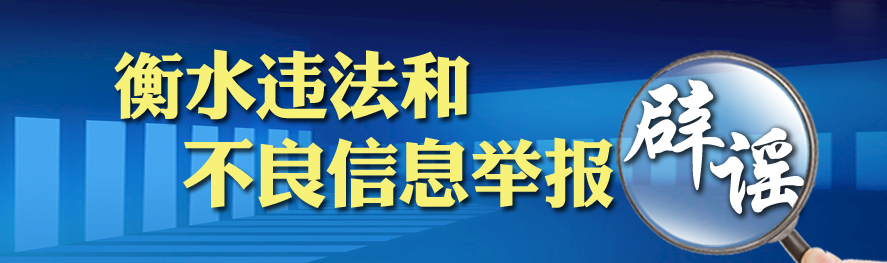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