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薰风起,盎然入夏来。漫步在家乡的大街小巷,看到一个个碌碡一声不响地躺在墙角一隅,仿佛睡着了似的。但它们筋骨犹存,依旧是那样挺脱、圆润、结实,默默地安卧在晨风中,进入了恬静的休闲时光。
掐指一算,这些碌碡退休也快三十年了吧!想当年,它们一个个威风凛凛,被高头大马,抑或健壮的黄牛,甚至是马力强劲的拖拉机拖着,在打麦场上碾来碾去。
“吱吱呀呀”,和火热的空气交织在一起,回响在打麦场的上空。小麦连秆带穗,平铺在宽阔的场院上,被炙热的太阳晒得蓬蓬松松。大碌碡碾压过来,浑圆的麦秆慢慢被压扁了,渐渐由黄变白,成了光溜溜的麦秸。鼓鼓囊囊的麦粒,被碌碡碾压下来,和麦秸、麦糠混在一起。碌碡越转越快,麦秸越压越平,在老乡们的吆喝声中,碌碡收拢翻滚的脚步,告别夏日最火爆的舞台。
芒种又至,收麦都机械化了。这些碌碡功成身退,静卧墙角,成为老乡们小憩的坐物。夜色阑珊,热气未消,老乡们端坐碌碡之上,谈论着感兴趣的话题,那气氛比夏日的空气还热烈。碌碡上却凉气频发,令坐者不躁不热,颇感舒适。因此总有老乡惦念着碌碡,匆匆吃过晚饭,便来此坐定,惬意地等着聊友。一位老乡在碌碡上坐久了,也会有其他老乡提出轮流坐庄,共享清凉之福。那些关于碌碡的话题,老乡们百谈不厌。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缺少娱乐设施。农闲时节,一到傍晚,年轻人不约而同,齐聚场院,纷纷玩起推碌碡、蹬碌碡、戳碌碡的游戏。推碌碡最为简单。推者弯下腰,双手使劲儿推碌碡,待碌碡缓缓启动,便两手交互替换,单手持续加力,越推碌碡滚动越快。推者驾轻就熟,甚至可以跑起来,简直就像推风轱辘一样。蹬碌碡最讲技巧。一个人先用脚蹬动碌碡,然后趁势站到碌碡上,双脚交互用力,踩动碌碡,或脸朝前,或面冲后,但身体需保持平衡。碌碡滚动自如,蹬者越踩越轻快,还可以表演吹笛子等才艺呢!戳碌碡可是个力气活。碌碡平躺在地上,戳者猫腰撅腚,双手捧定碌碡一头的底面,然后呼吸提气,陡然发力,拼命向上抬起。戳者一鼓作气,甚至大喊一声,碌碡就被稳稳地竖起来了。些许游戏,老乡们说得头头是道。现在想起来,既令人不可思议,又让人忍俊不止。老乡们的游戏尽管有些滑稽和笨拙,但他们以苦为乐,强身健体,我们油然心生敬畏,赞不绝口。
说起这些碌碡,可是真材实料,都是清一色的大石头。它们家居深山,脱胎于山石,但比山石更有灵性。它们被石匠雕琢成圆柱体,或长或短,或粗或细,不拘一格,但质地坚硬,以超凡的吨位,成为乡亲们轧麦碾谷的得力工具。它们粗犷的纹理中,刻满了生活的印记,写尽了岁月的沧桑。它们在岁月中滚动,消磨了自己的身躯,为老乡们奉献了甘美的生活。
家乡的碌碡,曾经是场院的主角,在那里大显身手,风光一时,而今成了挂满乡愁的老物件,静卧在小村的角角落落。悄无声息的碌碡,碾过了无边的岁月,滚过了漫长的历程。它们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它们是时代精神的守护神。
多少年过去了,家乡的碌碡,依然转动在我的心中,一刻不曾停歇。它们“石心石意”永不老,它们“石风石骨”万古存。
作者:刘誉盛 编辑:李耀荣





 广告
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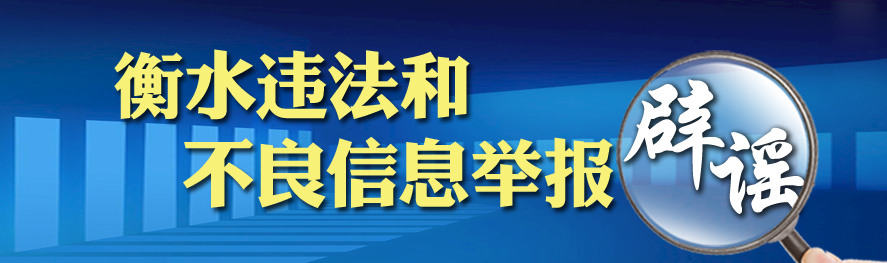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