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农村老家,一年当中两个节日最重要——春节和中秋节。
八月十五中秋节,也是农家秋收最忙的时候。白天,田地里还是晒热,穿半袖都能淌出汗来。母亲忙着掰玉米,白色干硬的玉米皮有些剌手,我跟在母亲旁边的田垄里把玉米一个一个掰下来扔成堆,棒秸叶子划到胳膊上道道血印子,汗水流下来,蛰得很疼。父亲拿着镐头在后面刨棒秸,俗称倒棒秸,要倒得足够深,留下根须太多会对几天后的种麦耕地造成困难。每倒出一棵棒秸,都要在镐头上把泥土磕打干净。几人走过的田垄后面成了一片空地,一堆一堆的玉米、一堆堆的棒秸等着拉回家去。水壶在地头上放着,不能轻易喝水,否则就会来回走很远的路。有时,水瓶子旁边还放着几个大甜雪花梨,为了赶快吃到大甜梨,我们铆足了劲儿想尽快掰完这几垄玉米。
八月十五前一天是姥娘家村的集市,距离我家几里之外。这个集是母亲必赶的,如果实在忙,母亲就派我去,梨和月饼是必买的,肉也会买一点。有了这三样,八月十五的东西就算是备齐了。一年当中,在八月十五之前,我从来没有吃到过梨、苹果这类水果。
八月十五当天,临近中午,母亲比平时回家要早一会儿,因为要准备像样的晌午饭。包饺子是没有时间的,多是烙饼或焖饼这类扛饿又比较省事的饭,油腥比平时多了不少,烙饼里有时会卷几片熏肠,有时会卷炒鸡蛋,焖饼里加了五花肉片,饼条油亮筋道,吃饭时就上几棵大葱、几瓣大蒜很是过瘾。
月饼是土炉烤的五仁馅,不到晚上是不能吃的,因为太少。
晚饭在院子里吃,大而圆的红月亮从东厢房上空升起,我不时抬头看看天上的月亮,期盼着早点吃上月饼。刷洗锅碗后,一家人坐在院子里剥棒皮,煤油灯笼放在外窗台上,月亮越升越高,渐渐地,院子里光亮如昼。蛐蛐声不时传来,湿气和凉意袭来,我拿出一件厚夹袄穿在身上。月亮升到了西南方,移过了那棵大槐树,母亲终于起身,在窗前扫干净的空地上摆上小吃饭桌,几个盘子里是月饼和洗净的梨、石榴、红枣。此时我们都停下了手里的活儿,兴奋地走过来,接过母亲掰成块的月饼和甜梨,月光散在院子里,南瓜、花生、棉花桃,玉米、枣树像披上了银装,我们满心喜悦,心里想着这真是一个丰收年。我也常常会有一个小心思,什么时候能自己单独吃一整块月饼就好了。
有一年八月十五,弟弟刚刚中学毕业参加工作,单位发了两条鱼,便兴冲冲地带着鱼从县城骑车赶回家,到家已是中午时分。本以为母亲会很高兴,谁知刚从地里回来的母亲看到鱼却生气起来,埋怨弟弟说:“你不知道地里正忙着,哪里有空做这鱼吃,听说做鱼得放不少醋,家里醋都不够了……”我忙劝母亲,并自告奋勇去村里小卖部打醋。母亲不擅长做鱼,她把切好块的鱼加上醋添上半锅水,做了一锅鱼汤,再撒上葱花,鱼是小鳞鱼,刺特别多,汤有些酸,那顿饭我是真的没有吃饱。
每年中秋节的晚上,母亲总是把月饼和甜梨给街坊邻居们分分,父亲把准备好的老白干酒给同族的人家送去,父亲在外工作时间长,父母总觉得平时给乡邻们添了麻烦。父亲也会把同族的兄弟或叔伯请到家里来喝酒,先在下午或晚饭前去送一趟信,回来时父亲笑眯眯的,母亲就会问一句说:“来不?”父亲说:“来。”母亲就会准备切熏肠、炒鸡蛋等菜。那时,尽管我们姐弟和母亲都不上桌,却非常高兴,因为一年里家里也没有几次酒场,听他们喝酒聊天也是一种享受。
多少年过去了,中秋又至,清亮亮的月亮触目可及,走在路上,轻风拂过,周围静而明亮。父亲母亲都已在几年前故去,我常常仰望那月亮,仿佛父母就住在月亮上,那挥洒下来的月光就像是父母对我温柔的触摸,这月亮,常常让我望着望着便泪流满面。
作者:刘兰根 编辑:李耀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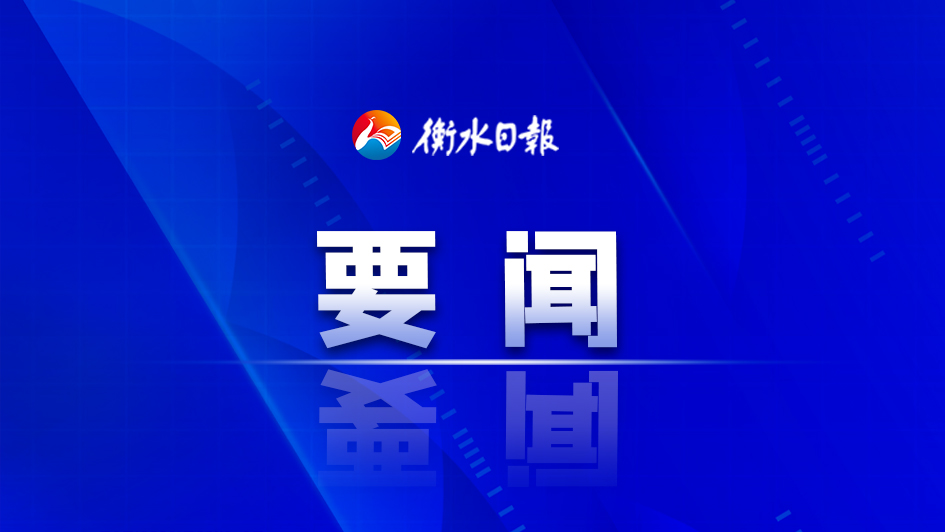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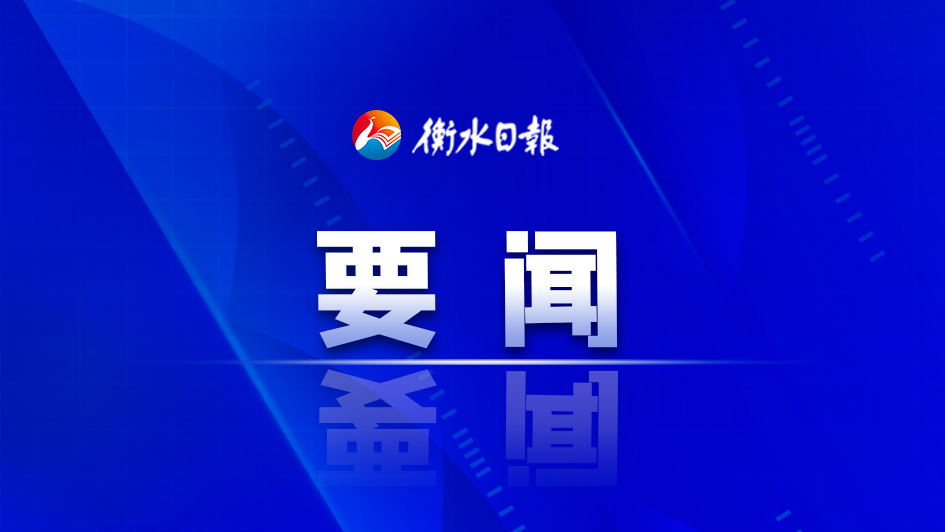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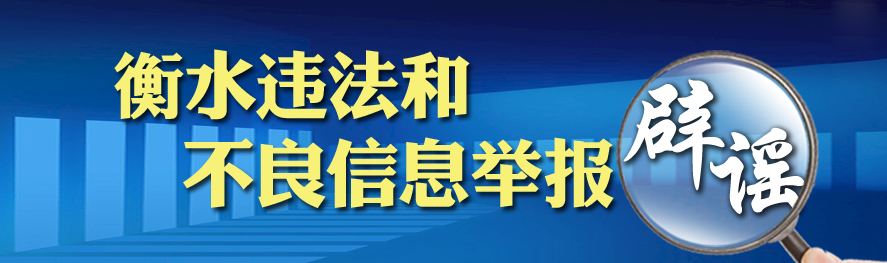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