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春,上海市的“梅兰芳公馆”有一场非同寻常的聚会。主客分别是大名鼎鼎的梅兰芳与刘宝全。一位梅派鼻祖,另一位京韵大鼓“鼓王”。二人欢聚,堪称京剧与曲艺的“峰聚”。
聚会前,梅兰芳先生专门对秘书说:“明天请刘老吃饭,一则叙旧,二来请他谈谈京韵大鼓的源流,三是请教他保护嗓子的窍门。”这次,梅兰芳既向刘宝全先生请教了从艺心得,也帮助他总结了诸多宝贵的表演经验。
民国初年,北京最热闹的地方无疑是“天桥”,清末诗人顾顺鼎曾这样形容那里的繁华景象:“酒旗戏鼓天桥市,多少游人不忆家。”盛夏之夜,人们一只手端着可口的豆汁儿,一只手拿着刚吹成的糖人儿,一边哄着孩子,一边看戏台上各类艺人的精彩表演。其间,当然少不了曲艺名家刘宝全与侯宝林诸位,更离不开梨园重镇马连良与杨小楼等人。
1915年,刘宝全刚成立“艺曲改良杂技社”,往返于京津两地,无论天桥庙会,还是津门故里,都留下了他的铿锵鼓点与唱念做打的身影。除京韵大鼓外,刘宝全具备三大绝鼓——弹琵琶、唱石韵与表演马头调。他曾应邀到京剧大师谭鑫培家,为其寿辰助兴。那种场景实属难得,曲艺名家偶遇京剧大师,美妙的大鼓与高雅的京腔,久久回荡在皇城夜空。
津门故里,堪称风雅之地。天津因漕运而生,几经沉浮,逐渐成为北方水陆交通枢纽。商贾云集,自然少不了文人雅士与民间艺人的出没。除了杨柳青年画与高跷风筝之外,天津卫便绕不过泥人彩塑了。清朝末年,草根匠人张明山在传统泥塑基础上,饰以色彩和道具,形成了独特的圆塑泥人艺术。传说,慈禧太后喜欢彩塑,专门把泥人工匠召进内宫。张明山将黏土掺入棉花,调和均匀后,捏制出栩栩如生的古代人物。慈禧连声叫好,当即赐名“泥人张”。这种做法,类似唐明皇迷恋丑角、宋徽宗钟情于“瘦金体”书法。缘分,当然能成全艺术了。
都市与乡村,都渴望精神文化的滋养。木偶戏,就属这样一种雅俗共赏的艺术,它源于汉,兴于唐,也叫“傀儡戏”,从元朝开始,逐渐由京城街巷发展到乡村市井。几百年来,长安街头、辽西集市与泉州庙会,都上演着相似的一幕:吆喝声中,一位民间艺人,挑着扁担,一头是小箱子,一头是演出道具,找个空旷的场地,搭个小小的舞台,围上布幔,艺人钻进去,敲锣打鼓,唱念做打,全凭一人操作。有时,还运用口技、雕绘等技巧,出神入化、惟妙惟肖的表演,深深吸引着帐外观众,很多人真想钻进布幔,“脸对脸”看个究竟。
任何国家与民族都可能派生出独特的民间艺术。比如,印度街头掩盖不住吉普赛女郎曼妙的舞姿;南非草原跳着原始部落风格的非洲鼓舞;巴西乡村集市到处活跃着拉丁舞者的身影;俄罗斯人在喜庆节日和家庭聚会上跳欢快的踢踏舞;土耳其城堡里反倒流行着威武雄壮的刀盾舞……那些与众不同的身姿、善解人意的笑容,不仅是土著的表演与梦想,更是当地人对理想生活的苦心追求。曲高和寡也好,雅俗共赏也罢,不同地域的民风与艺术,犹如波光潋滟的多瑙河,哪怕源于天涯海角,最终,也能流水淙淙、合为一流——正所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吧。
泰戈尔曾在著名的《吉檀迦利》中写道:“在那里,心是无畏的,头也抬得高昂/在那里,知识是自由的/在那里,话是从真理的深处说出/在那里,心灵是受你的指引,走向那不断放宽的思想与行为。”大概声息相通吧,戴望舒先生也曾多情地吟咏:“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或许,“无畏的心”与“丁香愁怨的姑娘”,正是不同国度、不同语言所培植起来的感悟和畅想吧。
其实,北京城的京剧和京韵大鼓,天津卫的“泥人张”与“杨柳青年画”……都与南非的非洲鼓舞、土耳其雄壮的刀盾舞团队殊途同归了。虽说京津秦淮、燕南塞北,很多艺术都发黄衰老了,它们微弱的血脉却顽强地跳动着。哪怕跻身穷乡僻壤,抑或仅供瞻仰的博物馆,依旧不舍昼夜地呼吸、成长。怪不得,人们还记得,上海滩那场快活的聚会呢。
作者:李秋志 编辑:李耀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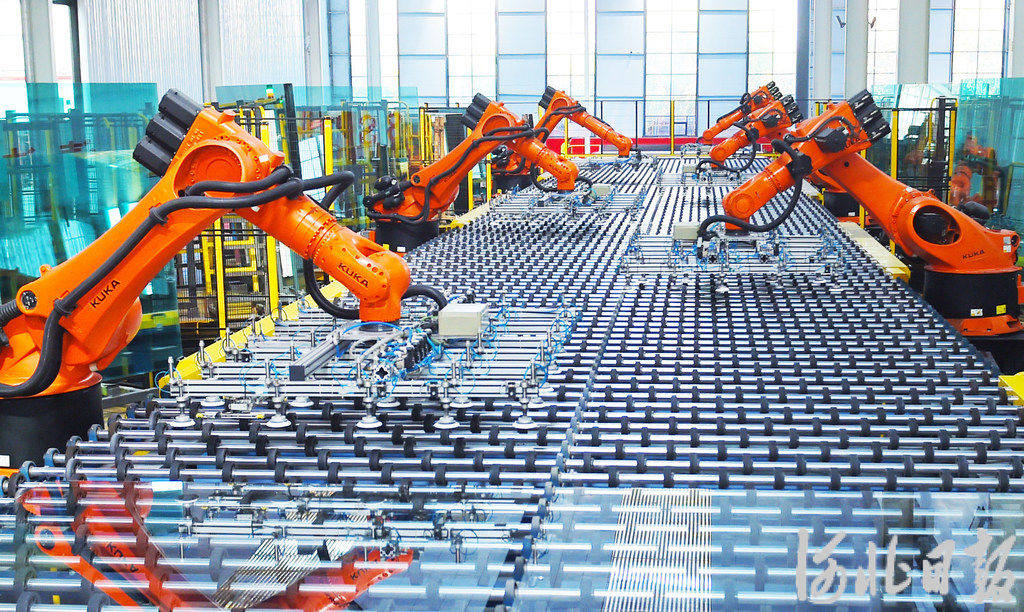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