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河畔认领时光
——读《诗经全鉴》有感
本报记者 赵栋

2200多年前,一位名为毛苌的年轻人,乘船沿滹池河(现称滹沱河)东下,行至饶邑(今饶阳县)。见此物阜民丰,便做了个影响中国人文历史的决定——在城东一小村住下,并向百姓传授《诗经》。清朝《饶阳县志》有记载:“毛苌宅在饶阳师钦村,村南有台,名诗经台,相传是当年毛苌讲经之台”。
这座讲台,被后人看作中华文化的传播源头之一。
因此作为一名衡水人读《诗经》,别有他意。
这“他意”,在于一种传承者身份的自觉认知与亲切感。毛苌并非《诗经》的原始作者,他是至关重要的传播者、阐释者。他让源自黄河流域、江汉地区的诗歌,在燕赵之地扎下了根。作为今天的衡水人,或是站在这片土地上的读者,我们无意中便接续了这种“传播者”与“接受者”的双重身份。
这“他意”,指向一种在精神原乡寻找心灵锚点的深沉慰藉。我们知道在自己生活的这方土地上,曾有一座土台,台上一位先贤正将“思无邪”的诗篇娓娓道来,这本身便是一种无言的滋养。它所象征的“诗教在此发生”的文化记忆,已融入地方的精神肌理。在衡水读《诗经》,更像是一次寻根式的精神还乡。
案头有一本《诗经全鉴》(中国纺织出版社出版),为我推开那条名为《诗经》的、流淌了千年的文明之河。
过去,那些“风、雅、颂”的篇章于我而言,或许更多是教材里需要识记的“最早诗歌总集”,是“赋、比、兴”等抽象概念的集合体。《诗经全鉴》所做的,正是拂去这层因岁月和学科划分而沉积的微尘,让古老的河面重新泛起活泼泼的、属于人的光芒。
“全鉴”之“鉴”,首先在于它提供了理解《诗经》的全景式入口与精微的注解,化解了初读者的畏难之心。《诗经》的语言诚然古朴优美,但其中大量生僻字、名物典章、历史背景,确是横亘在现代读者面前的一道无形门槛。《诗经全鉴》有详尽的注释、流畅的译文,以及对每一篇诗作背景、主旨的扼要解析。它告诉我,《关雎》不只是“后妃之德”的经学化训诫,更是青春萌动时最纯真炽烈的相思情状;它指出《七月》篇中“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一句背后,可能蕴含着女子对未来命运的恐惧。这“鉴”是工具,是桥梁,它让《诗经》的305篇都变得可读、可解,让我得以直接触碰诗中的温度与心跳,而非仅仰望其高度。
更深一层,“全鉴”之“鉴”,在于它引导我透过文字,照见那生生不息的先民情感宇宙与生活世界。《诗经》的伟大,绝非因其古老,而在于它所承载的人性、人情是如此鲜活和真实,且直抵当下。在《国风》中,《邶风·静女》里“爱而不见,搔首踟蹰”的焦急甜蜜,是任何时代恋爱中人都能会心一笑的场景;《郑风·子衿》“一日不见,如三月兮”的思念,稀释在今日的每一条微信的表情包里;《王风·黍离》中那“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的彷徨悲叹,几乎是一种关于家国沧桑、个人漂泊的永恒原型。在《小雅》《大雅》的朝堂颂歌与忧患叹息中,我看到了早期知识分子的责任与焦虑;在《颂》的庄严乐舞中,我感受到先民对天地祖先那份虔诚的敬畏。这不再是与我们隔绝的“古人”,而是一个个有着与我们相同悲喜、爱憎、渴望的灵魂。他们的世界,恰是“全鉴”所映照出的,一个充满烟火气息与生命韧性的中华文明。
《诗经全鉴》这面镜子里,最终映现出自身的精神图景与文明基因。现代社会的信息爆炸与节奏匆忙,常常使我们情感粗糙、表达钝化。《诗经》里那些以“草木虫鱼”起兴,委婉而精准的抒情方式,那种对自然万物细致入微的观察与热爱,提醒我重拾一种与万物共鸣的细腻感知力。诗中反复吟唱的“悠悠我心”“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则是一种远比现代快餐式情感更悠长、更深沉的情感质地。阅读它们,是一次精神的深呼吸。
合上《诗经全鉴》,河水的波光仿佛仍在眼前荡漾。这本书的价值,不仅在于它系统地注解了《诗经》,更在于它以“全鉴”的姿态,为我们架起了一座通古今之幽情、连天地之诗心的桥梁。
而当我以一名衡水人的身份沉浸其中时,这份体验便叠加了另一重维度的深刻:我感到自己正站在毛苌曾驻足的岸边,聆听同一条河流穿越古今的水声。那来自文明源头的清澈与丰饶,因为脚下这片土地,而显得格外亲切与坚实。
当然,毛苌当年的停驻,只是一个历史长卷中动人的偶然。他或许并未预想,自己的一念驻足、一方讲台,会为一片土地镌刻下千年不散的文化印记。然而,这偶然的背后,却潜藏着一种文明生长的必然:伟大的经典与思想,从不甘于囿于书斋或庙堂,它渴望寻找丰饶的土壤,渴望与最质朴的生活相遇,渴望在无数具体的地名与人群中,获得生生不息的具体形态。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衡水读《诗经》,不仅仅是阅读,更是一种认领——我们认领了这片土地被它点亮的过往,也认领了自身作为这永恒流淌的诗河中,一朵微小却清晰浪花的当下使命。这,或许才是那“他意”最深处,连接着历史偶然与文明必然的哲思回响。







 广告
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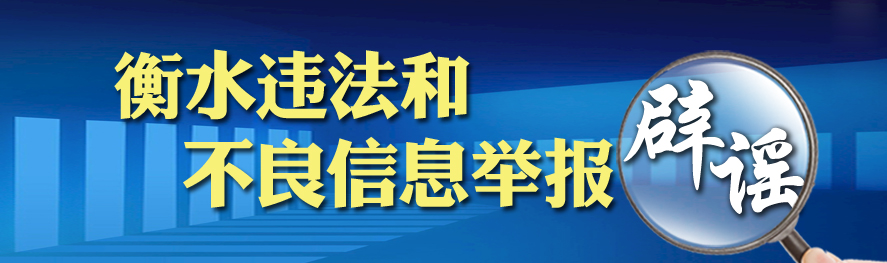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