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4日,深州市乔屯乡于回龙庙村的风里带着几分萧瑟,于庆坤的古琴工作室却暖意融融。案台上,一把半成品古琴静静摆放,他俯身专注上漆,拇指与食指稳稳捏着漆刷,手腕以极小的幅度转动,将取自秦岭野生漆树的天然漆液,顺着刷毛在琴面均匀铺展。这看似简单的动作,是他十余年制琴生涯的日常,也藏着他对古琴传承的全部热忱。


于庆坤与古琴的缘分,源于父辈从事乐器制作的经历,其幼时便在木料香气与乐器声响中度过。而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陈雷激抚琴奏响《太古遗音》的画面,更坚定了他传承古琴制作技艺的决心。“那一刻我就想,要把这千年的琴音传下去。”放下漆刷,于庆坤指尖摩挲着琴身,语气坚定。
带着这份执着,他一头扎进古琴制作的世界。四处寻访老杉木、桐木等优质木料,翻遍古今琴谱与制琴图谱钻研技法,日夜扑在工作室里反复琢磨每一道工序。手上的伤口结了痂又被木料磨破,他却从未停下手中的工具。
“做琴急不得,上百道工序,一步都不能含糊。”于庆坤没停下手中的漆刷,指着琴腹介绍。作为中国最古老的传统拨弦乐器之一,古琴流传至今已有3000多年,一张上好的古琴需经选材、开形、修形、掏槽、试音、上漆等复杂流程,全程要耗时两三年。

其中掏槽和试音是重中之重,直接决定古琴的“魂”。掏槽全靠手工,他握着刻刀一点一点挖凿,力道轻了音色发飘,重了则沉闷,掌心厚茧便是最好的见证;试音时他反复拨弦比对,有时为微调一个音能守着琴坐一整天。
眼前的上漆工序同样容不得马虎,“这道工序对环境要求极高,湿度得控制在65%~70%,温度保持在15℃~25℃,漆液才能慢慢晾干、牢牢附着。”他指着工作室里的温湿度计补充,“这秦岭树漆纯天然、耐酸碱,既能护好琴身,也能让琴音更温润。”这份对每道工序的极致严苛,让他的古琴兼具音域宽广、音色浑厚、余音悠远的特质。
凭借着这份精益求精的态度,于庆坤制作的古琴积累了良好口碑。销售渠道也逐渐拓宽,除了通过网络社群推广、熟人介绍,不少乐器店也主动与他建立了合作关系。“琴友们买了觉得靠谱会互相推荐,乐器店老板试过我的作品后,也愿意帮我代售,这都是实打实的口碑积累。”
更难得的是,多年来常有爱好者慕名而来学习制作技艺。如今,有的学生带着这份技艺留学海外,借着与学生的纽带,他的古琴远销美国、新西兰等国家,让千年琴音在异国他乡流转。
夕阳西下,余晖把于庆坤的身影拉得很长,也给古琴镀上了一层暖光。他手中的漆刷仍在缓缓移动,动作沉稳如初。在这个小小的工作室里,木材与漆液交融,传承与匠心碰撞。他用指尖的温度唤醒古琴的灵性,也让这穿越三千年的音韵,在时代的土壤里生生不息。
王亚楠 李云龙









 广告
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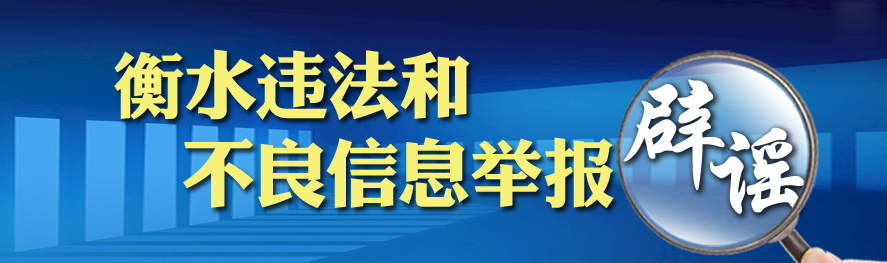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