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年轻时一度痴迷写小说,但属于热情有余天分浅薄的那类。虽“屡败屡战”,可是发表不多且质量平平。
当年文学历练的收获之一,是收到过数不清的退稿笺和一百多封编辑的来信。这些信件我至今装在几个牛皮纸袋里收藏着,偶尔翻看,仍为编辑的热诚和认真而感动。
这些来信中,《天津日报》办的《文艺》双月刊最多,共有十来封。从字迹看还似出于同一个编辑之手。我当时曾反复阅读思考这些信件,从语气能揣摩出此人对稿件似有取舍的权责。但来信从未签过个人名字,只署“文艺编辑部”。后来给我发过两次稿,邮寄刊物竟连信也没写。依我有限的阅历,作品一旦被采用,随寄样刊往往会收到一封编辑便签,有的甚至还让谈谈创作体会。这自然是为了便于联系,并不是希图收获一个作者的感激和回报。作者自然更想了解编辑姓名,这是不言而喻的。
这份《文艺》双月刊是孙犁先生倡办的,初名《文艺增刊》,其《致读者作者》《辟栏说明》及《更名缩短期刊启事》等,都是孙犁亲自撰写别开生面的精短美文(均收于《孙犁全集》第六卷)。
该刊继承孙犁多年主编《文艺周刊》的传统,重视自由来稿,倾力培养新人,每期目录都在《人民日报》刊登,在全国影响不小。
就在刚由季刊改为双月刊不久,该刊刊发了我的短篇小说《玉琴》,内容是写一个农村支书的媳妇,作为“贤内助”处理娘家宅基纠纷的故事。也许当时在该刊发稿不大容易,所以引起地区文联领导的重视,几次叫我参加文学活动,还把省作协首期作家班的唯一指标给了我,通知我参加省里召开的青年作者座谈会。这两次机会虽因故皆未成行,但我对编发这篇小说的编辑却始终心存感激。因除本地报刊外,我此前只在省报副刊发表过两篇文章,还从没上过较大的文学杂志。这篇发稿使我兴奋莫名,以为摸到了文学殿堂的门槛,也刺激了急于求成的发表欲望,就连续寄稿十几次,但却再也没能发表。幸喜那个编辑每稿必退且附一信,除指出明确的退稿理由,也不吝热诚的鼓励之语。尽管总不署名,但瞅着熟悉可触的笔迹,我对此人似乎有了一些亲近感。
1986年,我到县政府办主管综合文秘,因事务杂乱中止投稿。没料到1987年《文艺》竟然又刊发了我的小说《我是委员》。这篇小说是一年前寄的,如不发表我早已忘却了。印象较深的是还得到70元稿费,几乎相当我那时一个月的工资。
这次发稿与上次相同,只寄来杂志,却未附一字。我尽管不再投稿,但总觉这个编辑有些神秘甚至有点奇怪。他退稿时十分认真,总是不吝笔墨指出瑕疵,发稿后却又显得不冷不热,一副公事公办的面孔。
我对这个寿命不长的刊物印象极深,连续订过好几年,而且总以为主编就是孙犁。及至多年后读到孙犁的《记邹明》一文,才知道该刊主编是个叫邹明的人(那时刊物都不印主编责编之名)。孙犁在文章中这样说:“我有时办事莽撞,有一次回答丁玲的信,写了一句:我们小小的编辑部,于是外人以为我是文艺双月刊的主编。这可能使邹明很为难,每期还送稿子征求我的意见,我又认为不必要,是负担。”我这样的基层作者,自然是孙犁所指的“外人”。
《记邹明》,是孙犁晚年回忆文坛故友最长的一篇文章,足有五千多字。他说:“很多外人,把邹明说成是我的嫡系,这当然有些过分。但长期以来,我确把他看做是自己一个帮手。”“他是我最接近的朋友,最亲近的同事,初交以谈,后来也没有大起大落的波折变异。”“我这副科长,分管《文艺周刊》,手下还有一个兵,这就是邹明。他是我第一个下级,我对他的特殊感情,就可想而知了。”
谈到邹明的工作,孙犁更是非常肯定地说:“我对他看文字的能力,是完全信赖的。”“我写了东西,自己拿不准,总是请他看一看。”“他的资历、影响,他对作家的感情和尊重,他在编辑工作上的认真正直,在文艺界得到了承认。”
但这样一个好编辑却命途多舛。邹明曾受牵连调离报社,文革后因孙犁力荐才回来主编《文艺》。按孙犁所言,“他的官运不通,可能和他的性格相关,他脾气不好。在报社,第一阶段,混到了文艺部副主任,和我那副科长,差不多。第二阶段,编一本默默无闻、只能销几千份的刊物,直到今年十月一期上,才正式标明他是主编,随后他就病倒了。”令人扼腕的是,邹明1989年冬抱憾离世,倾注满腔心血的《文艺》也同年停刊。他去世后,孙犁先生立即写出长文发于《光明日报》,并多次提醒老朋友们关注此文。他对与邹的友情念念不忘,萦系于胸,以至常常梦见老友相会。据段华所著《孙犁年谱》记载,邹明逝后第二年的7月19日,孙犁在《书衣文》中悲怆记载:“梦见邹明,失声痛哭。”据刘宗武编孙犁的《书衣文录》载:1990年7月19日晨,孙犁又写道“昨晚梦见邹明,似从阴间请假归来探望者,谈话间,余提及已嘱李牧歌将纪念他的文章,及早汇印成书,不禁失声痛哭。邹瘦弱,神色惨淡,似颇不快,余急呼牧歌慰之,遂醒。”由此可见孙犁对他的感情之深,怀念之切。
最近有幸结识孙犁研究的著名专家段华,在其办公室看到许多珍稀资料。他电脑中收藏着多方搜求的数百封孙犁先生和友人的来往信件。他热情地打开几页请我浏览,一封一封如数家珍。这时我突然想到,段华肯定存有邹明的信件和手迹,那些对我认真指点的信件是否和邹明有关呢?于是我用微信图片把两封保存完好的旧信发给段华,他认真比照后,十分肯定地回复:“看了您发来的信函,找到资料,比照很久。从行文笔法上看,《文艺》给您的那两封信,就是出自邹明同志之手。”并用微信发来邹给他的亲笔信叫我反复对照。我兴奋地说这样的信自己有十来封,有钢笔所写,也有铅笔所书,但笔迹是一致的。段华回复说:“如果是同样笔迹,基本可以断定都是邹明同志亲笔所写!”
我心中释然了。自己虽没写出什么有影响的作品,但对那些默默无闻悉心指导帮助过自己的编辑老师应该铭记终生。
这里面自然包括邹明同志。
作者:何同桂 编辑:李耀荣
 广告
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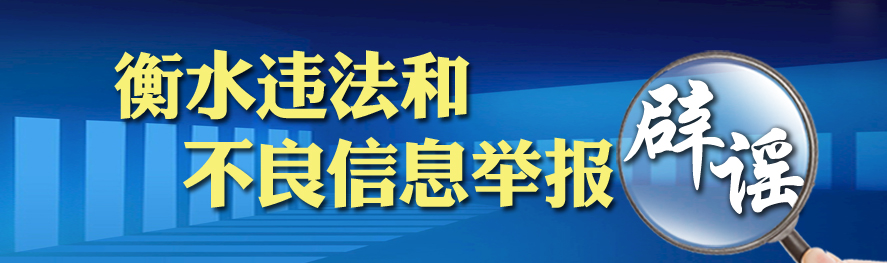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