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一玄教授自1946年起在南开大学中文系任教,是研究明清小说史料的知名专家。从我记事起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他家一直住在南开大学西村24号,与我家斜对门。他有四个孩子,四个孩子名字的最后一个字连起来是“中华人民”。其中老三叫朱予人,是我小学时的同班同学、初中的同年级同学。由于这两层关系,我称呼朱一玄教授为朱伯伯。
听父亲说,朱伯伯年轻时曾经被错划为右派,不能上台讲课,只能在资料室打杂、干重活,工资收入也相应减少。由于工作劳累,再加之心情不好,感染了肺结核。当时他家四个孩子最小的才两岁,最大的刚过10岁,生活本来就不富裕,朱伯伯又罹患重病,更加入不敷出,捉襟见肘。到我上小学时,他的病情才逐渐缓解,生活窘态也略有改善。
在我们初中二年级时,文化大革命开始。由于朱伯伯是摘帽右派,自然在劫难逃。无休止的抄家、劳改、批斗,折磨得他心力交瘁,可谓历尽磨难。
1969年,我们这一届初中毕业生下乡插队,我和朱伯伯的三儿子朱予人都被分配在河北省阜城县,但是不在一个公社,相距约有二十公里,交通不便,因此来往很少。只是听别的知青说,朱予人插队的那个村子很穷,劳动一年不但不能分红,甚至还需要向生产队里交钱,所以还需要家里父母给予补助接济。当时我想,朱伯伯什么时候能松口气呢?
文化大革命以后,知青陆续回城。我当时在衡水工作。听说朱予人被安排在唐山铁路局的古冶工务段工作。虽然工作辛苦,但是收入稳定,与插队时的困境相比也算是脱贫了。与此同时,朱伯伯错划右派的问题得到平反改正,他的大儿子和大女儿也都结婚成家,我心里为朱伯伯高兴,他总算过上了幸福安定的晚年生活。
但是,这样的幸福生活没过多久,就听说朱予人在工作中因事故死亡。这个消息对朱伯伯来说无异于是晴天霹雳,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让朱伯伯本就瘦削的面容更加憔悴。
尽管人生如此坎坷,朱伯伯以问心无愧的坦荡胸襟顶住了被错划右派带来的政治压力,以随遇而安、乐观豁达的心态战胜了罹患重病导致的身体痛苦,以常人不可思议的毅力承受了老年丧子的心灵创伤。他老人家始终矢志不移地坚持自己的学术道路,笔耕不辍。以甘为他人做嫁衣的孺子牛精神在中国小说史料学领域独树一帜,著作等身,不仅为三国、水浒、红楼、西游、金瓶梅、聊斋、儒林外史等传统名著编纂资料汇编,还著有《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等十多部专著,共一千多万字。
因为我自幼就认识朱伯伯,在我的心里,朱伯伯首先是一位和蔼可亲、慈祥宽厚的长辈,然后才是著作等身的学者。对晚辈提出的问题,哪怕是无知可笑的问题,他都耐心地予以回答。大约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我阅读《红楼梦》时,对五十回中薛宝琴所出十首灯谜的谜底很感兴趣,但是翻遍全书没有找到谜底。一次偶然碰到朱伯伯,就冒昧地向他提出这个问题。他对我的好学精神予以肯定,并送给我一本他撰写的《红楼梦人物表》油印本。当年没有电脑,朱伯伯完全靠手工翻阅整理、书写而成,其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
1997年,《红楼梦人物表》油印本更名为《红楼梦人物谱》,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朱伯伯没有忘记我这个提问薛宝琴灯谜的晚辈,特地送给我一本。他老人家对扉页上的留言颇费心思。因为我家和他家一直是近邻,他和我的父母都很熟悉,我和他儿子是同学,他老人家知道我的小名,但是不知道我大名。他感觉在扉页赠言中不应该用我的小名,但是再询问我的大名似乎也不妥(后来他老人家说,这么近这么熟的关系都不知道大号,不好意思问)。他老人家想了个两全其美的方法。在扉页上恭恭敬敬地写我父亲的名字,但是在将书送给我父亲时,特别郑重地嘱咐说,这是送给你女儿的,她喜欢读《红楼梦》,这书给她做参考。收到书之后,我非常高兴,非常感动。当面向朱伯伯表示感谢,朱伯伯回报以谦和慈祥的微笑。他说,写书的目的就是给人看的,你喜欢看就好。
进入21世纪以来,朱伯伯年事已高,身体大不如前,但是老人家依然阅读不止,学习不止,研究不止,并坚持练习书法。一天,父亲在外面散步,碰到朱伯伯,聊天时说起我以同等学力的身份考硕士、读博士,并且已经被聘任为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的消息。朱伯伯说,这孩子是我看着长大的,就像是我的侄女。她这么有出息,我也很高兴。隔了几天,朱伯伯托人将他写的两幅字送到我家,鼓励我再接再厉,不断进步。
过了一段时间,偶然看到一篇介绍朱伯伯的报道,得知朱伯伯因为罹患关节炎,各个关节都变得僵硬,手指关节不灵活,写字握笔拿笔很困难,但是仍然坚持写读书写作。我才意识到,朱伯伯送给我的字是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写的。我非常感动。我何德何能,竟然得到朱伯伯的如此关心和厚待。
朱伯伯于2011年10月16日仙逝,享年100岁,给后人留下了数量不菲的研究成果和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作者:周晓苏 编辑:李耀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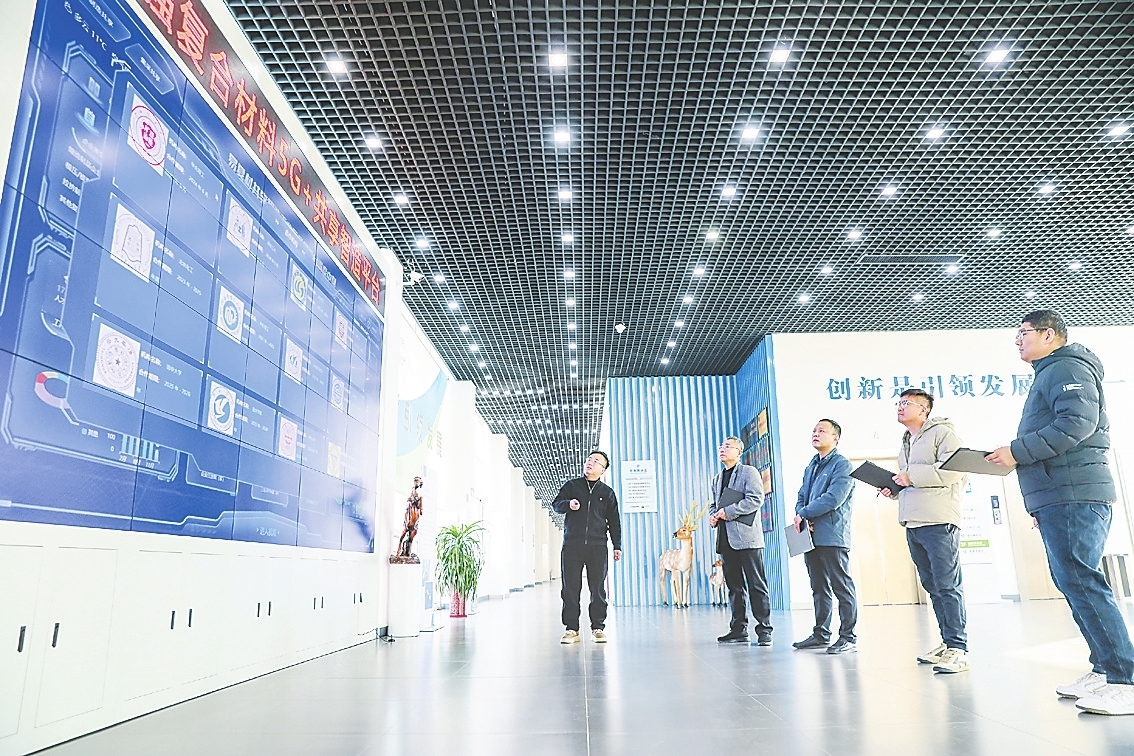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