滹沱河,是饶阳人民的母亲河。
这条日夜奔腾川流不息的河流,是饶阳的地理标识,也是饶阳的文化摇篮,是千年古县一道最壮美的风景,也是饶阳世代儿女心中永远的图腾。
遍翻饶阳史志,我们会看到,那些载入典籍的贤哲名流、志士英模都在滹沱两岸留下过闪光的足迹。那些脍炙人口的故事传说和诗词美文,也几乎都与这条河流相关,而名闻遐迩的饶阳十景则多是滹沱河滋润浇灌的花朵了。
饶阳是文明古县,也是文化强县。近年来文学创作非常繁荣,别开生面,涌现出很多优秀作者。尤其令人可喜的是,不少作者能够自觉上承文脉,下接地气,继续满怀深情地描写和讴歌滹沱风情,描绘着一幅幅五彩斑斓的画卷,吟诵着一曲曲韵味悠长的诗章。
刘善民同志即是其中的佼佼者,这部《老河湾的味道》就是一个证明。
善民是我的文友,相识已经三十多年。他生于滹沱蜿蜒环抱的大齐村,伴着蒲苇萌芽生长,和着涛声背书吟诗。这条日夜相伴魂牵梦绕的河流,似乎从少年时期就给他注入了热爱文学的雄健基因。我常由此联想到一些名扬国内的文学大家,如大运河之于刘绍棠,呼兰河之于萧红,滹沱河是否也是冥冥中起着这种神秘的作用?
善民对文学的痴爱是始终不渝的。他不论从军于古城沧州,还是转业于党政机关,不管就职于乡镇基层,还是服务于公益事业,总是利用业余时间读书学习,操笔弄文,不断有作品见诸报刊。特别是近几年来,他集中精力创作了大量讴歌滹沱河的系列散文,受到文友和广大读者的赞扬。
我非常喜欢善民的散文,只要见到发表就看得非常认真。后来有了微信,他每有新作也常发来叫我先睹为快。有一次,他把描写滹沱风情的几十篇散文打印出来,诚恳地说请我“提提意见”。我认真看了几遍,感叹于他的执着和才华,但并没有什么真知灼见予人。为表示自己并不敷衍朋友的态度,就认真标出几篇自认为写得较好的,指出几篇稍有逊色的。其实我说的只是一种感觉,究竟好在哪里,差在何处,也没说出个子丑寅卯。后来被我看好的一篇《芦荡情歌》被《河北日报》的《布谷》副刊以《芦荡爱琴海》为题选发。我听说后十分高兴,当时曾写一诗赠他,现抄录如下:
恰是寒风凛冽时,
欣闻“布谷”唱花枝。
芦荡恋歌如美酒,
滹水情缘胜好诗。
信手拈来清丽句,
灵感常有奇妙思。
每见华章情难禁,
文痴自古贵相知。
这首诗,是对善民创作不断攀高的祝贺,也表达了我对他作品的一个总体印象。
我喜欢善民散文中蓬勃的诗意。
美文如诗,自然是一种很高的境界和要求。善民的写作在这方面下了苦功。这也得益于他平时总是勤于写诗。他的散文多取材新颖,视角独特,行文轻盈隽永,词句鲜活灵动,读来有韵有味,令人感到一种阅读的享受。这是认真读书和反复锤炼的结果,也和天才秉赋有关。
我也喜欢他散文中那种充盈着水汽的泥土芳香。
善民的为人,是脚踏实地的,他的文章是言之有物的。他笔下的素材,来自于多年酸甜苦辣的生活积淀;他的灵感,得益于反复的思索和梳理。尤其是朝花夕拾的那些故乡风景、人物、故事等都写得有滋有味。在他的笔下,故乡的波光帆影、绿柳长堤、红荷嫩苇、草滩野花都如诗如画;同学玩伴、家人亲友、干部社员、东邻西舍,都活灵活现。这些储存在心的素材,在他笔下看似随意铺排,实则剪裁有度;看似信手拈来,实则颇具匠心。
《山爷》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山爷是本村的一个光棍老头。”在他脑海里“存了50多年”。他清楚地记得“山爷那两间土坯房,外墙用麦秸泥刷抹得光滑顺溜。屋内虽然窄小,倒也干净利落。进屋右侧紧挨门的地方是做饭的锅灶,迎门处的墙上,悬挂着一张发黄的武强年画《鲤鱼跳龙门》,彰显着他从未泯灭的梦想……”如此细腻的描写,让人如临其境。按年龄算,当时善民应为童年,如果不是左邻右舍,如果“这个庄稼老头”在他心中没有位置,断不会有如此深刻的印记。可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才能增加文章的厚重感。
善民写“山爷”,既着眼于他的一些生活小事,又关注到他在历史重大事件上的态度和表现。比如,在村街制止孩子们混吃商贩的糖葫芦不给钱,“不能坏了咱村的名声”;在抗日战争时期,面对鬼子的刺刀,“死也不出卖乡亲”;在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的政治风暴中,“他的那间小屋,从来也没冷淡过谁”。都是从人性角度,客观地反映人物的内心世界,不刻意拔高,不任意渲染,体现了一个“真”字。
1996年8月,滹沱河暴发了百年一遇的洪水。当年,善民在官亭乡任职,在北堤日夜坚守了半个多月。他的家乡大齐村就在下游不远处,早已成了“汪洋大海”。在《亲历“96·8”抗洪》一文中,善民没有将自己刻画成“高大上”的英雄人物,他在真实记录当时干部群众抗洪场面的同时,袒露了自己对家乡的担忧。
朴实的语言,真实的家乡情结,令人感动,体现了一个“情”字。
善民的文章,常常以情胜出。读他的文章,不仅可以看到他的经历,还可以走进他的内心,了解他的生活态度和处世准则,知道他的审美观念和善恶标准。
古人常说“道德文章”这句话,把道德和文章放在一起谈。毛泽东主席也说过:“文风就是作风。”善民文笔干练老道、自然细腻,字里行间透露着真情、良善、正能量,透露出一股豪爽之气,让人觉得他是一个可交的文友。
记得第一次相识是在我的办公室里。他那时只有二十多岁,刚从部队转业到县委报道组工作。他说当兵时读过我的小说《芝麻花》,因文末标有“作者系饶阳县委干部”,所以刚上班就打听我,说能够相识非常高兴。我那篇小说发表后,虽收到过两封来信,但并没人慕名找我,所以印象很深。那天他只说自己爱好文学,却没谈自己的创作经历和成绩。后来才知当时他已在《沧州市日报》等报刊发过作品。以他的年龄,这已属起步较早崭露头角了。但他没说一句炫耀卖弄的话,只是表示要“向你学习”。从此事可以看出,善民是处世低调且非常谦虚的人。仅此一点,就和那些成天云山雾罩、胡吹乱侃的人不可同日而语。“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真是千古不易之理。
善民出书,请我写序,并反复强调说:“你一定要给我指指缺点和不足。”我想,作为一个立志文学创作的人,必须力戒浮躁,尽量远离繁华热闹,锲而不舍,坚持苦练内功和定力,这样才能不断突破瓶颈,打造精品,攀越和占领新的文学高地。
我相信,善民会离这个目标越来越近。尽管他已经五十多岁,但在我心中,他依然是那个朝气蓬勃、埋头创作的小伙子。
作者:何同桂 编辑:李耀荣









 广告
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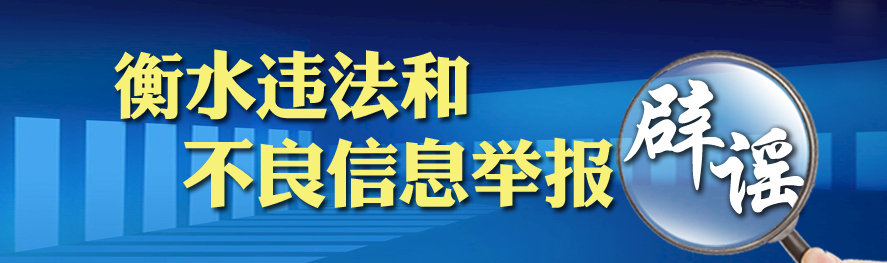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