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大同,有幸和朋友参观了一个门帘展。每一副门帘都是用五颜六色的旧布头拼接而成。布料有的薄有的厚,都被心灵手巧的女子合理布局,精心安排,成为整体美感很强的一幅画。图案有的是繁瓣的大花朵,有的是标准的几何图形,有的是俏皮的小虎小兔小鸡雏。这些门帘陪着女子的一家人,在山村里挂了很多很多年。
小时候,家里各屋挂的纸管帘子都是姥姥穿制的。先用废纸搓成细长的纸管儿,涂上油漆,油漆干透,再用带钩的铁丝把纸管儿勾串起来,一条条挂在横板上,一副纸帘子就成了。这屋是红白条的,那屋是黄蓝格的,屋屋各异,年年不同。最喜欢的是一副墨绿色门帘,干干净净悬挂在爹娘睡房和外屋之间,挡着苍蝇蚊子,晃着出出入入的人影。我和妹妹经常从帘子里钻出头来,攥着两绺细长的帘条子垂在耳边腋下,当成古装戏里皇姑的大辫子。纸帘子慢慢脏了,变形了,夏天就过去了。
再小的时候,我跟姥姥姥爷生活在一起。村里还没有电灯,晚上姥姥经常带我去“大姥姥”家玩。大姥姥家常常聚了好多人,人们围着煤油灯聊天,或者给我出谜语,让我跟桌子比个头。有时候,人进来得急,用力掀门帘,灯头忽闪忽闪,把持不住,熄了。这时候,大姥姥就从炕上起身,去摸火柴,人们继续说话。有火星一闪一闪,那是有人在吸旱烟。火柴一划,小火苗从火柴头粘到煤油灯上,慢慢跳跃,像它从来没有离开过一样。
大姥姥家的门帘是蓝色的,本是一块白粗布,请走街串巷的人拿去染了的。这长方形蓝布挂在大姥姥屋和外屋之间,凭着脚步声,屋里的人准会猜到要进来的是谁。有时候,脚步声不熟悉,人们就一起望着门帘。等来人撩帘进来,炕上、柜子上的人就松动起来,给来人让坐:“你怎么有空呀?”
大姥姥家的帘子里人们絮絮缓缓地说话。一大屋子大人之间,我是那个最不起眼的安静小孩,有时会跳下炕,来到地上“转裙子”。人快速旋转,等裙摆飘起来了,就猛然蹲下去,裙子就变成一个圆圆的花苞。大人们说他们的,我转我的。有时候灯头火苗也被我带动得忽闪起来,人们的影子就在墙上忽长忽短地游荡。等门帘一动,我便会飞快逃到炕边偎依在姥姥身边,一来是怕,二来是羞。小小的我,在那个幽暗的小屋里,度过了无所事事的童年。
老爷爷的屋里挂着一个竹帘。竹帘由细竹条横编而成,并不能上卷。想要进到门里或出去,必须推开硬硬的它,从缝隙里出去。所以每次出门进门都小心翼翼,不得鲁莽。老爷爷的床铺下有他的旧手绢,里面包着零钱,我和妹妹觊觎很久。后来,我们分别都作了贼。我攥着一张五毛钱一溜小跑跑到村供销点,买了一只玻璃管钢笔。妹买的什么我没问,反正后来她也招了。
老爷爷的橱子里,有时会飘出香味儿,那是老姑或是别的亲戚买的槽子糕。老爷爷总是慢慢打开锁,慢慢拿出这稀罕东西,我和妹妹一动不动,一直盯着老爷爷的手,直到那槽子糕堵住了口水。槽子糕的香甜松软是一座味觉丰碑呀,至今没有什么味道能够超越。
冬天,母亲会缝制一个棉门帘。把旧床单、旧被面裁剪成形,缝纫机嗒嗒响着,很快就成了一个布套子。把旧被子里拆出的棉絮装进去,再缝压好,寒气就挡在院里不得进屋了。棉门帘会挡住光,外屋在冬天都是暗的。除非点蜂窝煤炉子时,烟太多,才掀开棉门帘。过年时,爹娘会在门边门头贴上大红的春联。花棉布门帘被夹在正中间,好像它才是最尊贵的君王,震耳欲聋的鞭炮仿佛都是为它放的,神气得很呢!
如果手里端着东西,腾不出手掀门帘,就要用身子拱了。拱开棉门帘,身子一转,就转进屋了。很喜欢这个动作,有时和妹妹就算空着手,也要垂下来不去碰门帘,直挺挺转进屋。天气渐渐暖和了。太阳把棉门帘晒得很厚,身子都不愿挨它了。母亲就把门帘摘下来,换成轻巧的单布门帘。我们又可以隔着门帘藏猫猫了。
纸门帘、布门帘、竹门帘、棉门帘,都是童年少年的物件,不懂“帘卷西风”,不懂“柳絮惊春晚”,也不懂“帘动午风花气暖”,它悬挂在有老有少的普通农家,守护着平静温暖,慢慢陈旧,慢慢漂到岁月的长河里去了。却有时会翻浮上来,在记忆的浪花里和我重温过去的光阴故事。
搬到小城,人们已经不再挂门帘了,我只在书房门口挂了一个香樟木珠半截帘。人一过,帘子上的小木珠就摇晃碰撞起来。人走了,帘还在动,还在细响,晃晃悠悠,把时间都晃慢了。它也将是岁月的故事,帘内的人,会尽量把它写好。
作者:张爱丽 编辑:李耀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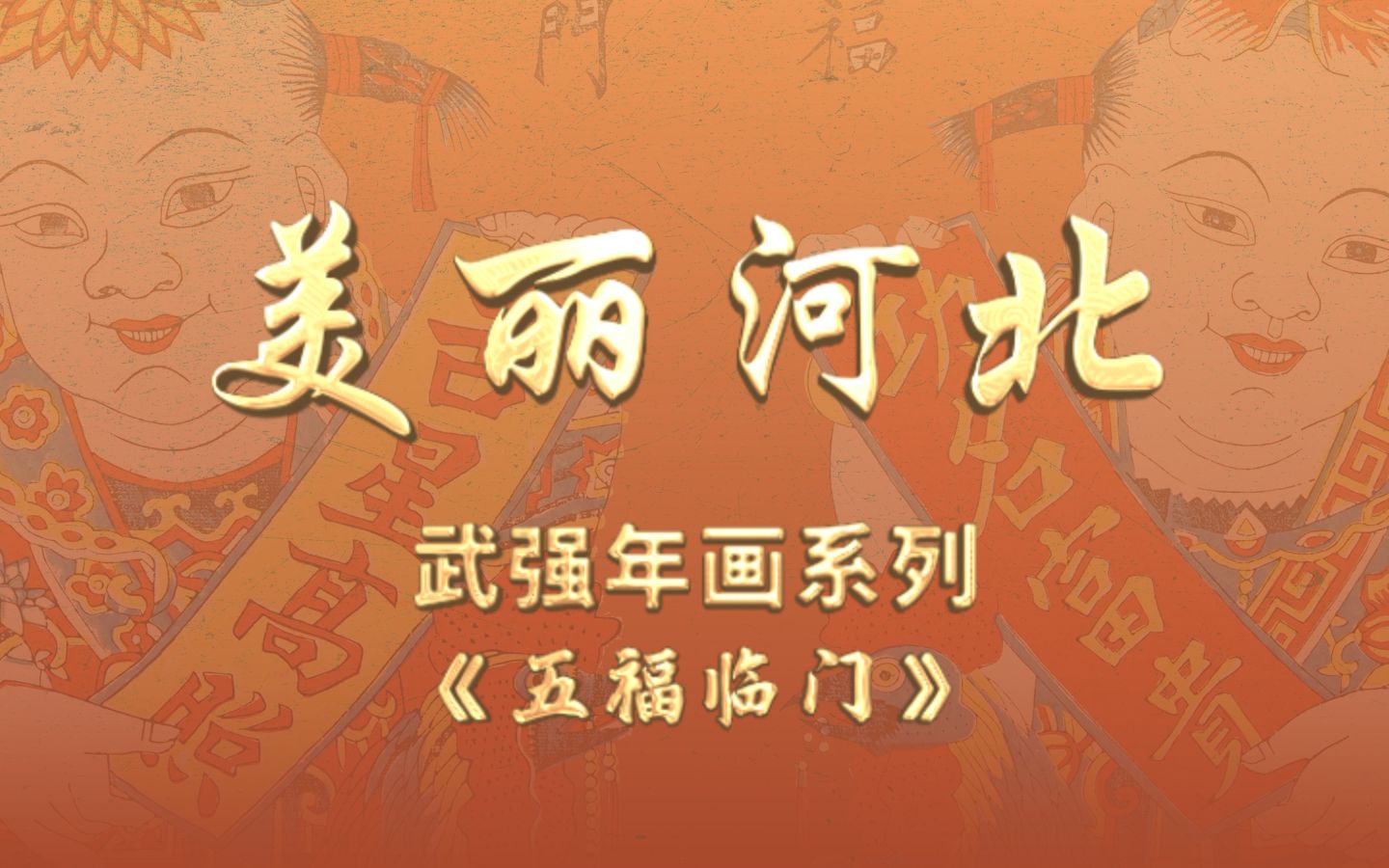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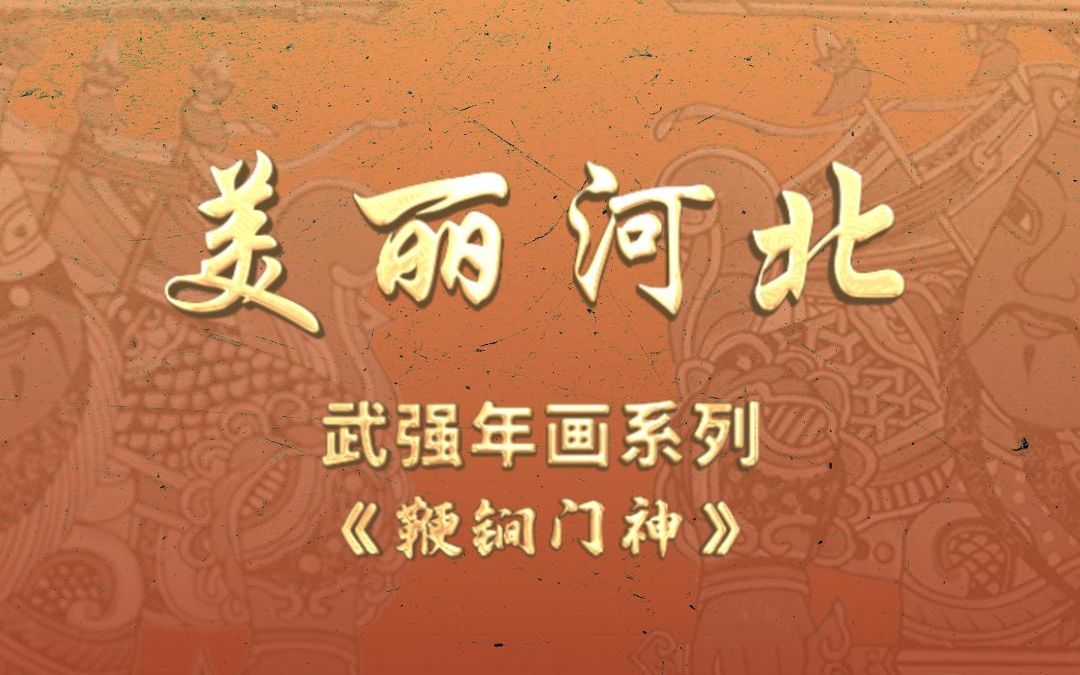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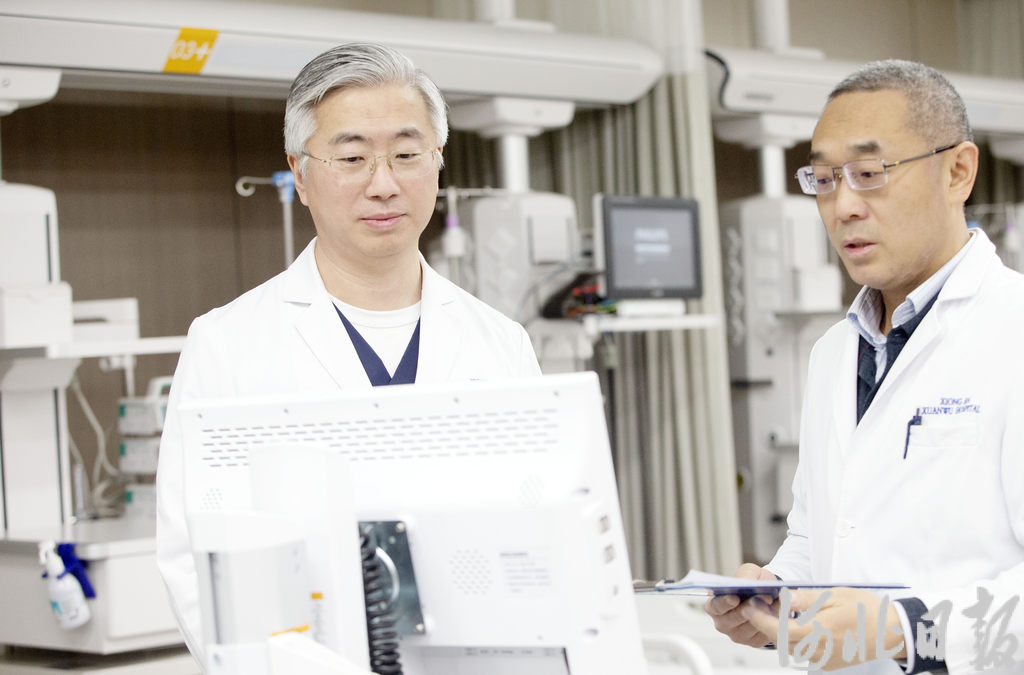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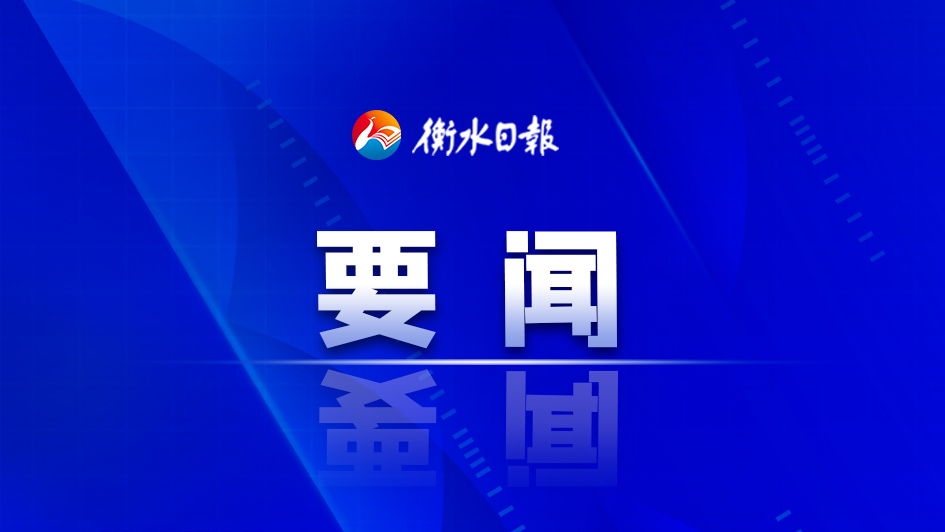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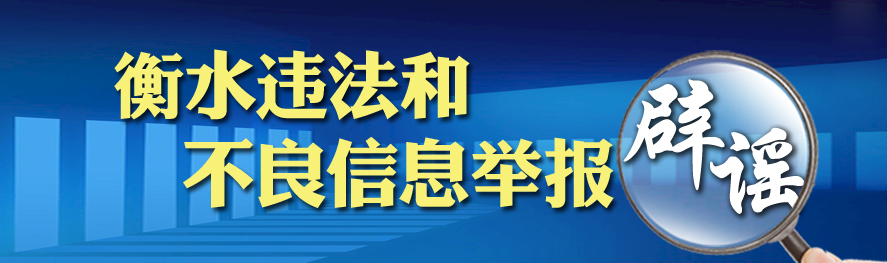



 广告
广告

 广告
广告


